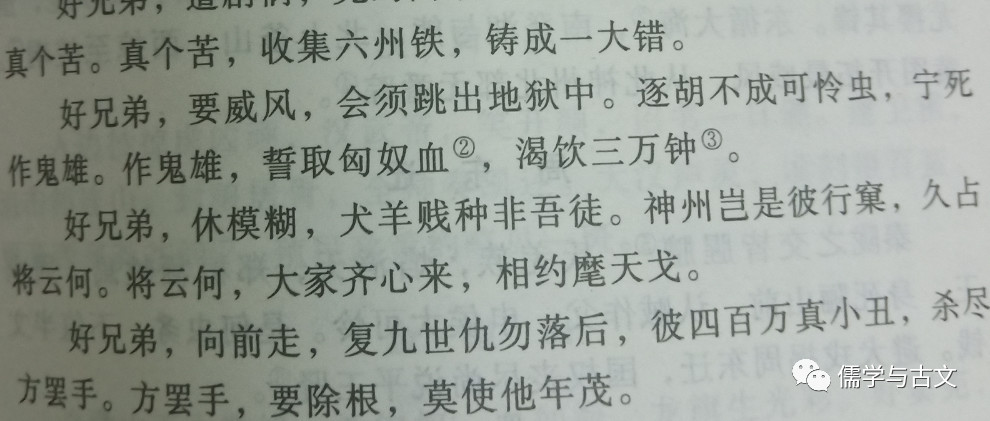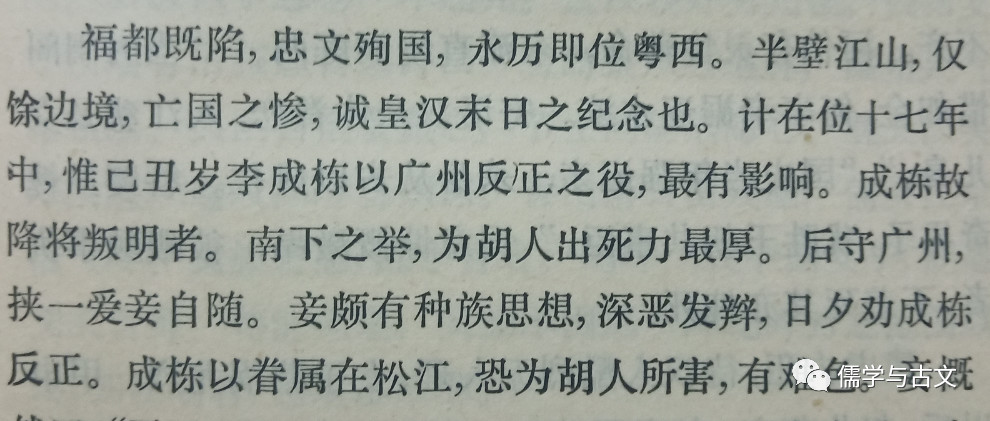商鞅之说秦孝公,先说以帝道,继说以王道,后说以伯道,或以为鞅本以帝王之道说孝公,奈孝公悦霸道,遂辅孝公行霸道耳。商鞅者,惨刻寡恩之人也,其说孝公以帝王之道,特试孝公耳,岂诚以帝王之道说之哉?其说帝王之道,亦不过帝王之粗,帝王之精意,固未达也。先说帝王之道,以自抬高,恐言之卑而为人主所薄也。战国之初,虽周礼坠地,而先王之道犹遗,诸侯尚未敢公然争利,以诈力为尚也。商鞅之说诸侯,不之六国而之秦,知秦之渴于求才,而其俗之好利,便于说,果于用也,先说帝王之道,不遽说霸道,未知秦伯之志,而以此相试也。非以说帝王不从,则说霸道也。夫帝之降为王,风俗之变迁耳,王霸则诚伪之别也,故帝王并称,王霸必辨,鞅以帝王亦判为两途,则知其言大欺人耳,固不知帝王之道也。而所说霸道,亦非真霸道,霸术耳。霸道犹以力假仁,以恤民为务,鞅之所为霸术,唯务国之富强,仁义无所假也,霸道尊主庇民,鞅之法,损下利上。岂比管仲狐偃之辅桓文哉?管仲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劝桓公张四维,兴灭国,继绝世,亲有礼,伐不仁,天下以之粗安。狐偃劝文公行信义而服诸侯,讨诸侯之无礼者,攘楚之强横,中原以之不危。鞅辅孝公称强,比于桓文之霸,则相去远矣,以力不以德,尚刑而轻礼,弃信而用诈也,诸侯畏其力而不服其德,民畏其刑而不守其礼,邻国惧其侵而恶其欺。且鞅之变法,败秦之风俗,害及天下,奖告奸而父子不相亲,行株连而多死无辜,作腰斩车裂之刑而伤天地之和,秦统天下,犹行鞅法,天下大乱,二世而亡,实源于鞅也,成也鞅法,败也鞅法,急功近利之多弊不可久,勿以王道为艰难,而笑仁义为迂阔哉!
鞅者,富贵中人,其说人主,不过求富贵耳,故但为君福而不恤民痛,但为近利而不虑后患。孔孟之游列国,其说人主皆以仁政王道,不用不合则去,不枉尺而直寻也,枉其道,未有能直人也,虽不成功得志,而后人皆称为圣贤,万世以为师表。鞅之说秦君,先以帝王,后以霸道,可谓反复矣,因阉人景监求见,可谓枉尺直寻矣,虽成功得志,封商君,后世学者耻言商鞅,引为训诫。德与不德也,何今人有慕于鞅者哉!其惨刻寡恩,奸诈无信也,刑公子虔,亲至渭水阅囚,诛杀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哭声遍野,又外欺公子卬,为诈于诸侯,而天下多以谲诈相倾矣,赵良以德义劝之不听,新君与大臣皆怨之,卒遭车裂,多为不仁,而积怨于人,作法自敝,鞅之谓乎!不恤民之苦而为严酷之刑,己身亦遭之,悔何及也?勿为不仁以招人怨,勿为苛政以为己敝,其以鞅为诫哉!鞅虽惨死,而其法犹行,使秦并六国,更行于天下,焚诗书,毁先王之道,堕礼乐,废三代之制,世之下,不复三代之风,鞅之死,人无之哀,其死非不幸也,而有余殃,秦亡犹余。曹操、诸葛亮、王安石、杨坚、武则天、朱洪武皆师其法,文革崇之以为伟人,父子相告,流毒之深,为祸之惨,不忍言也。君子所峻拒也。
儒家之法乃天下之公法,保民之法;法家之法乃帝王之私法,维君之法。或曰:无法家,我等安能于此争论?予曰:如若法家禁偶语,钳人言论,吾等诚不能于此争论矣。儒家光明正大,开诚布公,法家阴深诡秘,提倡君威莫测。法家之治至于霸道而已,桓文之霸也,其佐不过管仲而已,而仲尼曰仲小器,法家亦小器也,其末至于秦隋之暴,商鞅、韩非为之师,以偏邪之学,惨刻之法毒万世;儒家之治,帝王之道也,帝如尧舜,王如汤武,其佐者伊尹、周公,大贤大圣也,其流亦有汉唐之盛,孔子、孟子为之师,以大中至正之道,仁义之说泽万世。儒家法家高下立判,尊法贬儒者,何其悖哉!皆有雄才,光武尚儒而一统,复大汉之盛;曹操崇法而只为三分,不免魏晋之乱。法家之霸道亦以仁义为名,不过假之而已;儒家之王道为仁义,则诚之也。李宗吾曰:“读孔孟之书,满腔是生气;读申韩之书,满腔是杀机。”儒家推诚,待人如亲;法家多疑,防人如贼。儒家者,礼与德也;法家者,法与力也。礼非徒礼也,法在礼内,有德必有力;法则徒法也,礼在法外,有力未必有德。孟子光明俊伟,韩非阴深峻峭。
韩非入秦见秦王政,死于秦,扬雄曰:“《说难》,其所以死乎!”然哉其言也。观非之《说难》,何多虑说之难入也,多为揣摩之术,未闻道也。法家之人多不善终,商鞅车裂于秦,吴起肢解于楚,李斯腰斩,张汤弃市,皆当政者也。韩非未尝当政,唯著书,而亦为李斯所逼,饮毒而死,何哉?观韩非之书,多言阴谋权术,何其不正也!主严刑族诛,何其不仁也!虽未行不仁,而其言之流毒,以见赏于赢政,推行于李斯,而为天下之害,后世亦受其弊,则其饮毒而死,天之假手于李斯而先惩与!韩非《五蠹》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扞,以斩首为勇。”法者,所以治恶也,以为教,则善良与恶同治矣,吏者,所以治民,以为师,则文化为政所并矣,以斩首为勇,则长杀戮之戾气,惨刻哉!极权哉!不仁哉!李斯上书秦始皇曰:“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以吏为师,旷古未有,实为暴政,韩非言之,而李斯行之!焚书坑儒之祸,亦韩非《五蠹》有以启之也,曰:“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显学》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李斯之焚书,曰其以古非今,岂非源于韩非之说哉?韩非之言“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十仞之城,楼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之言亦为李斯所引,以阿二世而行督责,而秦政益暴,民益不堪。其诬尧舜禹为臣虏之劳,不足多也,亦为二世所引,以为极欲享乐之借口,甚哉其流毒之大也!韩非之死,非不幸也,立言偏邪之报也。君子立言,岂可不慎哉!岂可不慎哉!
让法家得势,疯狂起来,就是儒家的灾难,现在不少法家之徒也恶毒攻击儒家,且及孔子,还说儒生该坑,秦始皇坑的少了,还要再坑一次儒。对法家不能不警惕!牟宗三先生说:“要说儒家有敌人,那么最大的敌人就是法家。”法家有很强的暴力倾向,容易疯狂,容易邪恶暴力多在法家那里。几千年不变。儒法相通,
韩非曰:“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故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此法家之刚愎,不顾世非,独行其是,而为人怨也。法家亦欲救世,而峻激之过,防人甚深,治人甚严,强人从己,其所以为不仁也。以严刑重罚为治,哀怜百姓为危,必束民于严法之中,不信民性之善,防民如贼,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严者所以治吏也,非以治民,吏正则民亦正也,上行下效,风之自上至下也,吏之不正,虽用严刑以治民,而苟免无耻,岂能导民于正乎?激之且反矣。圣人治法,必逆于世乎?逆于世,顺于道德,世与道德相反乎?同于义而异于俗,俗与义皆相悖乎?盘庚迁都,虽逆民意,而多哓喻之,以平民心也。子产为政,民欲杀之,然当众怒之不可犯,则从众也。法家之刻,虽众怒之不可犯,犹强行之,不从者,杀之,如此之刚愎也!其所以招祸也,商鞅车裂,吴起肢解。王安石变法,曰:“人言不足恤”,亦与此同,其所以败也。逆难顺易,民心不可逆也,顺之,顺非徇也,顺民性之善,启之扬之,疏导之,使民自趋于正,孔子与民校猎也,民所不好者,则以礼乐化之,潜移默化以使之从也,岂强民哉!强之则为暴矣,为暴则不仁矣。法家以恶治恶,儒家以善治恶。以恶治恶,至于善亦与恶同治,而贼善矣;以善治恶,去恶而归善,扬善也。
儒家与现代民主之法以保民也,商韩法家之法,以维君也,防民如川,君以法制臣民,韩非《说疑》曰:“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自行动至言论及思想,皆在所禁制!君为人,而他人皆工具、牛马也!《外储说右上》曰:“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沉默退隐亦不容许!故焚诗书及百家言,坑儒士之祸,实有其势,非偶然也。韩非言之,而李斯决行之。《汉书·酷吏传》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工具耳,非本源也,法家治末不治本。穷于末而本失,法虽严密,不能止奸盗,法愈严,政愈乱。扬雄《法言》曰:“申韩之术,不仁至矣!何牛羊之用人也!”法家之待民,如畜生然,古人已论之。商韩去慈惠仁爱,绌文学。章炳麟《国故论衡·原道下》曰:“今无慈惠廉爱,则民为虎狼也;无文学,则士为牛马也”;“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过重集体,而轻个体,压制个体,岂以人待其臣民哉,犬马之也!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秦以天下臣民为犬马,甚乃草芥,天下胥怨而反之矣,秦之亡,无一大臣殉国者,二世之弑,子婴之杀,莫或之哀,非君犬马之,而以为国人之死,漠然不与乎?法家偏于国,为国之富强,而不惜奴使牺牲其臣民,不尊重人,以人为工具,儒家尊重人,杀人而取天下,孟子曰仁者不为,《礼记》曰:“虽负贩者,必有尊也。”以臣为股肱,视民如子女,爱护之不暇,何忍伤虐之乎?
韩非既深悉人性之恶,防人如贼,陈货于市,虽曾史可疑,父子且不可信,君主亦人也,其位最高,其权最大,最易为恶,何为不防?乃反更尊其位,强其权,如雷电鬼神,纵之任之,而肆其淫威,岂不危哉!岂不可惧哉!知防臣民,而不知防君,臣民易治矣,而君益骄,毒于天下而莫能治,后世之所以多乱也,民之所以多苦也。儒者知之,而以道制君,孟子以革命易位警君,董子以天命制君,屈君以伸天,程朱以天理正君,而郡县集权之世,难成其裁制,稍警其心耳。申韩之毒,骄君纵君,专制集权之弊,近代反思之,乃多归咎于儒家,舍魔鬼而攻人,申韩之毒,又于国初而极,舍商鞅、申韩而反儒之祸也,两者之书具在,何不分而观之?而哓哓于儒家者不息?
儒家讲究光明正大,开诚布公,鄙视阴谋权术,反对诡秘不测。或曰主道利周不利明,周者周密,暗秘也。荀子驳之曰:“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儒家以君为臣纲,为臣子表率,上行下效,有斯君而有斯臣,君安可不明,而幽秘以为不测,臣亦为诈使不可知也,推诚待人,则人信之,怀诈而使人,人将疑之。
韩非则背其师说,将君主神秘化,提倡君威莫测,阴秘不测,其《扬权》(扬权,扬君主之权也)曰:“主上不神,下将有因。神者,隐而莫测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测,则可因,故曰下将有因也。其事不当,下考其常。主事不当,则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较其非。若天若地,是谓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测者也。”主上不神秘,则臣下因君之情而为私,而欺君也,神秘,则莫测其由,不知其心思用意如何,不神秘,则可测其心意,而有因。其所流极,秦始皇闻有人言行踪,处死,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不悦。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人泄其语,案问莫服。而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决事悉于咸阳宫。赵高更让二世不要与群臣决事,幽居深宫享乐,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群臣希得见,以示其神,莫可测,随时可能触犯君主,人不敢谏言矣,此其弊也。韩非又曰:“主失其神,虎随其后。失神,谓君可测知,如臣能为虎,随后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将为狗。主既不知臣之为虎,臣则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阴谋其事。主不蚤止,狗益无已。臣既以虎为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则同事相求,皆为狗,益其朋党,无有已时也。虎成其群,以弑其母。母,则君也。既朋党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必见弑。……探其怀,夺之威。探其怀,谓渊其心知其所欲为。主上用之,若电若雷。威不下分,则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电也。主上用之,若电若雷。威不下分,则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电也。”以臣喻狗,权臣喻虎,不当使知,威不下分,如鬼神雷电之可畏,“君无为于上,臣悚惧乎下”,君威极矣,何其防臣而为君也。虽然防人之心不可无,然太过防备,君臣相隔而不相亲,土崩也易。王船山疑问申商之言何为至今不绝?以申商之术乍劳而长逸,故君相乐用之,细读其书,都站在君主立场上,如何强化君权,统治臣民,非仁义之君,莫不喜其法术也。人称韩非集法术势之大成,法者所以治民,术者所以驭臣,势者加强君主权势,集权独裁。法严而民畏顺,术暗而臣不可测,势强而天下莫敢违。
牟宗三称之为“物化的治道”,曰:“(一) 顺抬高君权,君主专制的政体走,而言君术,神秘莫测之术;(二) 以道家之道为体。商鞅言法,申不害言术,韩非俱以为不足,必须法术兼备。这也是一个发展。心肠硬,理智冷,本是不自觉的天资气质,并未就此于人性上追论出一套理论或原理。但韩非就此而普遍化之,先反贤,反德,反民智,反性善,进而反孝弟,反仁义礼智。如是人性只成一个黑暗的,无光无热的,乾枯的理智,由此进而言君术。由乾枯的理智与君术,遂把道家道家的道吸收进来以为‘体’。如是,心只成一个虚极静极而一无德性内容的玻璃镜子,以之运术而行法。道家的道,如前文所说,本是由破除外在的形式与人为的对待而显的一个浑沌,其中并无德性内容。故正好可取来以为法家之体。君在权位上本是个超越无限体,今复益之以无德性内容无价值内容之乾枯冷静的虚寂浑全之心以为神秘莫测之术府,则其为极权专制乃不可免。此神秘莫测之术府所运用之工具便是法。法本有普遍性与客观性,以及整齐划一性。然前期之法只限于共同事务领域之内,并未越其畔以笼罩划一一切。今韩非顺此普遍性与客观性之法扩化而笼罩划一一切。因为君的无限之术涵盖一切,而其工具又只是法。发于‘独’的术与广被于外的法穷尽了一切。术府中并无光明,所以法所传达的只是黑暗。而又反德反贤,反性善,反民智,则人间光明之根已被抹煞。如是整齐划一之法由术府中压下来而昏暗了一切,亦即化了一切。如是,人民只成了‘物民’,刍狗黔首,在今日就说是机械系统中的一个螺丝钉。韩非之教是极端愚民、独裁、专制之教。秦政、李斯实行这种思想的政策,就是焚书坑儒,反历史文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大败天下之民。其自身亦不数年而亡。此后二千年无用此道者。不图又重见于今日,复活而为工铲档。”申韩之术,阴魂不散,历代相沿,或深或浅而已。其失也物,视人如物,牛羊之,犬马之也。
韩非重法而薄慈爱,所引秦昭王,实乃极端功利主义者,曰:“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入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毁也,罚之也。夫非令而擅祷者,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复与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塞祷。郎中阎遏、公孙衍出而见之曰:非社腊之时也,奚自杀牛而祠社?怪而问之,百姓曰:人主病,为之祷,今病愈,杀牛塞祷。阎遏、公孙衍说,见王,拜贺曰:过尧、舜矣。王惊曰:何谓也?对曰:尧、舜,其民未至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杀牛塞祷,故臣窃以主为过尧、舜也。王因使人问之何里为之,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屯亦罚也。阎遏、公孙衍媿不敢言。居数月,王饮酒酣乐,阎遏、公孙衍谓王曰:前时臣窃以王为过尧、舜,非直敢谀也。尧、舜病,且民未至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杀牛塞祷。今乃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10,臣窃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于此?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吾释势与民相收,若是,吾不适爱,而民因不为我用也,故遂绝爱道也。
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着、谓草木着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蓏蔬枣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
君民不可相爱,民为君祷,反罚之,如此不近人情!君民不以爱相与,而以法相制,君民相隔,民之视君也如雷电鬼神,只有畏,无有爱,民不可爱君,爱道伤法,君亦不可爱民,唯有功受赏,有罪受罚,民讥而不济,济则无功受赏,为乱道,何其忍哉!然则君之视民,如牛马工具而已,岂圣人子元元之意哉!牛马饥,牧者且与之食,民饥而不与,且不如牛马,纯以功利,不行爱惠,秦昭王之冷血,法家之残忍,何至此乎?将爱惠与法对立也。不知德阳刑阴,天地不能独阴而无阳,国家岂可偏用阴道?爱惠人情,人之相与,所以合人群。赏罚国法,国之治具,所以维治安。并行不悖也,奈何重法则去人情?用赏罚则去爱惠乎?法家统治下,造成的必是一个残酷无情,机械而无人性的的世界,于此可见一般矣。
韩非《解老》曰:“爱子者慈于子,重生者慈于身,贵功者慈于事。慈母之于弱子也,务致其福,务致其福则事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明,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慈于方圆者不敢舍规矩。故临兵而慈于士吏则战胜敌,慈于器械则城坚固。故曰:慈于战则胜,以守则固。夫能自全也而尽随于万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尽之生也,若以慈卫之也。事必万全,而举无不当,则谓之宝矣。故曰:吾有三宝,持而宝之。”老子言慈,韩非释之矣,亦知慈之用矣,又何曰“严家无格虏,而慈母有败子”,非慈惠乎?为寓言曰:“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问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韩非自相矛盾。盖徒释老子而已,而不取老子之慈也,取老子南面之术耳。
韩非又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是以明主不怀爱而听,不留说而计。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测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阴密。天则不非,既高不测,谁能非之?鬼则不困。既阴密,谁能困之?势行教严,逆而不违,虽#16逆天下不敢违,此势之用也。毁誉一行而不议。毁誉一行,而天下不敢议。故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是谓赏同罚异。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禁诛于私。家不害功罪,赏罚必知之知之道尽矣。”
人之悦于慈惠,亦人情也,何为去之?唯以好利恶害为人情也,赏以诱之,罚以畏之,视人皆小人也。此言人主之用人如鬼,如鬼之阴密,高不可测,何与儒家之光明正大相反也?韩非《八经》亦曰:“韩非八经曰:明主其务在周密,是以喜见则德偿,怒见其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奸无所失。”
老子言虚静,道也,于韩非变为驭臣之术,其言主道曰:“道者,万物之始,物从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纪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纪。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纪以知善败之端。得其纪,其端可知也。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称之。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君见其意,臣因其意以称之。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好恶不形,臣无所效,则戒而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则臣智自明。去贤而有功,去君贤则臣事以功。去勇而有强。去君勇则臣武自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浮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用臣智,故智不穷。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君虽不贤,为贤臣之师。不智而为智者正。为臣之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劳,以为己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经,常法也。
道在不可见,君道必使臣不可见也。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各令守职,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则自尽矣。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执柄固,则人意望绝也。……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羣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暧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罪则奸人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观此,而知太史公以申韩与老子同列一传,诚有以也。
韩非主张严刑重法,彼不信人性之善,所接触者多为阴暗罪恶,以此度天下之人,皆有可能为奸,唯严刑重法可以治之也。又见春秋战国多篡弑奸乱之臣,而劝人主不可信人,曰:“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孔子曰不亿不度,不先疑人,亦不为所欺,韩非纯粹猜疑,而不信,亦甚偏矣。君不可信人,则疑人,防人,一切以机心相防,不亦累乎?君无心腹,皆当防之,则必疏之,不可亲,不亦孤乎?春秋战国多乱臣,风俗之坏也,岂无忠义之臣,而皆不可信?韩非言不可信之由,曰:“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慠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大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者,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酖毒扼昧扼昧,谓暗中绞缢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故曰: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韩非言君臣,势力相交耳,非仁义相与也。此其重势力而轻仁义也。于此言也,妻子之亲,且不可信也。商臣弑其父楚成,父为废立而激其逆,非子皆枭獍而不可信也,晋献公不信其子申生而杀之,晋以乱,岂信为患乎?韩非之言甚偏矫,纯以恶意,利害之心揣测人,而诫人主不可信人。导君猜疑其妻子大臣,君臣益疏,帝王夫妻父子益疏,以戮臣戕妻杀子,抑何甚哉!不在信不信也,在其人之贤不肖也。贤则何为不可信?信贤臣,国之福也,信奸臣,国之殃也。只可曰患在轻信人,而非患在信人。轻信臣,易受其欺,臣皆不信,有善言忠言亦不入矣。
韩非主张严刑峻法,不信人性,盖由战国之环境风俗极端黑暗无道乎?然春秋弑君弑父者亦层出,孟子亦战国人,孔孟为何对人性充满信心,而倡仁义,仁政,省刑罚,薄税敛,言性善,恭宽信敏惠,荀子虽对人性失望,犹曰可化,化性起伪,亦言仁义礼乐,此气质之异也。吕坤《呻吟语》曰:“尧、舜、周、孔之道,如九达之衢,无所不通;如代明之日月,无所不照。其馀有所明,必有所昏,夷、尹、柳下惠昏于清、任、和,佛氏昏于寂,老氏昏于裔,杨氏昏于义,墨氏昏于仁,管、商昏于法。其心有所向也,譬之鹃鸽知南;其心有所厌也,譬之盍旦恶夜。岂不纯然成一家人物?竞是偏气。
“孔子一团太和之气,孟子阳刚浩然之气,申韩阴惨之气。司马迁说商鞅天资刻薄,有些人天生心肠硬,理智冷,韩非亦然,又逢战国极无道之时代,风气所影响,而以恶治恶,反德化。有些人则天性温和,虽逢无道,不改其善良仁义。且孔孟家庭教育好,皆有贤母,接触的多是仁人君子。韩非生于诸侯世家,为公子,看到的多是小人,虽从学于大儒荀子,而受其性恶之启,更怀疑人性。申韩惨激之学,一由气质之偏于阴,冷硬,二由于环境之甚恶,黑暗太多,读其书,满腔杀机,与孔孟之生气相反也。
韩非亦反对暴政,曰:“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不可先以爱养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12权筴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予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也。”
以仁暴皆亡,误矣,彼以姑息为仁,不知仁之道,故薄仁义。老庄申韩皆薄仁,老庄以煦煦为仁,申韩以怜爱故息为仁义,皆从柔软理解仁,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则仁以刚为体也,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孔子又曰仁者必有勇,仁者意志刚毅,责任心重,勇于担当,不惧死亡,孟子言浩然之气,配义与道,至大至刚,爱人利误为仁,惩恶除暴亦为仁,姑息养奸,仁之贼也。慈惠者,仁之一部分,而非足以为仁,不忍,不忍于无辜善良,君子好善恶恶,非对所有人不忍,惠者,以对贫困,不是对所有人都施与,施与亦有度。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仁道大矣,夫子所不敢居,亦不轻许人。韩非所谓仁义非儒家所谓仁义,彼只知此等“仁义”,而未知君子之仁义,此所谓不及也,何为薄仁义哉?其倡严刑峻法,亦过矣,严以治吏,宽以教民,宽严有度,严过则刻,宽过则纵,韩非偏尚严刑,而为刻,刻则近于暴,鲜不流于暴也。韩非又曰:“古人极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珧,蜃。以蜃为铫也。即推轮也。上古摩蜃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然则韩非非反仁义也,以仁义用于古而不可用于今,当战国大争之时,唯可用力。不知仁义常道,不可须臾无也,战国亦当义战,乱世亦当有仁法,仁义以合人附民,非无用于战乱之世也。又曰:“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则以太平之时养儒侠,战乱之时,则用甲胄之士。秦已定天下,仍战国之法,悖矣,马克思言阶级斗争,亦于乱世,毛复用于天下已定之时,亦悖。商鞅之法,申韩之术,猛药也,唯战国时代可用之,太平时代用之,未有不招怨天下而亡者也,唯战国有如此之说,极端年代而有极端学说乎?
皆曰李斯劝秦始皇焚书焚儒,流万世骂名,而鲜知商鞅作始劝秦孝公焚诗书也,韩非于书称“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观《商君书》,亦多反《诗》、《书》之语,农战篇曰:“《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去强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靳令篇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呜呼!诗书礼乐皆反,以为无用,以为弱国,驱民于农战,何其悖耶!商鞅亦学于名儒尸子,而反儒,儒家之逆子也。尸子之有商鞅,亦犹荀子之有李斯乎?商鞅作始,行于秦,李斯极之,令于天下,鞅车裂,斯腰斩,皆绝其后,何其惨哉!毁先王之道,焚经书,非不幸也,天假手于惠王、胡亥以行天诛与!
有人讥笑汉元帝用儒而弱汉,明惠帝之仁弱,尚儒,也被成祖篡位,汉元帝虽崇儒,而不知儒学之精意,用的儒也非真儒,然西汉之衰肇于宣帝,成于成帝,非可咎于元帝,元帝中才柔仁之主,而非昏虐之主,元帝之后,还持续了五十多年。光武崇儒而中兴大汉,又当何说?明惠帝仁弱,遇成祖之雄鸷而败,然亡于同宗,总比亡于外姓好。惠帝之亡,殉国之臣甚多。崇尚申韩法家的秦二世才是千秋笑柄,偏任赵高,杀戮兄弟宗室大臣,指鹿为马而不知,两年多就把家底败光了,求为黔首不得,大臣多被杀了。秦朝之亡,无一殉国之臣。
始皇失道,大臣无一谏者,秦法严,始皇骄愎,无敢谏也,焚书坑儒,只有扶苏入谏,被贬去边关,为蒙恬监军。二世失政,李斯谏之,而二世且引用韩非之言指责李斯道:“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於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韩非之言成为二世自尊逸豫享乐的借口,不自责,而皆责大臣。法家不责君,一切责臣之过也。于是遂囚李斯,杀之。赵高要杀二世时,二世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愎谏,讳疾忌医之过也。又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馀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讳疾忌医如此,此秦之失道而无臣敢谏也。叔孙通面谀二世,事汉高,则谏汉高易太子,事惠帝,谏惠帝勿乘宗庙道上行,主之明,法之宽也。高帝囚系萧何,王卫尉谏之,高帝释之。高帝辱周昌,问我何如主,昌直称高帝为桀纣之主,高帝笑之而不杀,以此惮昌。高帝宽大,忠臣敢谏,此汉之所以兴也。秦帝严苛,大臣不敢谏,此秦之所以亡也。贾谊《过秦论》曰:“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法重,作法自敝,商鞅之不免于车裂。秦法之敝,于秦始皇亦见矣,史载荆轲刺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当时秦始皇何其狼狈,而无臣敢持剑救之,秦多忌讳,不能持剑上殿也,以防被刺,而不知刺客上前,无人敢救,荆轲剑术疏,而秦王得免耳,不然,殆哉!至于君主被人追杀,都不敢持剑救之,法之拘也过矣!故政以平易为上,威严之过,人皆离心涣散矣。虽有忠者,不敢近前也。
法家除了政治就是政治,法家是最功利,最残忍的,其理智很冷,心肠很硬,盖其眼里只有政治,亦由气质之偏于此也。法家其失也物,佛家其失也鬼。法家惨刻,佛虚寂。法佛皆儒家之大敌。法家政治与儒家相反,佛家人生与儒家相反。佛家阴柔,法家阴狠。儒家讲伦理人生天道,非偏于政治,法家只讲政治,难他没什么人生观?人生的情趣么?法家讲伦理,也是归于政治,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妇,是绝对服从。
韩非不相信人,以为父子之间且不可信,奈何相信同门李斯?而为李斯害死!
近代儒为天下垢,流言儒家愚忠,为君主服务,甚误解儒家也,儒家之忠合义,不合义之忠,固非儒家所许也,儒家人学,人所由之之道,君主者,所以领袖人群,荀子曰:“君者,群也。”岂偏为君主哉!儒家不愚忠,不为君主服务,若说愚忠,百家莫法家若也,实以君主为中心,为君主服务者。合儒法两家之书观之,可见也。孔子曰:“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则忠之前提,为君能待臣以礼也,非如法家之偏,唯臣事君以忠。鲁定公前用孔子为大司寇,孔子尽忠,至于受齐之女乐,而怠政,不礼孔子,孔子乃去鲁,游列国,孔子愚忠乎?孔子又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美尧舜之禅让,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汤武以臣伐君,以君主无道,暴虐百姓也,尧舜禅让贤圣,天下之公也,贬天子,退诸侯,疾时君之昏也,君有禅有革有贬,岂忠于一姓?岂忠于暴君?岂为君主服务?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则忠者,非独为君也。孟子之言尤烈,其对齐宣王,曰汤武伐桀纣,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残贼之人,不可复视为君。又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固以民为重,民者所以保民安民,害民者去之,君源于民,非民戴之,何能为君。孟子又谓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臣民非君之仆隶也,无道之君,可以去也,此言岂有愚忠乎?此警告君主也至矣,岂为君主服务乎?明太祖读此,怒而削之,欲贬孟子,固触独裁君主之忌也。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多责君,要求君主也。
荀子亦驳世俗谓汤武篡夺桀纣之说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 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圣王没,有埶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弒,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为君,则天下未尝合于桀纣也。然则以汤武为弒,则天下未尝有说也,直堕之耳。”其曰诛暴国之君如诛独夫,与孟子同。又曰:“上下易位然后贞。”非法家之所谓冠履之不可易也。
其《子道》篇曰:“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尧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命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故劳苦、雕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非仁人莫能行。诗曰:‘孝子不匮。’此之谓也。”孝子有三不从命,愚孝乎?从道不从君,愚忠乎?盲从君命乎?又引鲁哀公与孔子之对话曰:“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子贡以臣从君命为贞,子从父命为孝,孔子斥曰小人无识,当审其所以当从。皆反对盲从,反对愚忠愚孝也。
董仲舒之《春秋繁露》曰:“屈君以伸天。”其言春秋之法,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进退不由君命也。以天命制衡君权,曰:“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故封泰山之上,禅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明言无道之君可以伐,立王以为民,不可贼民,革命之思想继承孔孟荀,何尝愚忠?岂为君主服务?明末大儒王船山曰可禅可继可革,唯不可世夷类间之,曰一姓之存亡,私也,百姓之生死,公也。儒家为公不为私。
若法家则强化君权,神秘君主,教君如何驭臣驯民,多为君主服务,君臣绝对,只要求臣忠,而不要求臣如何礼待臣,体恤臣民。于《商君书》、《韩非子》可见一般。商鞅教君重刑以治民,禁民之迁徙,曰:“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昌言愚民:“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其所以反智反文,使民皆为农战之工具。又弱民,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民,善之则亲,利之用则和;用则有任,和则匮;有任,乃富于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奸多。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弱,则易统治也。
韩非教君主如何驭臣,防臣:“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羣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罚,则民畏臣而轻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赏,则民归臣而去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又曰:“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言,名也,事,则也。言事则相考则合不可知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不当名之害甚于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为罚。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寝寤而觉。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守业以当官,守官以当言,如此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扬权》曰:“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昼夜四时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节,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则病形;皓曼所以悦情也,耽之过度则捐精;贤才所以助理也,用之乖宜则危君也。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谓臣民,中央谓主君。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倡君主独裁,曰:“用一之道,以名为首。一,谓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其唯正名乎,故曰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见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见事,则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则自举其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因其事以与之,彼则自举之。正与处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举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从而以名举之,则刑名审矣……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道德不与物宁,而物自宁。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言当因道以考汝报命。而,汝也。死生,犹废兴也。谓其教命时可废则废,时可兴则兴也。参名异事,通一同情。参考异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于万物,故能生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故能成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故能知其轻重。绳不同于出入,故能正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故能均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故能制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道以独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下当陈其名言以祷于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言君主独尊,异于群臣,如道之不同于万物。《主道》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称之。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君见其意,臣因其意以称之。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好恶不形,臣无所效,则戒而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则臣智自明。去贤而有功,去君贤则臣事以功。去勇而有强。去君勇则臣武自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浮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用臣智,故智不穷。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君虽不贤,为贤臣之师。不智而为智者正。为臣之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劳,以为己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其为驭臣防臣亦至矣!
《有度》曰:“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则军旅不敢辞难,朝廷辞贱,则下有缺上之心。军旅辞难,则事有偷存之志。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为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视,为君视也。”“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非愚忠而何?儒家讲君有诤臣,君有过则谏,君之乱命不可从,法家则只教臣顺从,高下立见矣,何为诬儒家愚忠耶?
韩非《忠孝》又曰:“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此则非汤武为弑君,诋尧舜、汤武皆为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与儒家美尧舜禅让,赞汤武革命相反,君虽有桀纣之暴亦不可反,以为冠虽敝,必戴于上也,与孟荀诛暴君如独夫何相异也!孰为愚忠,孰为君主服务?彰彰见矣。《礼记·儒行》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若法家于此等清高之人则杀之,韩非曰:“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为寓言曰:“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褥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正,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皆要为君主服务,不能不听使用,法家尊君也至矣!
奴性始于战国法家,臣者,君之辅弼也,可进可退,孔子言事君不得志则去,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君,孟子亦曰不合则去,其于君命,孔子曰命顺则顺,命逆则逆,孟子以友视君,君亦友也,非亢之不可议也,曰责难于君谓之恭,说大人则藐之,又曰君有不召之臣,有德之臣,君之师友也。荀子亦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君臣虽为上下,而亦为一体,其人格等也。吴起虽功利之士,亦对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险。”以臣莫如己者危,抑君之骄也。自商鞅毁孝悌以使事君,而臣道卑矣。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雎,命之以天下为桎梏。”李斯曰:“行督责之术,然后绝谏争之路。”而君多骄恣矣。韩非曰:“贤者之为人臣……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为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视,为君视也。”则臣如奴仆之顺君而不可议也,非臣也,奴也。又曰明主不务德而务法。又曰:“道不同于万物,故能生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故能成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故能知其轻重。绳不同于出入,故能正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故能均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故能制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道以独为容。”岂徒以法毒天下哉!亦亢君卑臣,为专制独裁张目也。
君臣,义也。儒家以为君臣以义合,而在韩非眼里,君臣全成了势力,以势合,他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臣是惧怕君主势力才不得不事。君臣之间不能信任。不能信人,只能威之以势,以权术相驭,在韩非之学,就是法术势,没有义。此其重术势之故也,而于术尤重。
就是夫妻之间也不能信任,他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儒家的推诚之道在韩非哪里是根本没有的,韩非看世道政治非常黑暗,因此反对仁义慈惠,认为只有法术势才有效。
韩非以人性好利,他为君主安全这样着想:“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与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因此对妻、子,大臣都要小心防备,曰:“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晕围於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
韩非还直说:“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君臣之间就是互相计算的,“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因此要“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申韩法家就是不好处看人性,所以提倡严刑峻法。
韩非是尚法不尚贤,重术不重道,然而韩非所讲的术,也不是一般人能学习的,胡亥自小习于韩非之书,看他引用韩非之言驳李斯,为人君当享乐的借口。刘禅也自小受申韩之教,按刘备对刘禅遗诏曰:“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刘备被称为仁君,三国正统之君,却以商君书,申韩之偏邪惨刻之书教子!然而胡亥弑于赵高,刘禅降于司马,申韩之效,又焉在哉?有些智商的君主,学习申韩,阴惨刻薄寡恩矣。其有智者如曹操,杨坚,武曌师之亦不长久。用申韩而得令名者,不过刘备,诸葛亮耳!王道易易而久,虽有庸君,能温仁守成,亦能安而不亡,霸术繁难而促,虽有雄君,亦难免于亡。
韩非《解老》曰: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无术者,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虚,则德盛;德盛之为上德。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
韩非如此发挥老子的虚静无为,发扬道家的无为,就是无不为,独裁统治!看似什么都不做,却把什么都控制好了。虚不是为了虚,虚是让人摸不透,不让人知,意无所制,而实皆制之。这是法家的术,术是无为的,看似无为的,是隐性的,法是有为的,是显性的,术示人以无为,强调严刑峻法,而无不为,什么都干涉。老子的无为无不为,就被韩非如此发挥为阴深的帝王权术了。
韩非《主道》: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
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韩非笔下,君主装得神秘莫测,什么事都不做,却让群臣悚惧而莫敢不从。无为真是一种权术啊。“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这种权术对君主很有利啊,无为而治,有功,就称颂君主之贤,无功,就把臣当替罪羊!真高明,但不道德啊!
王船山很疑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众怒之不可犯,众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为至今而不绝邪?志正义明如诸葛孔明而效其法,学博志广如王介甫而师其意,无他,申、商者,乍劳长逸之术也。……任法,则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则天下逸而人主劳。”申韩者,专利人主者也。逸己劳人,任法不尚贤。
儒者为何要距申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只是因为申韩严刑峻法,还有申韩的险暗,提倡一些阴谋权术,坏人心术,一些君主政客看了这书,学了这个,就拿这套去控制人,去整人。先儒距之,而未公开其权术,今可公明之。
一些人指责荀子流为申韩,其实荀子是纯正的儒家,和申韩大不同,他反对阴秘之术,主张君主为天下仪表。荀子曰:“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君主要为万民表率,上梁不正下梁歪,反对道家法家这种说法批评,曰: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
荀子又曰: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这和老子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针锋相对!儒家要明之,道家要愚之,儒道相反也。
和韩非的“君无为于上,臣悚惧乎下”,也是一种对立,荀子反对那种阴谋权术,让臣下害怕自己。
儒家君臣之间是温情脉脉,君臣如父子,或如师友兄弟,而道家,则君主显得神秘莫测,岂可亲?法家,则更诡秘莫测,如雷电鬼神之可畏,岂可爱?
秦用申韩之术,却二世而亡。
秦始皇居住隐秘,史载: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阳宫。
他儿子胡亥也读申韩之书,赵高就劝二世居住深宫,不要与群臣相见,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而二世最后被赵高逼弑而无人救。
真是君以此制臣,臣亦以此制君!君主还是要光明正大的好,玩神秘,迟早会出问题。
读商鞅传,感商鞅之刻薄,读商君书,更觉商鞅之邪恶。唐虞三代莫不以正治国,而秦始以邪,商鞅导之也,莫不劝人以善,遵道行德,而商鞅反善,反道德仁义,公然而不掩。
商鞅之反对道德文化,盖以为无用,纯粹功利强国,彼曰:《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商鞅又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甚矣其言之悖也!三代以善民治奸民,而商鞅倡导“以奸民治善民”,为强其国,不顾道德,颠倒善奸,故商鞅变法,成秦为奸诈之国,狼兵酷吏盛于秦也!
商鞅又曰: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其反道德之言甚多,彼意以为当以恶人治善人,以奸诈之人统治国家,国家才强大,其言之荒悖,诚旷古绝今矣!“不仁者在上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何商鞅之反善而用恶乎?秦终亡于任奸,反道德,而纯用奸诈,未有不遭其反噬者,赵高之奸,亦可谓空前,惊骇古今矣!
商鞅还有个奇葩的逻辑!他说民贫则弱,民富则淫,就要“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赵高就是劝二世:“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然而秦二世而亡,虽赵高导胡亥以淫暴,溯其源,则商鞅之术,固如此也。
《商君书·去强》:国
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以奸民治善民,商鞅这是什么用心?商鞅要排斥诗书先王之典,排斥礼乐,否定孝悌,实为反文化反文明反道德!商鞅这句“以奸民治善民”,真是邪恶!要用奸诈的坏蛋管理那些善良的民众,民苦矣!鞅之不仁也!
“以奸民治善民,必治至强”,商鞅认为要用奸诈的人管理善良的民众,国家就必定强大,也就是用狼性管理,彼盖以恶之力量强于善之力量也!商鞅变法就是释放发挥恶的力量,让百姓士兵如虎狼般杀敌,然而民风败坏矣。
《商君书》有篇《弱民》,讲弱民,贫民,辱民。商鞅把国与民对立,他直接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对民众的压迫,赤裸裸,毫无掩饰。弱民,就是让民众没有独立的意志,没有反抗的意识,只充当君主的工具。君主让民众干什么,就干什么,好比机器一样。商鞅弱民,就是驱使民众为国家的耕战机器!
儒家提倡富民,孔子说对民庶之富之而后教之,荀子曰:“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孔子弟子对鲁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而商鞅则怕民富,而要贫民,他说:“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商鞅变法,要贫民辱民,他的逻辑是:“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商鞅还说国不能行善,行善则多奸,商鞅的国就是朝廷政府吧。商鞅的“国”是让百姓畏惧的。民一切为“国”服务。
商鞅驭民之术,这段最体现他的狰狞可怖,阴险卑鄙:“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
他的意思就是,对民众要羞辱他们,他们才以爵禄为贵,削弱他们,他们才尊敬官员,让他们贫穷,他们才重视赏赐。对人民从人格上羞辱,意志上削弱,经济上剥削。就好统治驱使民众了。他说,如果人民自尊,有个人荣誉感,则看不起官员,人民富裕,则轻视赏赐,所以统治人民,就要用刑罚羞辱他们。商鞅变法,严刑峻法,百姓稍有不慎,就会受刑。
商鞅为此,提倡刑多赏少。《商君书.去强》曰:“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如此赤裸裸地鼓吹控制压迫民众,古今以商鞅为烈矣!商鞅刑九赏一,这是要多用刑罚让人民恐惧啊。商鞅的国家多用来惩罚刑罚民众。重罚轻赏,刑九赏一就是商鞅的治民之术!这种治民,百姓是时常生活在恐怖中。百姓自然挨刑罚远远过于赏赐,受罚之酷也远远过于赏赐。难怪秦法行于天下,十几年,人民就受不了了。实源于商鞅之法也!只有虎狼之秦才会接受,才会实行。
商鞅变法强秦是以牺牲人民幸福的代价,压榨人民,把人民当做牛马机器,驱使全民为他的农战机器!
商鞅曰: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政治要做百姓所恶的事,民就弱了。严刑峻法,重役杂税,就是民之所恶。
法家的君主阴秘莫测,是让臣民恐惧的:
邓析:君者藏形匿影,群下无私,掩目塞耳,万民恐震。
韩非: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
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
君主如雷电让人害怕:“探其怀,夺之威。主上用之,若电若雷。”(《韩非子·扬权》)
提倡君主周密不测:“明主,其务在周密。是以喜见则德偿,怒见则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韩非子·八经》)
提倡重罚轻赏,刑多赏少,让人民恐惧:“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商君书·去强》)
加重刑罚:“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韩非子·饬令》)
这种奇葩法律太恐怖了,不告奸的要被腰斩。人民没有沉默权,沉默者也要腰斩!父母有罪,也要告发父母,不告,腰斩!子告父,弟告兄,妻告夫,人伦颠倒矣。
贾谊《治安策》: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于,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没有人伦了。商鞅法行,对人伦的破坏是巨大的,夷人道于禽兽!
韩非曰:“道在不可见,君道必使臣不可见也。用在不可知。”“主上不神,下将有因。神者,隐而莫测其所由者也。……神隐不测,故下不能得之,治道无踰此者,故曰治之极也。”“明主,其务在周密。是以喜见则德偿,怒见则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提倡君主当神秘莫测。
这与儒家提倡君主当光明正大,开诚布公相反。荀子就反驳主道利周,他说: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儒家以为君臣当相亲,而非法家君主使臣感其如虎狼鬼魔之可畏也。君主玩弄权术操控大臣,大臣就不会玩弄权术糊弄欺瞒君主?无法猜测君主为何意,感觉难伺候,担心君主杀己,他就与党羽合谋弑君矣。荀子说君主让臣下恐惧,这个君主就危险了!君主的危险莫过于让臣下害怕害怕你,就疏远你,就猜疑你,君臣相疑,安能无变?故不测之威,君子所不取也。
曹魏儒士杜恕《体论》就批判这种权术:商鞅、韩非、申不害者,专饰巧辩邪伪之术,以荧惑诸侯,著法术之书,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于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奸说。此听受之端,参言之要,不可不慎也。元首已尊矣,而复云“尊之”,是以君过乎头也;股肱已卑矣,而复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过乎头而臣不及乎手足,是离其体也。君臣体离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闻也。且夫术家说又云:“明主之道,当外御群臣,内疑妻子。”其引证连类,非不辩且悦也,然不免于利口之覆国家也。何以言之?夫善进,不善无由入;不善进,善亦无由入。故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何畏乎驩兜?何迁乎有苗?夫奸臣贼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尝不有也。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未知奸臣贼子处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独立,是无臣子也,又谁为君父乎!是犹髠其枝而欲根之荫,揜其目而欲视之明,袭独立之迹而愿其扶疏也。
直中商鞅,申韩法家要害。批判法家尊君卑臣,是让君臣离体。儒家是主张君臣一体,君如元首,臣如股肱,君当视臣如手足而亲之。法家尊君卑臣,君臣相悬,导人主以卑贱猜防其臣,这是正统儒家非议的。责法家申韩利口覆家,因为申韩导人主猜防其臣,君臣之间没有信任了,君臣关系紧张。
他说法术不可恃,君主以术驭臣,臣就不会术对君?以独制多,必不胜也。
其言曰:人君之数至少,而人臣之数至众,以至少御众,其势不胜也。人主任术,而欲御其臣无术,其势不禁也。俱任术,则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
君主可以一时玩弄臣下,受其操控,岂能长久?君主智商未必如臣下,晋元帝用申韩之术对付权臣王敦,只是激敦之反,攻陷京城,将元帝幽禁而死。宋文帝直道而行,公然表示他的悲怒,则铲除权臣谢晦等人。申韩那套权术,只有少数智商高的君主玩的好,一般君主玩他,只把自己玩死!
一个人太让人恐惧,毛骨悚然。这个人也是危险的,人害怕虎狼,也有捕杀虎狼的猎人,人害怕蛇,有些人就想着铲除蛇,因为你的异类性。故儒家反对阴秘之可畏。君子之可畏,乃是可亲可敬而可畏也。人畏其义,而非畏法家君主之不可测,提心吊胆也。
法家就是狼,对弱者表现凶残,对强者表示奴性。儒家关怀弱者,又不畏惧强者!挑战强者!讨伐强者!战胜强者!儒家是龙!
法家人物几个善终的?吴起被人刺杀,商鞅车裂,李斯腰斩,韩非饮毒,张汤被斩首,来俊臣被斩首灭族。作法自敝!儒家著名人物都是善终的,孔曾孟荀都活到七八十岁,安然正寝。
儒道家人物都善终,就法家人物多死得惨!车裂,腰斩的酷刑,灭三族。法家人物惨刻寡恩,对人惨,下场也惨。
韩非没当过政,也饮毒而死,李斯嫉妒韩非的聪明才学,把他毒死。法家同门相残!亦莫如法家。韩非自身都不能保全,他写的那些东西,只是为秦王,李斯所用而已!韩国却先亡了。崇尚法家权术的韩国最先灭亡。可见用术者,其尤危乎?秦这样的强国,用申韩之术,也十三年而亡。
王船山曰:曹操之雄也,申、 韩术行而驱天下以思媚于司马氏,不劳而夺诸几席。诸葛孔明之贞也,扶刘氏之裔以申大义,申、韩术行而不能再世。申、韩之效,亦昭然矣。
崇尚法家的都不长久!
韩非曰道在不可见,法家的道,是不能公开的,不能光明的。其实仍是术。道只能让君主看见。
韩非之法,也不是纯粹的法了,参杂了太多权术。韩非之学,术多于法。可言术家,法术家,韩非好言法术之士。跟李悝之类的法家不同了。春秋战国初的法家没讲那种权术。申不害开始讲权术,被韩非发扬。
儒家之臣,乃君之辅佐,匡君抚民,战国法家之臣则完全为君主服务了,成了君主的奴仆!如韩非《有度》曰:“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则军旅不敢辞难,朝廷辞贱,则下有缺上之心。军旅辞难,则事有偷存之志。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为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视,为君视也。”都是为君,而不为民,为天下,为道义,不就是君主的奴仆吗?
法家强调君主之威,而忽视德,法家君主如雷电之可畏,韩非有篇《扬权》的文章,就是扬君主之权,如何强化君主权力,君主要与众不同,独裁:“道不同于万物,故能生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故能成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故能知其轻重。绳不同于出入,故能正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故能均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故能制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道以独为容。”
君主要神秘莫测:“若天若地……天地高厚,不可测者也。”“凡治之极,下不能得。神隐不测,故下不能得之,治道无踰此者,故曰治之极也。”君主失其神秘,可测,就危险了,他说:“主失其神,虎随其后。失神,谓君可测知,如臣能为虎,随后以伺其隙。”
君主要如雷电之可畏:“探其怀,夺之威。探其怀,谓渊其心知其所欲为。主上用之,若电若雷。威不下分,则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电也。”
法家君主权术大概如此。
秦始皇好读韩非之书,就爱装神秘,史载:“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阳宫。”
然而崩于沙丘,群臣莫知,独李斯赵高知之,而矫诏废长立少以乱秦,向使正大以明示天下,斯高安能行其私哉?欲秘,而不可胜秘,终有知之,不若以明也。人君愈秘,人臣愈疑,而愈欲探测君意。光明正大,明吾好恶,臣自敬畏,何敢行私?
法家君臣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君主要时常警惕防备臣下夺权,韩非说:“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夫上位可宝,上利可贪,居下者常有羡欲之心,欲静则不能,欲取则不得,二者交战,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羡之心,常匿私以试上,故上必当操度量以割断其下也。”呜呼!导人主以猜防甚矣,虽防贼不至于此也!曰黄帝言,实寓言也。君臣一日交斗一百次,那这君主真够累的,几乎时刻和大臣勾心斗角。韩非之书出,而政治愈阴暗矣。
商鞅作法自敝,终车裂,当政者也,韩非徒著书,而未有用于政,然言权术太露,书出不久,而死于同门,世俗言李斯害之,固亦秦王疑虑畏而杀之也。术者,言之犹危也,况用之乎?秦用之,二世而亡,宗庙为墟。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陶扬鸿:辟法家集(三万字)发布于2021-07-06 00:1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