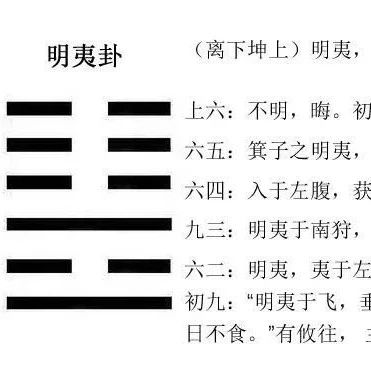怀帝
(一)
孔子曰唯名器不可假人。夷狄无称皇帝,称皇帝,立朝号者,始于西晋匈奴人刘渊,习汉文而假之也,辽、金以边荒之夷而僭称皇帝,立国号,汉族败类之士教之也,而夷狄乃以帝王自居与中国伉矣,且与中国争正统矣,甚至胡元胡清窃主中国,代中国之统矣,以君臣之义责我汉人而奴役之,使我中国忘其为夷狄贱种,而戴为君后不知背也;忽其为夷狄僭窃,而以为中华不知逐也。后世作史者亦无与正之,虽有正之者,而犹有不明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刘渊之族赤于靳准,固无后矣,而劝夷狄僭号,辅夷狄窃据者,可胜诛哉!
(二)
张宾自比子房,而佐胡将石勒灭晋,子房之所羞,岂子房之伦哉?子房为韩报仇,辅佐汉高灭暴秦,功成而退,张宾图一己之功名富贵,不择华夷,辅佐胡羯陷帝京。子房以仁伐暴,张宾导夷猾夏,相去远矣!盖以比子房智谋也,有智无义,奉异类以攻中国,不如其无智也。汉人之为夷谋臣,虽前有之,西汉中行说之事匈奴也,然寇扰中国,未至导之陷中国之都,执中国之主也,张宾其始矣!其后刘秉忠之辅元,范文程之辅清吞噬华夏,为祸愈烈。
自汉末以来,礼崩乐坏,俗趋功利,鲜闻道德仁义。建安以来,申韩之苛政立,士免而无耻;正始以来,老庄之玄风煽,俗薄而无节。曹氏之束缚,人畏法而不知有名义;司马氏之放纵,荡检踰闲,骄淫愞靡,廉隅益以荡然。故贾充之逆,公然助司马弑君,而不畏天下之清议,贾后之悍,以妇废姑,而不顾古今之伦理。董养曰:“天人之理既灭,大乱作矣。”司马氏、王浚延异类以相攻,名义廉隅之坏至此极矣。助奸臣以弑君,君臣之义失矣;导狡夷以猾夏,夷夏之防裂矣。在上者不知有夷夏之别而用夷相争,则士之无耻者,但为功利,而择主何分夷夏哉!故名义不可不讲也。孟子首言仁义,吕留良四书讲义亦多辨义利,以为华夷之乱,根在义利之辨不明也,未立足于义,可盗贼,可夷狄也。
(三)
刘聪陷洛阳,执怀帝,帝称臣受其伪封,使帝青衣行酒,百官无一死者,廉耻忠义于此荡然极矣!呜呼!帝不能逃,又不能以身殉国,安足以责诸臣之仗义死节乎?夷狄猾夏,虽自古有之,犬戎杀周幽王,未至如怀帝之称臣受辱也,而终不免于聪之忌害。夷酋悍暴无常,何如早自裁决,以免今日之受辱而死也!
而诸臣之碌碌,耽念洛阳之钱财,周馥请幸寿春而不听,苟晞请迁都仓垣而不果,卒至君臣皆虏。文武之恋财也,帝之贪生也,恋财而终不保其财,而更受其俘,贪生而终不保其生,而又受其辱。故君子有弃财以全人者,有舍生以取义者,明义理,而择轻重也。
愍帝
(一)
甚矣!好谀之患也,石勒之虏晋帝,杀王弥,反刘聪,天下孰不知其可畏?王浚之凶,乃受其巽辞所诱不备,为其所禽。王弥之忌石勒,而与之书曰:“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推戴勒之言也,而勒以其位重言卑,必图己矣,外示救弥而因酒醉斩之,其狡诈有甚于操懿矣。石勒之横行中原,而卑辞厚礼奉戴浚为帝,势强而言卑,亦弥之心也,何浚不察乎!好谀则不知虑也,不知防也。好谀由于自矜,非浚之自矜其强,勒之谀言又何能入哉!故君子之修身,去矜而守之以谦,则绝谀言之患。
(二)
帝王出降夷狄,始于晋愍帝,曰:“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偷生之借口也。犬羊之徒,乱我华夏,执杀中国之主,不共戴天,誓不与贼俱生者,凡中华士民皆有距之之责,守令降之,且为耻辱,况堂堂中华天子乎?夷狄岂不畏中国哉?人所胥戴之共主,一再为其所擒,则轻中国,以为不足惮也,夷狄乃极其猖獗以毒虐我中夏之人。
胡贼之无礼,出猎使帝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睹,多有歔欷流涕者,诚哉可悲也!天子且受辱于夷狄,而况下民哉!亡国之痛,此真痛矣!刘石乱华,诚中国之不幸也。刘聪又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执盖,晋臣在坐者多失声而泣,尚书郎辛宾抱帝恸哭,为聪所害。不久,帝又遇弑。帝王降夷,未有能免者也,徒受辱耳,梁元帝之降鲜卑,为魏人所害,宋徽宗、钦宗之降女真,亦受辱而死,蹈怀愍之覆辙,明隆武绍武之抗满虏,绝食自缢而不降,乃立中夏之节。
二帝被执,无一勤王之师,二帝被杀,无一报仇之士。司马叡之据江南,唯图偏安,奋勇北伐者,独祖逖、刘琨而已。呜呼!汉帝辨之弑,有关东聚兵讨董卓,魏帝芳之废,有淮南起兵抗司马。晋以老庄虚无毁廉隅,而节义荡然至此,天子为夷狄所执杀,而无奋勇以讨者。故周之犒京沦而旋复,秦晋起兵驱逐犬戎也,晋之两京乃至中原陷于夷狄达两百余年之久,当时诸臣忘仇观望也。
元帝
(一)
刘聪之死不久,子粲即位,听靳准言,杀宗室殆尽,旋又为准所杀,竟灭其族,毁刘氏二陵,斩聪尸,焚其宗庙,愍帝之遇害不过一年,而刘宗之遭祸也如此之惨。怀愍之恨,晋不能报之,天假奸人之手以戕夷狄之宗乎!刘聪未死,天降火灾焚杀其子矣,害中华之主,人所不忍,亦天所不佑也!
刘聪面讥怀帝骨肉相残,而己之骨肉相残更甚司马氏矣,聪已弑其兄和,使其子杀其弟乂。子粲之至愚,委权于靳准,胡亥之流也,靳准以女惑聪,并惑粲,杀害忠良,刘氏重宗,赵高之流也。准之受聪宠,何仇刘氏如此之甚?尝以为身为汉人,切齿逆胡,先陷事而后暗报之。迹其所以乱汉,有如赵高之乱秦矣,或曰高之乱秦,以高为赵人之后,欲报赵仇也,准之乱汉,以准为汉人,切齿胡人,欲复汉人之仇也。尽杀刘氏男女,掘刘渊、刘聪之陵,斩聪之尸,可见其于胡虏之仇恨也。既灭刘氏,称藩于晋,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嵩不敢受,准怒杀之。又遣使者膏司州刺史李矩曰:“刘渊,屠各小虏,因晋之乱,矫称天命,使二帝幽没。辄帅众扶侍梓宫,请以上闻。”而观拒准之王延骂准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杀我!”则准之杀刘氏,为匈奴屠各内讧,非为汉人复仇也。汉尚书北宫纯等招集晋人,堡于东宫,而其弟靳康攻灭之。其称藩送玺于晋,结晋为援以对刘氏余宗耳。准之掘其二君之陵,毁其尸,焚其庙,非特赵高之于赢氏也,骂曰“屠各逆奴”,盖其世为刘氏奴隶,受压抑甚久乎?非此难解也。
(二)
五胡乱华,北土沦于戎狄,既晋武帝之失策,八王之争,延异类以逞,而五胡未如金元满清齐心并力逼中国,相争相制,且二世之主多昏政,旋起旋灭,有英雄之主,聚豪杰之士,乘其内衅,收复甚易也。汉遭王莽之篡十五年,光武且能复之,况戎狄之不正愈于莽,分散之势不及莽之一乎?伸华夷之义,士必多归,人心必合,易于诛篡也。晋可中兴,而元帝无志无度,只成偏安,元帝之责也。祖逖有驱逐戎狄,恢复中原之心,仅给一千之兵,唯能与石勒相持。后祖逖立威河南,为石勒所忌,复以戴渊制逖,而逖不能尽意讨狄,又闻朝廷将有内难,郁郁而死。制王敦不以其道,而任刘隗、刁协刻薄之人,名为讨胡,实备王敦,逼王敦之反。岂但王敦欲反,朝臣亦多离心,不御敦之侵,王导为敦之弟,而不规劝敦,利敦之反以杀刘刁也。故敦之反,势如破竹,旋踵而入京城,挟制元帝,元帝忧死。
元帝不能望光武,且不如周平王,能任秦襄公驱逐犬戎也。平王之待秦襄,失之厚,感秦襄救周之功,以龙兴之地西歧赐于秦,后秦卒以亡周;元帝之待祖逖,失之薄,给兵少,又以庸臣制之,逖以郁终,不能制王敦之逼,敦以逞于晋。明帝英武,平王敦之乱,而惜早死,不及恢复。后之具臣沮恢复之略,石虎之暴也,篡位弑君,劳役游猎无度,且与逆子相残,势可图,庾亮欲开中原,是也,而太常蔡谟沮之,极称石虎之强,晋不能当,朝议亦多有谟同,而亮不能北伐。后殷浩欲北伐,王羲之亦谏之,曰“当此区区江左,天下寒心”。石虎死,冉闵杀其子孙,桓温欲北伐,亦制之不得行,而赵地复为慕容所取。慕容俊、恪之雄杰死,桓温伐燕,秦救之,败于枋头。多以为温之咎,然燕之臣申胤曰:“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沮以败其事。”史不著乖沮之实,孙盛之流,又徇流俗而矜直笔,著枋头之败,固温之所恶也。皆为收复之机,而失之败之。呜呼!庸主具臣舍夷夏之大防,忌英雄之得势,沮恢复之大略,晋宋如合一辙!晋之能保江左而不吞于夷狄者,惟不如宋贬赵鼎,杀岳飞,斩韩侂胄之首送金之过耳。
(三)
王敦势如破竹攻入京城,挟制元帝,杀戮朝臣,似可篡矣,而不篡者,非敦之畏名义,知节制,只诛君侧也。敦之易入,非敦之善战,威足以服人也,元帝任用刻薄,朝士解体,多不御敦,甘卓拥兵,敦之所畏,而坐怀观望,王导之贤,亦不尽忠,是元帝之昏致王敦之横也。而士大夫唯许敦之杀刘刁,除所恶也,敦欲篡,则必义所不容,势所不许。敦自知之,亦有所惧,不朝天子,复还武昌。明帝即位,而敦之志小矣,谓钱凤曰:“我死之后,莫如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何其馁也!与前之攻入京城,杀朝臣以逞威,大不同矣。既疾之甚,不能统兵,亦知明帝非元帝之比,任用贤能,以宽大为政,复合朝士之心,复为逆谋,非算也。钱凤不知形势之异,而以下计为上计,敦未死,即与沈充谋逆。明帝谋讨敦,王导闻敦疾笃,帅子弟为敦发哀,众以敦死,咸有奋志。遂列敦罪恶讨之,敦闻诏,大怒,欲举兵伐京师,势在骑虎,不得不下,而疾笃不能自将,以王含为帅。导与王含书曰:“兄之此举,谓可得复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今则不然,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以刘刁为佞臣,则诚利王敦之反以杀刘刁也,敦又枉害周伯仁等善人,人心亦失,转于明帝矣。而敦为钱凤所误,临终为逆,王含败师,敦大怒,作势欲起,而疾愈重,不能,寻卒。王含、王应以灭,敦出尸,焚衣冠,哀哉!而元帝之长不能制王敦,明帝之少,而敦志不能逞,卒平敦乱,任人之失道与得道也。苟任人得道,示天下以公,又奚患强臣之不可制哉?任用刻薄之臣,以刑名为准,未有不失人心者也,元帝之忧死,实有自致,未可徒咎敦也。
明帝
(一)
王敦死,王含败,欲奔荆州,王应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归也,江州当人强盛,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及;今睹困厄,必有愍恻之心。荆州守文,岂能意外行事耶?”含不从,奔荆州,王舒遣军迎之,沉含父子于江,王彬闻应当来,密舟待之,不至,深以为恨。呜呼!可不为古今之鉴哉!当王敦之强,陵逼天子,威压朝臣,杀周伯仁,而王彬敢哭之,冒死数敦抗旌犯顺,杀戮忠良之罪,仁义为怀,不以势之强弱为易也。敦怒之,而不知之以托王彬,则门户可免于灭。应知其势能立异,能愍伯仁之死,则必亦能愍己之困,而含违之,以王舒顺王敦而投之,卒以父子俱死,彬欲救而不得,哀哉!世人多悦顺己之徒,不知逆己之可依,如含之愚,又岂少哉!
(二)
明帝既平王敦之乱,有司奏:“王彬等,敦之亲族,当除名。”诏曰:“司徒导以大义灭亲,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亲乎?”悉无所问。善矣,光武灭王郎,不问吏与王郎交通之书,官渡之胜,曹操不问将与袁绍交通之书,而安众也,若问之,众必哗起思变矣,何能平哉?况未与敦之逆谋,尤不可除名也。然明帝恶敦之逆,欲禁锢敦之参佐,则非矣,王允诛董卓,不宥卓之余党,而激李郭之乱也,允死,天子复为李郭所制,前车之鉴,而何循之乎?温峤谏之,以为王敦刚愎不仁,忍行杀戮,亲任小人,疏远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间。处其朝者恒惧危亡,故人士结舌,道路以目,诚贤人君子道穷数尽,遵养时晦之辰也。且敦为大逆之日,拘录人士,自免无路,原其私心,岂遑晏处,如陆玩、羊曼、刘胤、蔡谟、郭璞常与臣言,备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奸党,宜施之以宽。郗鉴以为先王立君臣之教,贵于伏节死义,王敦佐吏,虽多逼迫,然进不能止其逆谋,退不能脱身远遁,准之前训,宜加义责。不知元帝以刻薄责臣,而人心离,正宜改以宽大而合人心,明帝违郗鉴而从温峤,是矣,明帝之明也。
成帝
(一)
幼主辅政,大臣辅政,鲜有不国疑而乱者,周公之圣,且有管蔡、武庚之叛,霍光之贤,亦有上官之变,诸葛恪之奇才,死于孙峻,况庾亮志大才疏,轻躁寡谋也。虽与西阳王羕、王导、卞壶、郗鉴、温峤与俱受托孤之遗诏,不专于己,贤于汉之窦、梁。而杀南顿王宗王,旋废太宰羕,则人心惧矣,亟召苏峻而激其反也。苏峻之乱,挟持天子,陶侃平之,合侃与亮合,坚侃以抗峻者,温峤也,苏峻之乱平而峤卒,盖忠劳而死乎!王导称江左夷吾,名过其实矣,管仲尊王攘夷,辅桓公驱逐戎狄,王导外不能北伐以灭羯胡,唯保守江南,内不能平苏峻之乱,使天子挟于贼手,其与管仲相去远矣!而晋朝之乱甚多,权臣几逼帝室,西晋八王之乱,戎狄乘衅,二帝虏于匈奴,东晋有王敦之逼,攻陷帝京,元帝忧死,明帝即位而平之,苏峻之乱,成帝为所挟持,而陶侃平之。桓温废帝,欲加九锡,而谢安止之,桓玄篡位,而刘裕讨灭之,迟迟至百年之久,刘裕以赫奕之功,乘安帝之至愚,方移晋鼎。其故何也?晋以宽厚结人,大封同姓以相维系,又使各家相互牵制。王敦之势如破竹攻入帝京,似可篡而不篡者,惧陶侃诸人之势也;苏峻之得志,亦陶侃所不愿也。桓温之雄才,有废立之威,而不敢篡者,谢氏不附也。皆未有如司马氏之植根深,势力广,所附者众。
(二)
惮京都之残敝而迁都,未有不弱亡者也。曹操之雄也,迁都许昌,此其所以不能一天下也。周东迁而不能制诸侯,王室日微,楚迁都于陈,而愈为秦所侵,终亡于秦,梁元帝迁都江陵,魏人围之而降。晋平苏峻之乱,以建业残敝,廷议迁都,独王导以为不可,一言而定江左百年之基,抗十六国精悍之师。庸人与戎皆伐楚,楚欲迁都矣,蒵贾曰:“不我能往,寇亦能住。”伐庸灭之而威戎狄,示敌以强也。若迁都者,非徒示敌以弱,我益退,敌益进,亦长偷安之情,安可自强进取哉!
(三)
石勒虏晋帝,杀王衍、王弥,反刘聪,禽王浚,灭刘曜,横扫中原,岂不雄哉!乃晚年不能制石虎,身死不久,妻子为虎所陵虐,无遗种,何其惨也!虎之残忍不顺,非不知也,其谓徐光曰:“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暗警石虎也。程遐、徐光劝石勒除之,勒不听,以征伐之功,虎为最,且为骨肉,何忍除之?宗室之中,虎为最强,若除虎,汉人执政,东晋乘衅,羯赵危矣,程遐、徐光虽为心腹谋臣,岂比石虎之亲,除石虎而程徐专权,亦勒所虑也,故不从程徐之言,略削虎权耳。而虎自以功高不得为嗣,怨勒,私谓子邃曰:“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不足复留种也。”勒寝疾未死,而虎已急不可耐矣,矫诏召秦王,彭城王。勒知其必难为臣,临终犹告虎善保其子,以司马氏为鉴,深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虎之鸷忍,惟怨是怀,岂听勒之诫?勒方死,即劫太子宏临轩,收程遐、徐光下狱杀之,召邃将兵入宿,猖狂霸道甚矣,弘大惧,欲让位于虎而不听,怒斥之,虎必欲废之,而不听弘之让也。乃加虎九锡,总摄百揆,篡位之序也。勒妻刘氏与彭城王堪谋诛虎,反为虎所杀,不岁而废弘,又杀之,并其母程氏,甚哉石虎之暴也,逼君之虐过于董卓矣!
五胡乱华,刘石为首,辱晋二帝,恣杀戮之酷,而旋起旋灭,渊、聪之子孙夷于靳准,曜灭于石勒,勒方死不久,子为石虎所杀,石虎子孙后亦诛于冉闵,皆无遗类,天报之不爽,有如是哉!
(四)
石勒石虎皆尊奉西域僧佛图澄,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使司空李农旦夕问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可谓尊宠极矣,奉之如君如神也!国人化之,率多事佛,佛图澄所在,无敢向其涕唾者,争造寺庙,削发出家。呜呼!此佛教乱华之始也!佛虽自汉明帝入中国,天子不尊也,附于黄老,上者有崇佛,不及于下也,汉人皆不出家,王度曰:“魏世亦然”。劝虎禁公卿以下勿得诣寺烧香礼拜。佛曰化恶,而楚王英事佛,笮融事佛,皆为逆恶诛灭。夫君子不仕危邦,无道则隐,今羯赵奴虐汉人,石虎甚之,且父子相残,穷凶极惨,而佛图澄仕之,耽其荣宠,而不能改其暴,恶在其能化恶?曰奉佛则昌,而羯赵内竞甚烈,不数十年而亡,为冉闵灭族。佛图澄不能改,不能救,又不去,耽荣宠也,其所讲者空也,而耽荣宠,空者所以自高,荣宠所以为生也,佛之伪甚矣!浮屠之教恒与夷狄相引,浮屠不得夷狄之尊不盛,夷狄不得浮屠之化不足以奴役汉人,以浮屠神其所出,愚汉之民,相利相报也!汉之世,奉佛者少,自五胡乱华,石勒、石虎、姚兴、拓拔珪等胡君莫不崇佛,奉佛者何多!寺庙遍于四海矣,僧人几与农侔矣。又可见浮屠之妖妄,非得帝王尊之,不能大行,故浮屠大僧恒假帝王荣宠以行其教,自佛图澄始也!
佛固夷狄之教,夷狄所崇也,石虎曰:“朕生自边鄙,至于飨祀,应从本俗。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特听之。”中国崇之,自趋于夷矣。胡君崇之,中国之君又效之,自宋孝武崇佛,齐梁尤大兴佛教,中国变为夷狄矣!夷狄者,浮屠之鼓,浮屠者,夷狄之鼙,如鼙鼓之相引也,三代西汉,未闻佛教,而夷狄未为中国大患,东汉入之,汉亡不久,五胡乱华,五胡为乱,佛教始昌。故浮屠入,夷狄为巨祸,夷狄乱,佛教昌,佛教昌,中国之祸愈烈!后金元,满清之祸,率天下而皆夷狄之,可谓蹈天矣!
(五)
刘石乱华,张骏伤中原之不复,而曰:“先老消谢,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悲哉其言也!岂徒生长夷狄之世者不知有中国之君哉?江左君臣亦自忘之,刘石之内乱,庾亮欲伐之,而蔡谟止之,桓温欲经略中原,而朝廷违之,伐慕容氏,复乖沮其事而使之败,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而于强臣防之甚深,收复中原,早已忘之矣。梁武帝时,胡后杀主,尔朱荣沈其幼君,分崩离析,内竞甚烈,亦可乘而取也。梁武帝以陈庆之为将助元颢北伐,七千之兵,一年之余,克四十余城,破数十万众,所向无前,势可定也。而梁武并无收复之心,不加庆之之兵,唯使庆之挫魏军之锐,以振国威而已。乃以洛阳委于元颢,马佛念劝庆之杀颢据洛亦不从,已忘晋室沦没之恨,则委于夷狄而不惜也。庆之则叹北土衣冠人物,江左不及,则不以彼为戎狄矣。满清治中国近三百年,而中国之人亦多忘其为入寇华夏,奴治我之夷狄,夷夏无殊矣,咸丰之腐朽已及,曾胡犹为之效死命,非洪杨之起,孙黄之倡,孰以其为鞑虏而欲驱逐哉!台湾与大陆相隔近七十年矣,台湾人多忘其祖原为大陆,不得已而迁台湾,思乡之情至死犹深也,然其子孙生长于台湾,茫然不知大陆。台独势盛,蔡英文昏悖之妪而执台湾之政,多去中国之文,削中国之史,使台湾忘其为中国之土,中国之人,以大陆为敌国矣,大陆上下亦置台湾于海外不顾,隐然敌国矣,岂非先老消谢,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哉?且相忘也,则其相敌也,相离也久,难复合矣。故收复统一不可缓也,缓之则必久不归,久不一矣。台湾教科书多削中国之史,诚可恨矣,彼不自以为中国而欲独立也。大陆固自以为中国也,而春秋华夷之战,汉武北伐匈奴之报,卫霍之为将,五胡乱华之祸,蒙元灭宋、满清入关之痛,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屠杀之惨,亦皆削之,曰为民族团结也。蒙元满清之后,犹有蒙满之族在中国,似有所嫌,然昭昭历史大事,岂可削哉!十亿之汉族,顾以蒙满数千万之小族为忌乎?至于匈奴五胡早已灭亡,岂有后在中国为少数民族,而犹讳之削之?夷狄乱华,古今殷鉴,而削之,则多忘前车之鉴,而循其败轨矣,岂可哉!以今日之盛,而忘前古沦亡之痛,恃目前之安,而不顾后世之患,当今专家之罪,可胜诛哉!史者记往日之兴亡成败以不忘也,今之人乃自削其史,使人忘之,君子曰:“忘记历史,等于背叛”,祖宗所患者,而亲之,祖宗所为基者,而坏之,非背叛祖宗哉?削史叛祖之罪,不可逭也。
(六)
郭璞欲为颜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含虽非理学家,而此言,真通理学矣。命在天,非可强求,修己则不愧不怍;性之微,非可强知,守道则无忧无惧。不卜而自有其寿,璞之亟欲人知,则见杀于王敦矣。
(七)
刘翔为慕容皝求燕王之爵,皝使之也,欲借晋之封号以号召中原汉人,豺狼之野心,不可测也。“诸葛恢拒之曰:“夷狄相攻,中国之利。惟器与名,不可轻许。”义正而计亦得。
刘翔以汉高王韩彭为例,引喻失类,韩彭,中夏之人也,高帝之臣也。慕容氏名为戴晋,而实夷狄异类,非晋之所能驭,安保其无异心?刘翔曰:“借使能除石虎,乃是复得一石虎也。”引虎制虎,除一虎,唯人是噬矣。石虎虽暴而将衰,慕容皝谋盛而日盛,除虎,皝之势益大,谲于虎,尤为晋患,且不如两存以相争也。翔之比慕容于桓文,骂恢忌间忠臣,党慕容氏也,段匹磾之非晋忠臣乎?而害刘琨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古人之明诫也,况慕容之据守一方,志怀叵测者乎!先世尝寇晋矣。且晋无人乎?必恃皝以灭胡?皝以此轻晋矣。桓温有英雄之才,晋不能推诚任之也,乃以慕容为忠臣可用乎?其后石虎死,冉闵灭虎之族,慕容氏又灭闵而据河北,公然自帝,为晋之锐敌,诸葛恢之言验矣。幸慕容俊之早死,其继者不才也,不然,晋之折入于鲜卑,未尝不可也。
惜诸葛恢持之不固,晋之诸臣无有折其说者,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而亡,何充、庾冰、蔡谟皆碌碌庸才,畏皝上表暴己罪状而屈从之,晋之不振也!
康帝
庾翼以灭胡取蜀为己任,遣使东约燕王皝,西约张骏,其志是也,联张骏是也,联皝失矣,皝夷狄之狡者,其情不可测也,朝议多以为难,唯庾冰意与之同,而桓温、谯王无忌皆赞成之。后取蜀者,温也,以专制晋朝矣。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读史通论:晋怀、愍、元、明、成、康帝十八篇(8688字)发布于2021-07-06 00:3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