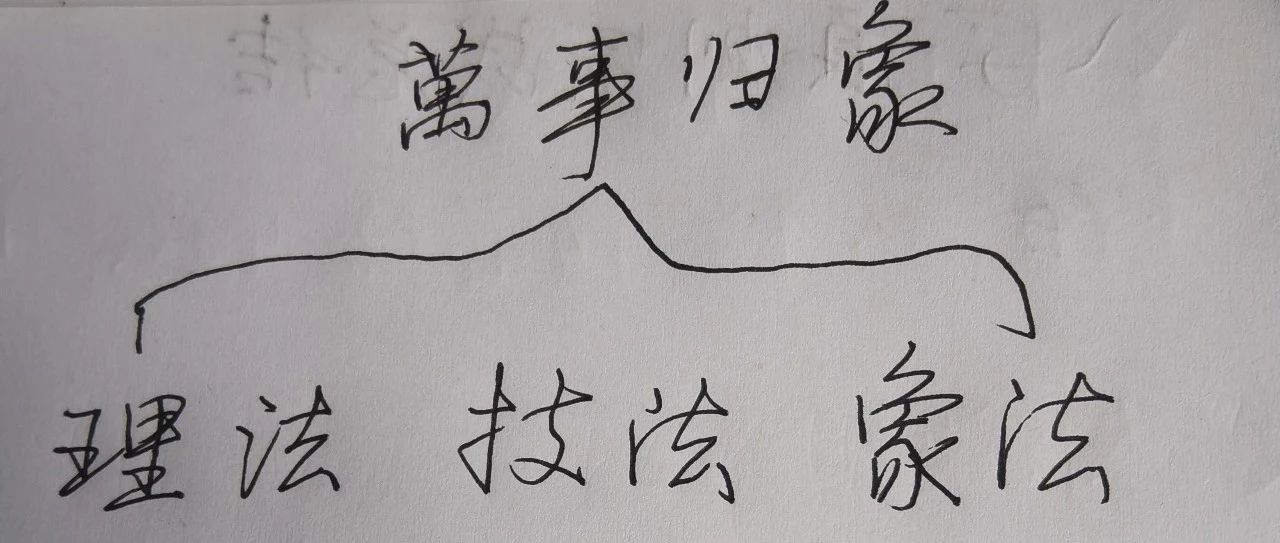吕留良案可谓清代最有名之文字狱,此案颇关满汉民族问题。其源由清以外夷入主中国,士人怀华夷之辨者,无不深拒之,抗清而死者,不可胜数矣。而满虏终得稳据中原,汉人多为之屈,遗民知武力之不可驱虏,乃著书以传大义,王船山之重言华夷不已,诚以种族之痛也,而吕留良于此亦烈矣,竟以此遭身后之殃。雍正年间,有书生曾静者受吕留良著作影响,而萌反清之心,宣言华夷之辨,谓“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以满洲为夷狄,中国为夷狄窃据,当驱逐之,而致书当时占据高位之汉臣岳钟琪,弟子张熙传送书信,以其岳飞之裔,劝其举兵反清,光复汉室。而岳钟琪怀满清之惠,不顾民族大义,乃告发之,于是震惊雍正,雍正亲审此案,查为曾静,源于吕留良之书,而自作《大义觉迷录》书与之辩驳华夷等说,并将此书宣讲天下,下令将已死之吕留良及长子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诀,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吕留良之徒严鸿逵,此时已死多年,但他“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即使死去,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亲、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诀,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子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可谓牵连甚广。而曾静未处死,曰使其心服。至乾隆即位,则曰“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令与其弟子张熙凌迟处死。而雍正之《大义觉迷录》亦为所禁,子禁父书,亘古未有,为其中有隐事不可公者,又关乎满汉种族问题,此书如何,吾可剖析之。于此可见汉族士人之排满心理,至八九十年犹存,满清君主如何歪曲解构华夷之辨,摧灭汉人民族思想,而满清性质是为外国入主,虽雍正不讳也。
满清以夷狄入主中国,非华夏之类也,其不正也明,《春秋》内夏外夷,“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则更不与夷狄主中国,士人执此以反清,雍正为解构此义,乃以天下一家,惟德是辅之说消泯民族之分,其言曰: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驳曰:夷狄之盗中国者,自知非类,乃以道德辨华夷,以泯汉人种类之见。夫德以辨君子小人,华夷之辨,本为族类之辨,以道德混淆族类,则可弃己之父,认他人为父矣。《周易》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华夷大辨,防夷之乱华,岂雍正所谓“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哉!择君以德,然也,所谓德,华夏之有德者,中夏地广人众,岂无有德之人,而迎蕞尔小夷为华夏之主耶?以道德辨华夷,其实为势力之见也,满清岂有德者哉!入关之前,屡犯边疆,掠杀吾汉民上百万矣,入关后,更为剃发易服,逼迫屠戮吾汉人之死者不知数千万,仅扬州之屠,有八十万,残虐无道极矣,汉人起兵反抗者数十年,至康熙,犹不止,朝鲜亦痛中国之亡于满清,暗称清帝为胡皇,贬其君,犹用崇祯年号,吊明反清形于其史册笔记者甚多,而曰“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何其言之不怍也!以成功者为有德,是雍正道德之论也。
余曰:人之不能认他人为父者,耻心也;人之不能认异类为君者,耻心也。无耻之人,以他人为父,而忘其所自生;以异类为君,而忘其所自出。充一无耻之心,卖国者多矣,民族将何保哉?
而彼则欲以所谓道德泯华夷族类之辨。曰有德则为吾君,夫于中国言之则可,于华夷言之,背华而从夷,以夷制华,其罪大矣!华夷不辨,曰有德则为吾君,投降夷狄之汉奸,岂不曰吾君有德,而文饰其降虏卖国之行!刘秉忠之宣扬元威,洪承畴之称颂清德也。
夷狄之贤者如金世宗,泽于夷狄,而非及华夏也,宋金世仇,宋人可以金主之贤而戴金主为君,而易宋帝乎?康熙泽于满洲,固满洲所谓贤君也,其于汉族则防之甚深,异族也,沿海迁界,虐汉民不啻禽兽,何其酷焉!
彼曰:华夷,必辨之以道义,不可辨之以种类。
余曰:华夷,即种类之辨也。若道德之辨,则君子小人也。安可全以道德为判断,而泯灭种族之大防乎!外国有贤者,吾敬之,而于两国交战,可输吾国之情于彼国乎?种界,国界不可破也。日本有信奉孔孟之学者曰:“虽孔子为帅,孟子为将伐吾国,亦当擒之以报吾国。”民族主义之强如此,岂以敬慕外国贤者而易其爱国之情哉!
君者,群也,率领吾族群而为福者也,可率吾族群者,吾族群之贤者也,异族有贤者,为彼族也,可同心为吾族乎?夫族群不知自立自强而引戴外人为主,其亦可耻矣!
无其德,不可为吾君,非其类,不可为吾君,有其德,为其类,可为吾君矣。君者,族群之长也。本族虽有不贤者为君,犹可易也;他族有贤者入主吾族,不贤者相继,不可易也。朋友虽善,不以凌兄弟;异族虽贤,不以主中华。亲疏之别,内外之辨,天理之本然,非以人之贤可以易也。
德有君子小人,辈有尊卑,位有贵贱,血有亲疏,人有华夷,地有内外,不相易也。子侄之敬父母叔伯,岂以其不贤而失其敬?岂以子侄之贤而易其尊?人之爱兄弟子女,岂以其不贤而失其爱,岂以他人之贤而易其亲?则圣人之内华夏,外夷狄,岂以华有无道,夷有贤君而泯其内外,使夷为华之主?况华夷为天下之大防,地之纪也,华夷乱,地维裂矣,虽圣人之德,无以易也。
光绪之有仁心也,而革命者犹反对之,斥保皇之非,立宪之伪,非我族类也。非我族类不入我伦,虽其贤德,非为吾族之利,而其愈贤,愈为吾汉族恢复之患。则所谓反清者,光复为首,除暴政专制,其次也,不患其暴也,而患其贤也。夫以数万万之汉人受制于数百万之满人,有可耻之心矣!虽光绪之有仁心,亦必反之,虽清室之行立宪,亦必革之,耻为异族统治也,欲求汉人自主也。耻心之存,人情之常,天理之正,以为狭隘者,其亦卑矣!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夷狄虽有贤君,不如诸夏无君,诸夏无君,亦不可求夷人为君。《春秋》不与夷狄之治中国,夷狄不与,《春秋》常辞。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圣言彰彰矣,安可以“道义”泯其内外之别哉!夫德辨君子小人,今乃以德辨华夷,则夷之有德,可为华之主,其似尊德义,而实裂地纪,始于崇德,而终于媚夷也。孔子有教无类,非有主无类也。
吾又作论《类可不辨乎》曰:
儒家五辨:人禽之辨、华夷之辨、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正学异端之辨,以要而言之,实三辨也:人禽华夷之辨,辨于物也;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辨于德也;正学异端之辨,辨于学也。
夫仁义有界也,界之者伦物也,爱人利物,仁也,施之豺狼则愚;瘅恶惩奸,义也,行于父母则悖。皆由无分,而乱大德,害大伦。德者,以辨义利,以别君子小人也,非以辨类也。以义而行于父子,则子可以弑父矣;以仁而通于华夷,则夷可以侵华矣。
父子,大伦也,子虽有德,不可以命父;华夷,大界也,夷虽有德,不可以主华。或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外国人苟能明明德,即可以作君师矣”,“君臣以义合,合其义即可为君,不必辨其类也”。呜呼!华夏之与夷狄,如人之与禽兽也,判然而不可易者,若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则禽兽进于人而亦人之乎!犬豕学人之语,为人之行,称犬豕为人,可乎?彼夷狄学华夏之文,为华夏之礼,而讵可称为华夏也?中国之道,中国之行也,夷狄能行中国之道乎?窃礼乐以自尊,而谓为中国之道乎?人之道,人之行也,禽兽能行人之道乎?模人之言行以相媚,而谓为人之道乎?以外国人为明明德者,可为中国之君师,则子之明明德,亦可为父之君师耶?合其义则为君,则凡合于仁者,皆可为父而不辨于类耶?夫以尧舜之德,贵为天子,不可以臣父;夷君有德,即可主夏耶?但辨德,而不辨类,则尊卑倒矣,民族混矣,非所以明伦也,非所以存国也。
且类者,即义之所分也,人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于亲而有父子,于位而有君臣,于人而有华夷,漫然无分者,异端也,而以儒言乎?父虽无道,子不可以不孝,朋友有恩于己,且不忍相害,况父乎?以父无道为戮而曰大义,实为不义,导天下以灭亲也;夷卑于华,夷虽有德,华不可以不攘,楚之变夷,诸侯犹欲共抗,况夷狄乎?以夷有德为君而曰合义,实为悖义,教后世以猾夏也。类之不辨而曰义,贼义;如学之不辨而曰道,贼道。此儒者所当深拒,而可为之言乎?
伪儒承昔日胡君之论也,胡君已死三百年,满清已亡百年,而犹有伪儒祖述其论,岂所谓心中辫子未去乎?甚矣,满清之流毒至今不息也,可不浚其源乎?
雍正又曰:“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
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佑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
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
驳曰:戎狄猾夏,盗据中国,乃妄称天命以欺人!杀我人民,盗我疆土,何绥何爱?而欲吾民除华夷之见。春秋之义,尊王攘夷,势之暂屈,非谓理之终服也,以夷治华,颠倒乾坤,逆理之甚者,而犹欲吾民尽臣道于尔夷,而不可怀有异心耶?尔夷之居心不良,处心积虑防汉,盗吾土而不释,犹欲吾民之无异心,岂不悖乎!所谓大一统,一统有分,有仁义之统,商周是也,有暴力之统,秦是也,君子尊商周而反秦,有华夏之一统,汉唐是也,有夷狄之统华夏,元清是也,华夏统于夷狄,不幸之甚者,君子欲图恢复攘逐者,何大之有哉!
逆虏背恩反噬,盗据华夏,封豕豺狼也,吕留良恶之,欲图恢复,而力之不能,托之于言,民族义士也。盗憎主人,而极言诋訾民族义士,欲保其所盗者也。德祐以后,华夏尽沦于夷狄,蒙虏盗据全中国垂百年,诚天地之大变,亘古未经,此明人之公论,岂吕留良一人之私见哉?
宋遗民谢叠山《送黄六有归三山序》感叹:“嗟乎!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有天地以来,无此变也。”天地未有之变,当时士人心境可谓痛矣。谢叠山《东山书院记》又曰:“自有天地以来,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极矣,……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竞灭于诸儒道学大明之时,此宇宙间大变也,读四书者有愧矣。”
明人陶鲁曰:“胡元猾夏,宋祚乃亡。宋亡,则中华变为夷狄,衣冠同于左衽,开辟以来非常之变。”
魏焕《皇明九边考》曰:“我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至于陷没疆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乱华蒙古灭宋,夷狄之祸于斯极矣。”
丘叡《世史正纲》曰:“有华夏纯全之世,汉唐是也。有华夏割据之世,三国是也。有华夷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也,有华夷混乱之世,东晋及五代是也。若夫胡元之入主中国,则又为夷狄纯全之世焉。噫!世道至此,坏乱极矣……天翻地覆,夷狄反为华夏之主。自天地开辟以来,未始有也,有之始于此。呜呼!岂非天地间极大之变也哉!……洪武元年春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
又曰:“世道极变之大有三:曰臣而僭君之位也,妇而当阳之刚也,夷狄而为中国之主也。自秦汉以来,僭君之位有莽、温焉。然前此犹有羿也。当阳之位有武翠焉曌,然前此犹有娲也,夷狄之主中国,则首昉于蒙古焉。前乎此者渊、勒,非不称帝也,然崛起而倏灭;辽金,非不僭号也,然偏安于一隅,未有混一天下,使凡覆载之间,止有夷而无华如元世者也。呜呼!岂非世道极变之会欤?”
丘叡的《大学衍义补》亦曰:“伏惟我圣祖承元人斁败彝伦之後,所谓大乱之世也。当是之时,以夷狄之人,为中国主,天地于是乎易置,华夷于是乎混淆,自有天地以来,所未有也。”
王洙《宋史质》曰:“胡元者,蹙金灭宋,取帝王礼乐衣冠之地,而以腥膻之,自天地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变也。日月为之薄触,时序为之倒置,天地为之反覆,冠履为之易位……”
王世贞《读元史》曰:“余尝怪晋世匈奴鲜卑羯氐羌以至索头之虏更迭而入为主,其割中国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袭华号,变夷礼,多足称者,盖至孝文而其俗彬如也,岂其先尝杂处中国,有所觊慕于志耶?宋亡,而薄海内外鲜有不为元者,顾其君臣日龂龂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国之俗,省台院寺诸路之长非其人不用也,进御之文非其书不览也,名号之锡非其语不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视中国之地若瓯脱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国之民若赘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以供吾嗜而已。于乎!不亦天地之至变不幸者哉!”
姚涞上疏明世宗曰:“夫华夷大分也,臣请为陛下陈之,中国之与夷狄,其防至严也,是故内中国而外夷狄,岂非以其荐食上国,糜灭人类,有甚于乱贼之当诛者欤!自有典籍以来,犬戎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讨,此中国之大仇耻也。刘石诸胡囚执晋怀愍,盗据神州,而晋人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仇耻也。完颜吴乞买入汴,而虏徽钦,奄有天下之半,宋人窜于江南而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仇耻也。此数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愤者也,然犹未全盗我中国也。蒙鞑继兴,有所谓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石,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伦,变我礼乐,而万古帝王之中国,始尽胥而为夷矣。”
陈棐上疏明世宗曰:“元乘宋之弱而吞噬之,习中国以胡俗,正以胡人浊我寰宇。歝我彝伦。始则以夷猾夏,既而变夏为夷。当是时,吾天地所开之中土,吾万古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区尽沦胥而为夷狄……”
王船山《尚书引义》曰:“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
夷祸之极于胡元,前古未有之变,有心者皆知之也,不能深惩大诫,使清步元之后尘,而其祚之久,毒之深,倍屣于元,岂但复见而已哉!王船山曰:“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揆之满清之世,岂不然哉!尔夷入主中国,为禽心鬼计,治汉无所不用其极,以桎梏吾民,多忌讳,严刑罚,士以文字罹祸,民以聚集遭刑者众,压抑甚矣,极阴之世也。“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吕留良以满洲为外来入主也,强盗也,而犹诋汉人怀此疆彼界之私,国可无界乎?侵盗有理乎?立国所以为界也,无界何为立国?华夷之界,不可无也,侵盗之无理也,夷之猾夏盗夏,尤为逆理也。尔夷逆理之甚者,不自愧也,而敢横诬华夏圣王舜文为夷,舜文岂尔夷之无道者可比乎?舜文,皆黄帝之裔也,居在九州,非尔为女真遗孽,出自荒外也。舜之君临天下,尧让之,天下推戴之,非尔夷之侵盗也,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吊民伐罪,非尔夷之猾夏贼民也,而敢相拟乎!《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尔夷之阴鸷,是必膺者,尔夷之盗夏,屠戮汉人无数,是必惩者,荆蛮不恭,则必膺必惩之,况尔夷之横恣毒夏者乎!秦楚非如尔之为外夷,故孔子不以为外,秦楚世系,史记记之详矣,何待辨哉!而今犹有小人伪儒者诬秦楚为夷,以证满清入主中国为合法,承雍正之绪论,岂胡君之徒子徒孙乎?
华夷之说,由来久矣,《春秋》所辨,《诗》、《书》所称,晋世,五胡乱华,鲜卑入主,僭号魏帝,北陷于胡,衣冠南迁。南实华夏,北为索虏,而反贬华夏为岛夷。清亦索虏,固不辨华夷,故为似公之论。清之天下一统,非统一于华夏,乃统一于夷狄也,所谓华夷一家,实为夷狄盗夏,喧宾夺主,贵满贱汉,夷高于夏,何为一家?汉家义士辨析华夷,使后人不忘尔夷之为寇盗,而诋为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盗之反詈主人,尔夷为甚矣!蜂蚁不若者,为夷之伥,残害汉人之汉宄也,若洪承畴、尚可喜、孙之獬是也,蜂蚁犹知爱护其类,此辈不知也,反为异类助虐,而以加之吕留良爱国之义士乎?盗憎主人,不惜颠倒是非矣!无父无君,非其德,非其类,何父何君?认夷为君父,华夏之耻也,不愿认为君者,恻隐羞恶之心不泯也。寇盗华夏,而犹以君臣之义责吾士,甚矣尔夷之颠倒错戾,丧心病狂,至此极也!
明自嘉靖以后,固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然此为中国之事也,中国之乱,中国之人定之,于尔夷何预?乘吾中夏内乱,假汉奸之助,侵暴吾地,系累吾民,率天下而皆夷狄之,为剃发之丑。中国之乱,民荼毒已甚,尔夷入寇,而倍屣之。屠戮已尽其威,使吾汉不能复抗,而假托安抚之名,内行奴役之实,不欲吾民之怨疾尔夷亦已矣,而敢反称吾民沾尔夷之恩耶?“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此清初唐甄之言也。不及明代远甚,明犹有集会之自由也,犹能清议也,尔夷尽禁锢之。
尔夷之无道,亦敢言天地以仁爱为心,何以视吾民如草芥而刈割之?视士人如猪狗而蹴辱之?尔夷之外远,其德也,何及于吾华?而自万历以来称兵猾夏,寇掠不已,是谓德乎?而敢自称大德受命,盗之大言不惭,自为狌狌狂吠,而反詈主人之愤言?保己寇盗之私,不欲人言,而反斥主人恢复为私?斥主人为逆贼?为贼,孰有过于满虏者乎?卑卑小夷,人口不足百万,盗据泱泱华夏,并侵吞他国,贼之大者,反以詈主人,贼喊捉贼,莫此为甚矣!
雍正又曰:“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以夷狄譬诸禽兽,自古以来之论也,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建夷之阴狡,乘衅入寇,借汉奸之助盗据中华,乃敢矫诬天命,曰“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则满清为外夷入主,雍正亦不讳矣,“夷不乱华,裔不谋夏”,岂有外夷可以主中华?逆之甚者也。满清非中国,明矣,满清之君自认也,奈何今人多认之为中国,忘其为外夷入寇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诸夏虽乱,无君,犹胜于夷狄之君,而无有求夷狄为华夏之君者,此吕留良之意也,势之屈于夷狄,不如夷狄之阴狡得逞,岂谓诸夏之德不如夷狄乎?戎狄无道,盗据华夏,淫杀无数,无德之甚者,犹自诩有德,詈我华夏之人乎?
雍正既以成败道德说解构华夷之辨,继以版图扩大说称扬满清之功,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驳曰:华夷在人不在地,齐鲁之地,周以前亦为夷也,周封诸侯,华夏据之为国,则华夏矣,元清虽入主中国百年,犹夷狄也,岂以居华为华哉!有内夷,有外夷,向化之夷,内夷也,不向化之夷,外夷也,岂徒以不向化斥为夷狄乎?华夷之分,类聚群分也。羌汉杂处百年,汉苗杂处上千年,而犹有华夷之界也,况满汉之于先世,素不相接乎?尔夷非向化者,而又猾夏肆凶,为吾华夏附骨之蛆,中夏有志之士,必谋攘逐。亡我中国,摧残吾士人,奴役吾人民,又侵吞他国,中国之大不幸,亦其他夷狄之大不幸,而曰为我中国开疆拓土?则何不归国权于吾华?
雍正此说为近代伪儒康有为所承,康有为之驳革命,而称满清之功曰:“国朝之开满洲、蒙古、囘疆、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汉唐,而轶宋明。”至今则有学者称满清为中国版图之扩大有贡献。呜呼!不思亡我中国近三百年之恨,备极压榨,犹谓有功于吾华耶?满清之开疆,与中华何关?小儒竖学乃艳称以为荣?无耻之甚也!虽灭蒙古,西藏,实汉满蒙藏分治也,不使相往,故满清亡,而蒙藏皆思独立,内蒙,西藏至今属中华者,则共和国之出兵有力也,舍汉人之功,而以归功满清耶?
虏君已死二百年,犹有康有为之徒祖述其论以拒革命,雍正曰:“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於圣德乎?”康有为曰:“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当今伪儒如余东海辈亦为此论,为满清辩护,而不惜上诬古之圣王,丧心病狂,何至于此也!雍正曰:“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康有为曰:“所谓满汉,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雍正曰:“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同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猡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为夷狄可乎?至於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并蒙古极边诸海,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士,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之分论乎?”康有为曰:“中国昔经晋时,氐羌鲜卑人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徧布中土,多以千亿,又大江以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康有为真虏君之孝子贤孙也。虏朝已亡百年,至今犹有承其绪论者,何虏君之狡,可以欺当时,摧灭吾汉人民族思想,且可欺后世耶?何有汉人之愚,受其欺而不觉耶?心中辫子犹未去乎?虏君之魂犹治吾汉人之心乎?虏君著作犹在也,邪说之源也,从根驳正之,而当今颂清之谬论可以息矣。
雍正又以君臣之义责吾汉族士人,曰:“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君道子元元,是也,欲臣奉君如父母,何其责臣之严?君之亲孰与于父?而以君拟父母?虽不仁于臣民,亦不可疾视之?君臣不可与父子比,父子天性,天性不可离,君臣以义合,义不合,则去。吾闻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雍正之意,君犬马土芥其臣,犹欲其臣奉之如父母?何其责臣严而责君宽?待臣薄而待君厚耶?满清之尊君卑臣,臣以奴婢自称,三跪九叩,杖打时加,曾犬马之不如也,则其民可知矣,而厚颜不惭,曰尽父母斯民之道耶?君辱其臣,而曰父母?臣议其君,而曰诽谤?况尔夷非吾固有之君,强以势临之,胁华人拜汝为君,而欲珥华人之谤耶?
雍正恶汉人之图谋恢复者,曰:“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驳曰:康熙年间,各处起兵,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假称朱姓,反清怀明也,欲借复明驱逐尔僭窃之夷也。元末,韩山童亦假复宋之名反元也。历代之亡,复明者最多,非明之德厚,历代不及也,代明者满清,非华夏之类也,其祚久。雍正言“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则汉人之不服满清统治者多矣,非以满清夷类僭盗之故耶?恶汉人之图恢复者,称为奸民,论奸孰如尔夷?假称为明复仇,剿灭流寇,自据北京而有之。称中国人君之子孙必至于无噍类,则满清非中国矣,明之宗室为尔夷戕害殆尽,而以咎吾民乎?
明太祖之起兵,始于复宋也,北伐蒙元檄文,称“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矣,固继唐宋而非继元,元犹据漠北而与明对峙也,得国之正,莫如洪武,而诋为篡窃。尔夷既与明为邻国,尝称臣于明,则当守邻国之分,何敢荐食上国?灭邻国,非侵略之罪耶?呜呼!诋恢复者为篡窃,文谮窃者为有大造于中国,颠倒是非莫如尔夷!
论边患莫如尔夷,倭寇犹其浅者也,明末之大乱,尔夷为罪魁祸首,善哉张煌言曰:“自辽事起,而征调日繁、催课益急;以故溃卒散而为盗贼,穷民亦聚而弄干戈,是酿成寇祸者,清人也。乃乘京华失守,属国兴师;诚能挈旧物而还之天朝,则是吐蕃、回纥不足专美于前。奈何拒虎进狼,既收渔人之利于河北;长蛇封豕,复肆蜂虿之毒于江南?”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昆阳之屠,江阴之屠,大同之屠,皆汝清军为之,不自反,而责明军之杀良冒功耶?四川之人,致靡有孓遗之叹,虽张献忠之残忍好杀,汝清军所为亦多矣,使多为献忠所杀,何以四川犹能抗清至十三年之久耶?尔夷之狡,尽推于献贼矣!
一将功成万骨枯,仁人犹为叹之,况尔夷之屠戮汉人数千万,乃统一中国,夷狄之统一,暴力之统一,中华之大不幸也,尔夷以为功耶?尔夷入寇,使汉民如火益深,如水益热,何强盗之厚颜大造也!当时遗民朱舜水曰:“逆虏得国之后,均田不可冀、赋役不可平,贪黩淫污、惨杀荼毒,又倍蓰于搢绅之祸哉!”尔夷之淫杀,朱舜水曰:“贫者两三家派供一日,稍可者日逐坐养一兵;贫民半菽不饱,情何以堪!既已养之,仍要淫其妻子,不敢不从。若有一家杀死兵丁,诬以谋逆,则阖村洗荡;不得已忍辱忍气,不敢轻举。”尔满夷之淫毒至此,吾汉人之大辱也。尔朝暴政,如朱舜水言“满清暴政“海口造船,并派近海民帮工舂灰、牢钻匠作,饭食更须民家承值;虽官给朱银,百姓不胜扰害。今岁造船,明岁又须修船;修而复烂,烂而复造。何时底止,穷民何以聊生!”“栓锁鞭箠,为过期之利息;出妻献子,作别项之添头。”“奸淫万状、科派百端,又其罪之最重者。然一部十七史无处说起”,“大兵所过,四出骚扰;指称奸细,搜灶株连:处处皆然,人人饮恨。虽民间冤惨号天,然无力俾离水火。又苦笔力短弱,不能绘监门之图、播道州之咏,奈何!”尔夷之罪恶,擢发难数也!厚待明代,名曰加恩,实残害朱明子孙殆尽,天下已定,汉人不能复起,方假安抚推恩之虚名以愚吾民!吕留良之不忘明代,实不忘中华也,乃有明之贞士,中华之义士,分别华夷,使后人知尔满之为夷狄寇盗,冀后人之恢复,诚尔朝之敌人,而明代之忠臣也!
雍正之强盗逻辑如此,甚又歪曲篡改经典以文其侵盗,曰:“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
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驳曰:中国,中国人治之,何可令外国人入主?而曰非是非之公?外国之君,以华夏为异类,能以中国人为赤子乎?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戎狄猾夏,寇据华夏,华夏之人谋所以攘逐之,人情也,何谓非人情?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非不非其大夫也,出自论语,圣人之言,尔夷亦敢篡改!大夫有贤不肖,事其贤者,是也,何为贤不肖皆不可非耶?不容人议,尔夷之阴鸷倍于厉王之珥谤矣,厉王珥谤败,被放,尔夷珥谤成,犹据中土也。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尔夷之伤人,何可胜数哉!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夷不如夏,诸夏虽无君,犹胜于夷狄之君,则安可延外夷入为中国之主?尔夷乃歪曲其意。韩愈《原道》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千古名篇,尔亦敢篡改其言!韩愈之意以辟佛,谓诸侯用夷礼则贬为夷,用中国之礼,则复中国之称,岂谓夷狄可进为中国哉!雍正篡改之言,以辩护清之强盗为合法。然满清之剃发易服,三跪九叩,显然夷狄,又不待辨者。
“不欲归美外来之君”,则元清皆外来之君也,夷夏大防,夷夏不杂,矧以夷狄主中国哉!中国不数其罪亦已矣,而欲美之乎?以华夷之见为私心,尔夷之无道,亦自广而狭人也。谐臣媚子颂元清者岂不备至?而谓可以劝善乎?至非贬辞者,为世道人心之害,何尔夷之专制,不令中国之人讥刺外国之君也!极言吕留良者为千古罪人?洪承畴之汉奸,于尔夷有功,则为千古功臣乎?尔夷所谓功罪,但对尔夷,而不对中国也,盗之反詈主人,喋喋不已,尔为极矣!理之不直,而何色之厉也!
又以陈胜等辈警吾汉人谋恢复者,君子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苟能因此驱逐戎狄,恢复华夏,何计一身之祸福?陈胜、项梁死而秦亡,刘福通、韩林儿死而蒙元亡,犯天下之险而首事者,虽未有不败,而以震暴主夷君之胆,为其灭亡之先征。司马迁之列陈胜世家,彰其反秦之功也,韩刘之反元虏,义更高于陈项,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大义也,岂认贼为君,为大义乎?雍正斥为奸民,贬为万世罪人,何其保己之攘窃,而恶夺回者耶?
雍正又曰:“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甚矣,雍正强盗之理也,既以君臣混淆华夷,又以君臣重于父子,谓不认彼为君者为禽兽,为逆天,此又鄙陋至极,无须辩者。
雍正驳曾静曰:“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驳曰:曾静曰:“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此实言也,尔夷尝为明之属夷,而僭窃中华,悖逆之至,而自矜其功若此乎?尔所扬言之功,皆对我中国之罪也!侵吞诸国,尔曰统一诸国,为诸国共主,则满清非中国也。与明为敌国,何夺明之江山?南明亦不容其存在,台湾亦必绝其一线之延,尔夷之无底线也。南明非明耶,何为不取于明?蕞尔属夷,荐食上国,敢自拟汤武而过之!何尔之厚颜不惭!
雍正称己,犹可言也,吾见网上一伪儒名“一大袋活蛆”者则以清比汤武,何其言之似雍正也。彼曰:“有清氏之兴,以德征不道,亦汤武矣。”吾驳之曰:“以夷狄为汤武,以中华为桀纣,则夷之侵华,当也。则其所谓君主以德不以类者,不过美夷之德,以助夷之侵华耳。斯言也,不可谓有人之心矣!而降虏卖国,为虏灭华之汉奸亦可自饰曰:‘吾归有德而伐无道也。’为汉奸而不惭,则汉奸者众矣!曰有德则可伐,蒙元之攻宋,满清攻明,日本之攻民国,孰不称己之德,不过侵略之借口耳。有德则可伐人耶?果为德耶?元清以夷狄乱华风,以犬羊干天纪,其所谓道,夷狄之道耳,而中国生民受其吞噬而憔悴,死于屠杀文字狱者不可胜数,而乃比于汤武耶?汤武以仁伐暴,满清以夷寇华,其可等乎?徇恶美夷,何至于此!清有道,日本为猾夏,日本猾夏,满清之攻明,非猾夏耶?志士之恢复,辛亥之革命,非耶?所谓德,为华而讨夷,则顺,为夷而攻华,则逆。父母之邦也,祖宗之土也,虽其治之者无道,忍引异类以伐之乎?称颂入侵者之德,而诋斥本国之恶,其何忍!论德之有无,不辨族之同异,而其德者,势力之论也,势强者为有德,势弱者为无道,强可侵弱,族之不辨,认虏为君,使之寇据华土,而为吾民之害大矣。且明末虽腐败,未若桀纣之暴也,犹中华之主,满清虽兴起,岂比汤武之仁乎?且为夷狄之主。清之攻明,岂为顺乎?汤武,桀纣,皆中华也,一仁一暴,然而武王之流血漂杵,义士非之;清与明,一为夷,一为华,而其德之相齿,未见清之胜于明也,若文之相伦,则清之逊于明矣,以藩邦攻上国,以蛮夷寇华夏,为之抵抗而死之烈士,不屈而隐藏之遗民不可胜数也。岂清之有德哉?剃发改服,屠杀文狱,无道甚矣,况为夷狄猾夏乎!”“一大袋子活蛆”可谓虏君孝子贤孙矣。
此汉奸之论,当年抗清烈士张煌言斥之矣:“夫建酋,固我明属夷也;一举而踞北都,再举而窃南纪。共主蒙尘,宁藩化碧,而乱臣贼子顾曰: ‘彼沛公也,亡秦者也;我子房也,报韩者也’。则是闯贼得比始皇,而沛公实杀韩公子也;则是子房当事楚霸王,而建酋可称汉高帝也!呜呼!诬子房矣。”
至于为明复仇,则当时张煌言亦驳之矣,曰:“昔日之北庭,非本朝之属国乎? 建州之甲,已忘休屠之恩矣,辽左之烽胡为乎? 北平之旗,似同回纥之义矣,南牧之马又胡为乎? 旧都嗣服、正朔相承,冠盖方达乎蓟门,鼓鼙已震乎吴会。 自是而蚕食东南,翦灭之不遗余力。 凡我天潢,虽在遯荒,靡勿芟薙。 夫以高皇帝骏德鸿功,而使其子孙祸酷徽、钦,祀荒杞、宋:宜人心之不服者。”
陈去病《建虏入关手段之变迁》曰:“建虏之入关也,廷臣咸以秦师之救楚视之。以为他日事定,全师返北。已可让地通款,以酬其庸。初不虞其一人不再出也。故城破之日,上下欣欣,争相迎犒。或奋起而与闯王为难,以是自成不能支,竟舍城去。而建虏又即为帝后发丧,谬加恭敬。凡先明各官俱听照旧视事,一不干预。不剃头,不易服,安民四出,鸡犬不惊,民皆大悦。说者谓:八国联军据城之役,其情景盖仿佛似之。既而始托词,令群臣咸出诣朝计事。至则侍卫森列,朝仪备具。内殿传宣,景阳钟动。虏酋福临,已乘辇出登宝座矣。乃皆大惊,失色相顾,目瞠舌挢,而不敢动。顾事已至 此,其早怀二心者,已俯伏阶墀,山呼万岁。遂不得已,陆续拜跪,称臣叩首,祝皇帝万岁焉。又未几,而易服令下矣。又未几,而剃发令下矣。又未几,而虏兵大举南下矣。又未几,而屠城令下矣。又未几,而破扬州、陷南都、虏福皇帝,下杭城、降潞王矣。又未几,而入浙、闽、戕唐皇,逾岭南、迫滇黔、临缅甸、缚永历,且杀之矣。呜呼!棋局骤翻,着着棘手。狡虏之阴贼险狠,残忍刻毒,吾亦何忍缕言!”
为明复仇,名也,乘虚盗据中华,实也,南明四帝,继崇祯者,而满虏剪灭之无遗,诚张煌言所谓祸同徽钦。譬如一家有难,奴仆弑其主,其子弟继其业,有一盗入之,杀其奴,而又戕其子弟,遂占据其家园,犹自称有造于其家耶?何逆虏言之不羞,而有汉人受其愚也!
距甲申八十年,而犹有曾静等儒生不服满清,诚以满清戎狄异类,贪残无道也。中国之土,尔夷据之,中国之栗,尔夷食之,何尔言之反也,谓我汉人履尔清之土,食尔清之栗,此土久为汉土,相传千年数千年,尔夷近年外入者,久据不归,则以为己有耶?
其他言论亦如此类,或鄙陋不堪,不必辩之。而曾静反清之书,必为雍正焚毁,不可见矣,唯于《大义迷觉录》见其片段,有云:“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者,天下得而尊之亲之。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有责岳钟琪之言,如“戴皇祖之仇以为君,且守死尽节于其前”,“俯首屈节,尽忠于匪类”,责钟琪以岳王之后臣事其仇女真之后满清也,匪类指满清也。
曾静之书《知新录》又有“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之说,颇为雍正所忌,曰:“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华夷第一义,韪哉其言也!君臣之义,在华华之间,移于华夷之间用,裂华夷之大防矣,犹以忠臣自诩耶?失于第一义,尚何君臣之义?
曾静又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欲鼓动汉人驱逐满虏也。
曾静又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此亦为雍正所忌,封建利于御夷,诚如所言,吾史论言之,此且不论。雍正驳曾静曰封建之废为势之不得不然,然已为宋儒所非矣。赞成封建者,宋明学者颇多,雍正斥为“奸恶倾险”,何其忌于封建也,满清高度集权,满清自为夷狄,恶汉人为牧伯者也。
曾静又云:“中国人之诡谲反复无耻无状者,其行习原类夷狄。只是恶亦是人之恶,天经地义,究竟不致扫灭。若是夷狄,他就无许多顾虑了,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此亦发挥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而雍正对此如泼妇骂街,骂曾静为禽兽不如!
曾静又云:“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此真直言快语,船山曰寇贼我者,多杀而不伤吾仁,岂可姑息!
按曾静一老书生,犹有如此强烈之民族思想,受吕留良著作之影响也,故雍正患之,乃亲自著书驳之。华夷之辨由来久矣,历代相承,雍正自知不足以否定之,又驳曾静曰:“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
此论旧调重谈,无须再辩之,雍正为否定华夷之辨。并否定中国历代之君量为不广。而其愈辩愈见满清之非中国,为外夷入主,雍正前曰“方眷我外夷为中国主”,满清之为外夷,雍正自认之矣,此又曰“眷佑我朝为中国主”,是清朝非中国,而殖民中国者也,曰“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蒙古、中国并称,是中蒙本为两国,而满清并吞之也。
凡此皆可见当时士人排满心理犹存,著书立说之影响后人也。自雍正之文字狱,解构华夷之辨,摧灭汉人民族思想,而正论不复见矣。而乾隆禁其父书,一恐其书自辩,愈辩愈显其丑,二恐强辞辩华夷,不足以服汉族士人之心,汉人犹知满清为外夷入主。
又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大义迷觉录中》,雍正曰:“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何其与圣人之言相悖也,偏责臣民,而宽于君,满清之尊孔崇儒,岂其诚也哉?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陶扬鸿:关于雍正《大义迷觉录》之满汉民族问题,驳斥胡君邪说谬论(约两万字)发布于2021-07-06 00:3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