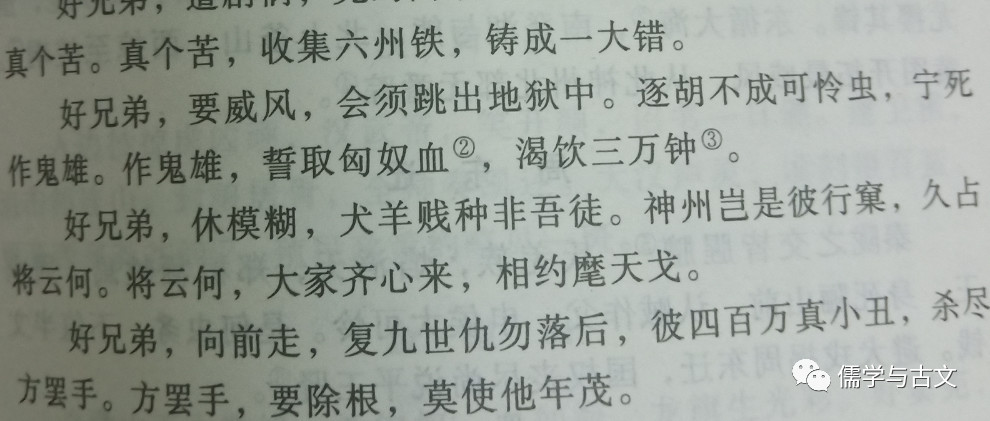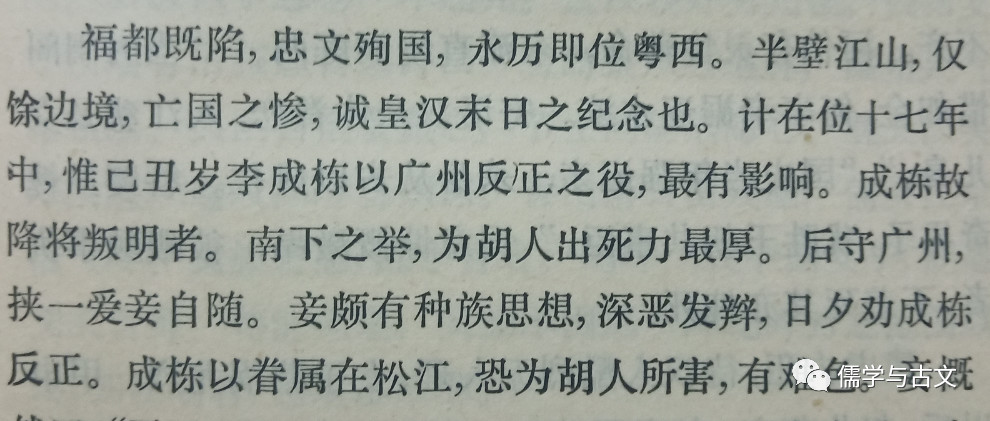元帝
(一)
汉元帝称柔仁,元帝柔则柔矣,而未可谓之仁也。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元帝于此远之矣。柔者能为爱,而不能为仁。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不可谓其不爱民,观其恭俭何亚文景哉!而悦弘恭、石显之柔佞,迫死萧望之,恭显叩头以谢而不罪。以太子不肖,欲立他子,史丹涕泣切言不可而不忍。柔者动于情,而非必顺乎理,则于其他有所不恤。唯刚而能仁,以远奸,以去恶。元帝好仁,是矣,而不能恶不仁以远奸去恶,非所谓仁也。
(二)
陈汤一副校尉耳,而欲击匈奴郅支单于,勇士也,欲甘延寿议之,延寿欲奏请于上,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知庸主具臣不足谋也,汤之胆识,何其卓哉!如请之,匡衡等必沮其事,而禽灭郅支之奇功不成矣。其后匡衡劾其矫制之罪也。汤敢矫制,亦知汉重武功,必宽吾所为也。
(三)
汉代威震四夷而无夷狄之患也!为其铁血报怨,非如后世之姑息。匈奴之侵扰边疆,屡出兵征讨,犁庭而扫穴,使匈奴漠南无王庭。苏武曰:“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其后楼兰王杀汉使,傅介子斩楼兰王之首而献之阙下,莎车王杀汉使,亦为冯奉世斩其首级。汉使之尊,杀汉使,虽番王不免于死也,而况敢犯我汉疆哉!苏武曰独匈奴未耳,未能捕戮之耳。至于元帝之世,陈汤以副校尉斩送北匈奴单于郅支至京师,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岂不壮哉!岂不伟哉!匈奴大国之主杀汉使,不免斩首,其他四夷安能免哉!汉家之威于此为极矣!
(四)
夷狄强则骄逆,弱则卑顺,宣帝之世,呼韩邪率众稽颡,岂以其诚哉!与郅支相争不利,遂称臣事汉,欲借强汉以制郅支耳。郅支已死,大患除矣,见元帝非如宣帝之英睿,乃上书称“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其伪也,劝帝罢边备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其诈也,驰汉之备,而己志易逞。突厥启民可汗于隋炀帝岂不恭哉?亲迎帐下拜之,至欲同服为臣矣,炀帝之末,其子始毕可汗乃围之于雁门,矢及御座,微李世民解之,炀帝不免矣。孰知呼韩邪之后不为此哉!侯应议曰:“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而况单于?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也。”韪哉其言也!元帝听之而拒单于之请,明矣,虽惑于石显而害忠臣,至于华夷大计,未尝失也。汉代之人不驰于防夷,所以无后世夷狄之患。炀帝恃强好谀,不听段文振之谏备突厥,几不免重蹈西晋之祸。勿以夷狄衰弱,夷狄恭顺而忽之哉!
(五)
匈奴之为汉患大矣,高祖以三十万大军伐之,而困于平城,几不免,乃有和亲之耻。武帝承文景之余荫,用卫霍之大将,竭天下财货,倾举国兵力,仅乃克之,匈奴既破,汉亦虚耗。陈汤矫制发西域诸国之兵,禽斩郅支单于,威震百蛮,使匈奴日衰,无复边患,灭高、武未能灭之虏,成卫、霍未有成之功,岂不伟哉!汉世获单于者,唯陈汤耳,郅支为匈奴之枭雄,呼韩邪所不能胜,而以降汉也,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灭此二国,任其崛起而不制,则复为中国之患矣。陈汤晓其志而发兵斩其首,防患于未发,不劳官军,集合胡汉之兵,不过数日,所费甚少,且多收获,实为千古奇功!
按周礼,伐夷狄有功有献捷,不必奉王命也,晋破赤狄,《春秋》与之,岂以矫制罪之哉!而佞臣石显沮之,石显不足道,乃匡衡宰相名儒亦妒其功,恶其矫制,以为生事蛮夷,为国招难,殊不可解,盖亦萧望之之流也。元帝内嘉其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优柔之主也。幸有刘向上疏曰:“寿、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服……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比之方叔、吉甫、齐桓,善哉其言之乎!齐桓有尊周攘夷之功,后有灭项之罪,而《春秋》为之讳,功大于罪也,陈汤岂有如齐桓者哉!而抑之不著,悖乎《春秋》之义矣。萧望之之好与人异,匡衡之好妒人功,不如刘向之知义也。
(七)
汉重武功,厚武将,武将在外有专制之权,边将多立奇功。若傅介子之斩楼兰王,冯奉世之斩莎车王,郑吉之破车师、降日逐,段会宗之深入乌孙,诛其太子番丘,陈汤之功尤伟,斩匈奴郅支单于,征服北匈奴。自武帝奋兵四夷,而立奇功之将如此之多也。东汉则班超威行西域,制西域数十国,窦宪破北匈奴,段颎破西羌东羌,斩首五万,亡仅四百。中郎将张修与单于呼徵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匈奴之于东汉,可欺若此矣!岂后世可及哉!唐重武将之权,庶几近之,宋明裁制武将之权,武将不能如意指兵,而以丧师辱国。
武帝以后,匈奴日渐衰弱,分为南北,臣服于汉,陈汤斩北匈奴单于,匈奴不复振。夷狄之强,过百年之鲜矣,乃汉魏四百余年伸威于夷。自汉武帝至晋武帝四百三十年,皆华夏压倒夷狄之时也。惜破于内徙胡人,而三代两汉之势不复矣!
成帝
《大学》曰:“知其所亲爱而辟焉。”人之蔽于亲爱,不复问亲爱者之是非。汉成帝之于舅氏,是也。成帝为太子,数不悦于元帝,元帝欲易之,王凤与皇后、太子同心忧之,成帝至少倚于王凤,感其爱己之恩也,而亲之也甚。即位,重用凤为大将军,委凤以大权。成帝友于定陶王,定陶王来朝,留之,凤劝成帝遣定陶王还国,则不得已而许之,知凤之不贤,欲以冯野王代凤,太后闻垂涕,不御食,而念凤之亲,不忍废。于是王氏五侯,兄弟伯侄相代,汉业以替。若能知所亲爱而辟之,焉有王莽之篡汉哉!
哀帝
(一)
成哀之际,不足观矣,妇人之天下也!成帝之时,王氏盛,一门五侯,哀帝之时,傅氏盛。朝野上下为王氏傅氏争荣枯。王莽尊其姑母,而以傅氏为元帝藩妾,不得为太皇太后,丞相朱博则以师丹抑傅氏尊号为亏损孝道。以傅太后之好恶而黜傅喜。傅喜之黜,称喜之贤;王莽之退,讼莽之冤,岂天下舍王氏傅氏之外,别无辅政之臣乎?哀帝欲封傅太后从弟商为侍中,汝昌侯,当时谏之者独一郑崇耳。傅太后怒之,哀帝终违谏封之。妇人干政,外戚专朝,而汉业以衰,不可复振矣!
(二)
亡汉者,元后王政君之大罪也,西汉之亡,虽有成哀之淫昏,而固无大伤于天下,王莽虽奸,而无诡谲鸷悍之才,非政君授之以权,不得以坐移汉历。方哀帝之崩,即之未央宫,取玺授,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迫董贤自杀,废赵后、傅后,皆令自杀,此汉亡莽篡之机也。呜呼!政君之私爱于亲,兄弟五人并侯,兄凤以大司马辅政,凤死而音代,音死而商代,商死而莽代,世及如此之久,而卒倾夫家。及莽之篡,自顾罪之深,卷卷不欲授以玺,尚何及哉!而论者宽之,多责莽之奸伪无比,恶足以盖其助莽亡汉之大罪哉!元后之寿长,元帝、成帝、哀帝死,而后犹在,虽中有丁、傅之得势,哀帝、傅太后寿不过元后,而终废之,以权授莽。莽之为摄政,为假皇帝,皆与之。莽篡五年,而元后方死。司马氏之夺魏也,亦司马懿之寿大过于魏文帝、魏明帝,明帝死,而诛曹爽以制幼主,岂天也乎,何兴之暴也!不然,吕后之强,封王诸吕,未能代刘,桓温之权,有废立之威,未能代晋。
平帝
(一)
王莽居摄,子宇谏,莽杀之。逢萌语友曰:“三纲绝矣!祸将及人。”即解衣冠,挂东都城门,将家属客于辽东。
父子天性也,不可离,父之于子,可挞之,辱之,而不可杀之,杀子是杀己之身也,子而忍杀,于君于友于人亦何不忍杀乎!虎毒不食儿,虎之凶暴,人皆知之,忍于物而慈于子,人而杀子,是暴于虎也,智者远之矣,不远将祸及于己。逢萌闻王莽杀子,而痛言三纲绝矣,辞官而远徙辽东,可谓明于见几,而全身远祸矣。忍于子,必忍于臣,忍于天下,使其居位,天下必受其残。然吾犹怪其见之尚未早也,当王莽之子获虐杀奴婢,而莽逼获自杀以偿奴命,莽以此得誉士林,称其至公,不以亲子而废国法,重奴之命也。呜呼!莽之伪也,色取仁,饰礼乐以欺天下,众不察之,而望为周公。而莽之忍也,有心者不动乎?莽之诚,而杀子,亦残忍而戕人伦,而以国法盖之,无怪乎佛氏“冤亲平等”之说得入中国也。冤与亲岂可平等乎?亲杀人,亲之罪也,而为人杀亲,抑何忍乎?莽之杀获,莽为祸之始也。世多责莽之鸩杀平帝篡汉,弑君篡汉,莽之公恶也;杀子,莽之私恶也。而公恶源于私恶,察奸者,视其私而已,于父不孝,于臣必不忠;于子不慈,于人必不仁。莽以杀子得名,及得天位,而肆其恣睢,奋其威诈,毒虐生民,甚于桀纣,岂可胜道哉!莽之不仁,始于子,终于天下,忍于亲者必不能仁于人也,可勿察与!孟子曰:“亲亲而仁民。”又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亲其亲,不幼吾幼,而曰仁民,幼人之幼者,吾知其伪也,汉儒之欺于王莽,为淫于谶纬,不明圣贤之学,不察人伦之道也。
而莽之杀子,逢萌曰三纲绝矣,何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道之本而不可易。虽儒教特重之,而百家众教亦弗可离也,而近人谭嗣同攻之,谓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欲“冲破伦常之网罗”,其激也,而启鲁迅之非孝,至于文革之决裂,多父子相告,上下相攻,人伦颠倒,其动乱之极,为祸之大,尚忍言哉!而今人犹多以三纲为非,君子于此不可不辨也。非三纲者,皆谓君以此压臣,父以此压子,夫以此压妇也。三纲之压迫,古固有之,然非三纲之本意也,假之而为虐也。夫所谓纲者,表率也,君为臣之表率,父为子之表率,夫为妻之表率。孟子曰:“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君不尽君之道,则有臣不尽臣之道,位愈高则责愈大,孔孟以仁义,程朱以诚意正心责难于君亦至矣,胡岂曰君可任意宰制臣下也?君昏昧之至,无道之极,可废可杀,伊、霍以废太甲、昌邑,汤、武以伐桀、纣,君子许其大权,圣人赞其革命。君为臣纲,君当尊贤使能也;父为子纲,父当训子齐家也;夫为妻纲,夫当立身修德也。三纲所以维人伦而立人道也,岂可以纲常之压禁而破之!破三纲是毁人道也!古有君压臣,父压子,夫压妻之事,而无三纲,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人人相危,其祸愈烈,必沦于禽兽之道矣!三纲相与者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爱妻贞。古有不仁之君,不慈之父,不爱之夫,然于臣子妇不敢公然虐之,非忌于三纲之道乎?加之以不道之名,有人心者不能无惮也。若无三纲,父子非为天性,君臣不以义合,夫妇不以礼结,怀利相与,则父不父,而忍戕子,子危矣;君不君,而忍戮臣,臣危矣;夫不夫,而忍杀妻,妻危矣。而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妻之于夫亦何忌而不推刃以弑,通人而叛哉?人伦毁,胥为禽兽,必至率兽食人,人且相食矣!王莽杀子,而逢萌曰三纲绝矣!顺三纲之道,父不可以杀子也;废三纲之道,则为王莽之恶者相循而不止,肆行而无忌矣!惟王莽一人三纲之绝至于天下受其祸害,百姓遭其荼毒,况废三纲,人道岂有存哉!为君子儒者,保三纲以卫人道,所自任也!
(二)
莽之得权也,群臣咸称“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庙。”独大司农孙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今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得无非其美者?”然哉斯言也。虚誉过盛,其必不终,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誉满天下,未必非大奸。周公之圣,以叔父之亲摄政,召公且有不悦,莽之贤,岂过于周公哉?孟子曰:“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而莽晏然受之不怍也!
王莽市誉之盛,成败之俗,何与德酋希特勒相似哉?无安天下之功,而颂莽者万民;无积德之仁,而选希者亿兆。比之为周公,拟之为腓帝。莽亦自以周公,而周公矣;希亦自以腓帝,而腓帝矣。其受臣民之颂,尧舜之隆,无此之盛也;周公之圣,无此之多也;孔子之大,无此之极也。周公摄政,召公之贤且有不悦;孔子见南,子路之正且致其疑。莽希何以得此于天下哉?莽文之以周官,饰之以谦恭,而人以圣人望之;希鼓之以意志,煽之以民族,而人以上帝崇之。莽以行欺天下,希以言惑群民。虽其奸伪威诈之过人,而其能得志于天下,亦岂非乘风俗之蛊,因士民之欲而成哉!西汉之末也,谶纬之说日昌,以刘向、匡衡之贤且为之导;德意志之末也,排犹种族主义之风日盛,以康德、黑格尔之哲且以为说。遑论其流俗从而相靡,小人鼓而相辅也!故风俗不可不正也,学术不可不明也,不然,奸盗者假之以欺世害民,岂胜言哉!莽受尊之隆也,而以其书班之郡国,比于《孝经》,希享誉之盛也,而其书《我之奋斗》刊之天下,同乎《新约》。莽欲复成周之典,希欲复大德意志之地,既恃威强,而外伐四戎,血战欧巴罗,而匈奴不服,苏联相抗,黩武于外,而海内困耗,民怨沸腾,所不同者,希亡于外,莽死于内也。当其盛也,指挥而以为天下可定;当其亡也,坐守一隅而惟恐敌之兵临。希自毙,而其尸不为人见,莽之死尤惨,为商人杜吴所杀,汉军复肢解其身,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虐毒过于桀纣,复以《六艺》文奸言,而受罚也甚于桀纣,天报之不爽,有如是哉!
世多罪莽之篡汉,鸩杀平帝,此其公恶也,吾则甚怪其于子孙,抑何贼忍也!其居家也,中子获杀奴,而莽逼获自杀,以为己公;既居摄,子宇非其隔绝卫氏,莽又杀之,以为大义灭亲;子光私报窦况,莽切责光,遂母子自杀;为帝,孙子宗服天子衣冠,逼宗自杀,太子临与莽聚麀,赐临死。莽之诸子,于莽生前,且为莽诛之殆尽,呜呼!莽欲传之万世,而诛杀其子如此,传之于谁乎?父子之恩,三纲五常于莽绝矣,而犹缘饰经术以欺天下乎!而谁复受欺?莽之极恶也,而为至愚也。于子孙且惨毒若斯,而况天下乎?不能得于子孙,而能终得天下之戴乎?方其兵败命穷,尝导莽以篡汉之国师刘歆、大司马董忠、卫将军王涉且欲劫莽,众叛亲离,可谓甚矣。犹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以孔子自比,以天命自慰。始之谦恭欺世,中之以威诈篡汉,终之以愚怪亡身。欺人者而终以自欺,食人者而终为人食,甚矣夫!人皆知希特勒屠犹太,侵吞世界之恶也,而孰知其临终亦欲毁灭德国哉!希特勒以民族主义相号召,非以诚也,利用之耳,驱其族人争血于苏俄而不恤也。逮其势穷,国都失守,乃欲炸平德国,何疯狂至此哉?彼以日耳曼人弗能成功,则当灭亡,而其种族之争为非汝死,则我亡,为不并存之极端也,彼之言曰:“吾人或毁灭,但当吾人毁灭之时,则与世界同尽!”此其欲毁灭德国之机也。呜呼!其狂也极矣,不仁也至矣!夫民族主义,以爱族保群也,而希特勒驱其族以成其吞噬世界之狼心,不惜数百万军民之血以争之,其横也,既以世界为敌,欲侵吞各国,而其困也,愤战败之耻,国民之不欲死抗也,复以其民族为敌,而欲毁灭德意志,曰此民族既败,不值复存于世界也。孟子所谓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抑吾有言,圣人之功德泽于天下后世,民受之而不知之也;明王之功德惠于苍生,民知之而不誉之也;英雄之功业福于百姓,民誉之而不群起相颂也。庄子曰:“至人无誉。”王船山曰:“无誉者,圣人之直道。”圣人一心忧济元元,教化天下,岂冀士夫百姓之誉哉?夫有冀誉之心,则为私矣,安能与天地同其大而为圣人也?明王以治天下为务,兢兢业业而不敢怠忽,又何暇以礼乐自文,殉匹夫之情,博四海之誉?英雄以功业为重,虽有冀誉之心,而以为人之毁誉,何益损于吾之功业,吾自立其功业,何必悦人?而不过求人之誉也。尧舜禹孔之圣也,而立诽谤之鼓,求谅直之友,以闻过为善,犹不免伯成之讥,叔孙之毁;孝文光武之明也,亦有法重之谏;郭子仪之贞也,亦贻奢侈之谤。夫至于群起相追,称颂至极,欢呼不已者,非奸则伪也。此非世之祥,乃妖也,如海上逐臭之夫,园中绕王之蜂,衰世之兆也。若王莽、希特勒之受众誉若此其甚,使民欢呼若此之狂,而其为恶流毒若此之极,则信乎斯言之不谬也。呜呼!圣人不欲受人以誉,亦不轻誉于人,虽以令尹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犹不许以仁,且不得智。誉之过情,君子耻之,长人之傲也;誉之非实,君子恶之,长世之伪也。王莽、希特勒以小人奸雄而乘圣人之器,坦然受非常之誉而不惭,其愚也,使长傲遂非,而自以为承天命,自以为圣王,自以为救世主,无及我者,无所忌惮,而忠谏之言何从入哉!至于垂亡,犹以天命自欺也。受极誉于一时,而流谤于千载,身死名毁,两无益也。王莽、希特勒之恶,人皆知之,而誉其者之恶,逢长其恶者,孰能察之?有大恶之作,必有助成大恶之群氓也。
(三)
观人不可徒观其貌与其所举之名,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被服儒者,而为大奸慝者,自古有之矣,若王莽是也,史载其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品行无议矣,有谦恭孝慈之行矣。然而其后弑君篡国,杀子毒民,与桀纣秦二世同归,其所行者似乎是,而其所以者非,所由者妄也。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使莽诚为孝悌,何为篡弑之逆,作乱天下?所为以博名誉,伪也。莽之尊崇儒术亦至矣,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此举之盛,比元帝之崇儒而有过之,然而乱天下也甚,则观人岂可以其名也。莽之成功,颂德者以万人,至三万言,比之周公,其败也,乱贼臣子诟之,同之暴秦。后世曾国藩之恶,亦何亚于莽哉?佞者拟之程朱矣,更比之孔孟,以王莽比周公,诬周公也,以曾国藩拟程朱及孔孟,亦何辱孔孟程朱哉?观其实也,乃与之反。莽败而其名去矣,国藩成功,至今妄誉不绝。论者徒见其举儒教之旗而平洪杨异教之徒,而称卫道之大功,是圣战也,甚者曰:“微文正公,斯文其绝矣。”呜呼!孔子所以自任,而以称之国藩,佞媚之甚,亦何贬中华斯文,无曾必绝?诛洪杨之甚,谓必灭儒?而曾氏之杀戮,不留遗种,滥及无数平民,非但秦兵之暴也,王莽之毒也,彼皆不计焉,或视若无睹,虽知之不以为意,以为杀伐虽过,卫道之功不没,足以盖之矣。岂非徒观其名,不察其实之昧乎!与汉之伪儒称颂王莽,拟之先圣,同为惑也!
姑无论其重文而轻人命也。胡不观其他也?吴章名儒,而莽杀之,以腰斩磔尸之酷,并禁锢其弟子,沮莽之专权也,于此而有敬儒之意哉?黄巢之好杀也,逢儒不杀,而莽之所以待异己之儒如此之酷,曾不如草莽盗贼也。洪杨固有得罪于圣教者,焚经侮圣矣,然不过数月而改,改毁为删。天地会等会党非有为天主之教而得罪圣教,曾氏亦欲芟夷而无遗种。洋夷传教惑民矣,有民抵制之,乃曾氏杀民以媚洋,又非但不攘夷教以卫道,乃杀攘之者,且助之而容其蔓延也。至后观之,莽借儒术以欺天下,而乱过桀纣,暴秦,幸光武败之,莽婴族灭之惨,曾氏鸷悍之才过于莽也,无所不用其极,借洋夷以灭太平,惜乎无有明王如光武者起,使国藩受恶来、张豺之诛也!然太平虽灭,捻军继起,反清者未尝止也,清延祚几半百,而未尝有一日之安,政日失,中国之民日苦,辛亥虽覆夷清,建民国,而混乱犹不休也。继之倭人侵华,毛统之,旋为文革之祸,礼乐学术涂地以尽,邓氏除毛氏弊政,改革开放乃始安。垂百年而皆乱日也,生民之死者多矣,所以延误发展者甚矣,胡俗戾气之延如此之久,汉官威仪不可复矣。国藩之毒倍屣于王莽也,莽败而婴万世之贬,国藩成而受当代之誉,以成败论英雄,岂理之公乎!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陶扬鸿:读史通论:元、成、哀、平帝十三篇(7744字)发布于2021-07-06 00:3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