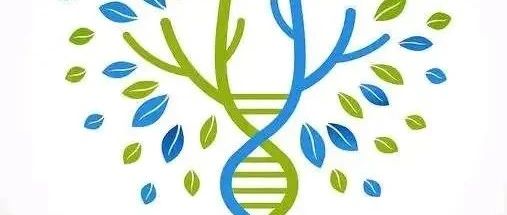曾国藩不足道也,无知浅学者推为大儒圣贤,于今乃有曾国藩热。其行事之恶,非圣贤,乃汉奸民贼,乃伪儒,败类之儒,予为文述之矣,其学术之驳杂,予读其全集,而知之,当更于此辨明之,明曾国藩非儒家,乃法家,或杂家。庶使人知其为人不之仁,而学术亦不正,人与学术盖相由也。
曾国藩幕僚有汪士铎者,此人甚反儒,乃异端之尤,维护满清,却赞太平天国之反孔删经,曰:“洪、杨删论语,去鬼神祭卜等类,功不在圣人之下。”以政治主张不合,而去天国,事满清,为曾国藩、胡林翼之幕僚。汪士铎尚法家,而诋儒学虚浮空洞,“徒美谈以惑世诬民”,不能救世。且至上非圣人,曰孔子之弊在于“过仁、过文”“讳言兵”,“长于修己、短于治世”。且提议朝廷“禁读《中庸》等大话”,极反理学,乃扬言欲将全天下道学家如除草杀禽般除尽,甚于李贽之狂悍矣!彼望秦始皇复起,统领白起、王翦、黄巢、朱温、张献忠、李自成等猛将或剧盗,“为苍苍者一洗之稂秀”,“杀无道以就有道”。张杀戮,崇屠夫盗贼,如此极端怪论,虽五四文革之反孔反儒亦未如此疯狂。而曾国藩乃引而用之,称其“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胡林翼更称其“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呜呼!诋毁圣学,猖狂,丧心病狂,无忌惮,吾不知其所谓醇儒者何在!曾胡自诩卫道,指责洪杨之反孔崇天主,何反于汪氏异端侮圣之尤称之用之?而处理洋务,则杀抵制洋教之民以媚洋,吾不知其为真心为辟异端,卫道也否?盖以扶满剿粤,义不足,特举卫道之旗以升其义乎?呜呼!卫道以名不以实,且肆行杀戮,保腐朽之虏廷而污道。儒运不终,式微而不可挽,诚小人乘君子之器害之。曾胡之亲汪士铎,亦其本质为法家也。
邓之诚为汪士铎《乙丙日记》作序尝详细论列汪士铎于曾国藩之影响:“尝疑曾胡定乱,必有为之谋主者,文正自谓学商鞅耕战之术,文忠则综核名实,皆近法家。及观悔翁所论,尊主权,重名实,峻刑戮,深恶理学及承平拘牵之事。文正自咸丰十年驻军祁门,又悔翁平昔所主张何其所见之若合符契也。及细译曾胡书牍,乃至悔翁实尝为之策画。”言曾氏近法家,发其藏矣,而犹未至也,吾将揭露其为法家之本质。
曾氏之为人,商鞅天资刻薄之类,其性之残忍,于其言见之。《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国家承平日久,刑法尚宽,值兹有事之秋,土匪乘间窃发,在在有之,亦望公正绅耆,严立团规,力持风化。共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若有剧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辕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满清之刑律也严,而曾氏犹嫌其宽,谓乱世当用重典,非祖述韩非之说乎?光棍亦须格杀,何其为刑之滥也,此亘古所无之奇葩之法!
曾氏又曰:“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夫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又见夫粤匪之横行,土匪之屡发,乃益嚣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抢风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鱼肉之。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已。”曾氏暴戾之气充满于此矣,以为当杀甚多乎?而咎有司之不捕戮?其祖曾子对犯法之民,曰“哀矜而勿喜”,曾氏与之悖。民之犯法,教之不足也,民之为乱,官逼之也,官逼民反,曾氏不反思官之贪暴,而辄防民之为乱,何以民为敌也?欲厉行诛杀,虽滥不顾,悍然不避严酷之名,非申韩之不仁,而孰与为此?而曾氏极矣!
曾氏又与其主咸丰疏曰:“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 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可谓君之鹰犬,而民之贼也!纯用重典,非法家乎?韩非犹曰一味诛杀则暴,亦不可,而曾氏之为,韩非之不如也!
曾氏《与魁荫亭太守》:“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呜呼!以残忍杀戮而使民之守法尊官,非商鞅、申韩之惨刻,而孰忍为此!残忍亦有由乎?
《复陈岱云》:“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洗此辈。”悍贼不不能剿,则欺弱民,暴戾之气又见!
《与李次青》:“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所出告示,严厉操切,正合此时办法。但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须能行之,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大局或有转机。”老子异端也,而有近道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曾氏欲使民畏己,“斩刈草菅”,是谓儒者之言乎?尽古今之不肖,险如商鞅、申、韩不忍为此言,而曾氏悍然言之,其所诵孔孟之书者安在?商鞅曰民弱则国强,曾氏曰民畏贼甚于畏我,则或有转机,与民为敌,不虑杀戮之滥,曾氏真非人类也!而其用陵迟剥皮等酷刑对待俘虏,曾氏之本质为法家,岂不明明哉!
或谓予:“昔读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误以曾国藩儒学素养甚好,今乃知其非儒也。《圣哲画像记》不当与孺子阅,恐误学子。”
予曰:于此文可见其学术之驳杂!如左庄马班并称,列入圣哲,左丘明犹不失为圣人之徒,庄子异端,马迁杂学,班固文儒,不可谓之圣哲。葛、陆、范、马并称,葛为诸葛亮,诸葛杂于申韩,其学亦驳。韩、柳、欧、曾、李、杜、苏、黄,韩欧固辟异端,不失为正,柳宗元佞佛,韩愈责之矣。杜甫固儒家诗人,李白则儒道思想兼具,或谓李白信仰道教。苏黄学术亦驳杂,朱子辨苏氏之学多杂老庄,船山所谓老庄之儒。而曾国藩皆列入圣哲,吾故曰以此文见曾氏学术之驳杂。清末理学家夏震武批曾国藩“加赋抽厘, 聚敛苛于鞅、晏;就地正法,用刑酷于申、韩。以庄、老为体,禹、墨为用,词章、考据为归,择术驳于陆、王。”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曰:“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中,有异端,有杂学,有驳儒,有考据之学,其可并列哉?而汉代大儒董子、扬雄,隋之王通、朱子之后学真魏,明代大儒薛胡,东林顾高,明末大儒王船山皆不在其列,可知其识向矣。
曾国藩曰:“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文章概论刚柔,子曰刚毅近仁,曾氏曰阳刚之美为义气,阴柔之美为仁气,其亦不知学与文矣。司马相如辞赋之雄者,并非儒者,推入圣哲,亦不伦也。
曾氏学术十分驳杂,彼应用最精者为法家与黄老,以法家治人,以黄老为全身之术,徒假借儒家名号,以笼络士子,博理学大儒之名,吾曰曾国藩甚虚伪,诈伪之流。儒名美,为正统,故假借儒家之名。观彼之文,于儒学唯泛泛而论,其儒学功夫实为肤浅,伪装较似耳。
其人阴骘,其学驳杂,乃彻底之实用主义者。曾国藩称圣贤,如许衡配享孔庙。而船山曰:“许衡之慝百于杨墨。”称许衡是小人之巧而贼者。曾国藩之慝,非但许衡比也,其学行比之许衡相去犹远矣!
许衡之学,犹纯然儒也,事夷主,而晚年有愧也,未为蒙古助虐以残害汉人也,欲导蒙古以德,不能化之耳,而船山以为辱身枉己,鄙恶之甚,况曾国藩乎!其学行之去许衡尤远!
曾国藩不导满清以德抚民,悍然施行严刑峻法,曰:“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吾故曰,其去许衡也远矣!遑论圣贤,比肩程朱哉?先儒之非议许衡,以其失节,为儒者之羞,其他,无甚可议,曾氏直是残忍好杀。
曰:儒生不当崇拜此类人。
予曰:论人则残忍好杀,诈伪不诚,论学则驳杂不纯,多杂异端,有何可尚哉?
予复于其全集取其言论以明曾氏为杂学。曾国藩曰:“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老庄之旨,以此为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荣趎赢粮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国藩每读之,不觉失笑。以仲尼之温、恭、俭、让,常以周公才美骄吝为戒。而老子犹曰:‘去汝之躬矜与容智。’虽非事实,而老氏之所恶于儒术者,举可知已。庄生尤数数言此。吾最爱《徐无鬼》篇中语曰:‘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又曰:‘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取老庄如此。
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士,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称关羽为帝,惑于流俗,其言是之,其行违之。
曾国藩《照复洋人》:“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阁部堂接得贵大臣照会。内称“现在未能极力弹压,立拿凶犯正法”等。因查五月二十三日之案,滋事凶犯,现已严饬新任道府赶紧查拿,断无任令凶徒久稽显戮之理。只缘是日津民聚众过多,不能指实何人为首,何人为从。近日访得数名,已令其先行拿案,严刑拷讯,务令供出伙党,按名缉获,处以极刑。以申中国之法,以纾贵国官商之恨。大约数日之内,必可弋获多名,断不至再事迟延。贵大臣尽可放心。”严刑处置抗洋,抵制洋教之中国人民以媚洋人。
曾国藩《纪氏嘉言序》:“从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则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为妄;从乎后世之事变、人心言之,则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略同。”其取称佛教如此。夏震武谓其学术驳于陆王,岂无由哉!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其取老庄明矣!虚无清静,无为自化,此老子之道也,曾氏以为体乎?“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庄荀之异如冰炭,而曾氏兼用之!虚无清静,圣人所不言,老子言之,曾氏以为体,圣人之言,曾氏以为用,将谓圣人不及老子,或赖老子补之乎?其溺于异端,而谓圣人不足可见矣!以老庄治心,而以孔孟治身乎?其学之驳杂,分裂体用,可见一般。
曾国藩又曰:“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曰:“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
夏震武责其以“以庄、老为体,禹、墨为用”,是曾氏自道之矣,益见其据。
曾国藩尚教其弟以老庄:“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国藩又曰:“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又与弟家书称:“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自道于老庄之爱尚,屡见之矣。又曰:“十一月信言观看《庄子》并《史记》,甚善。”其爱尚老庄,影响诸弟矣。曾氏学术之驳杂也如此,于此益见。
老庄清静,申韩惨刻,乃曾国藩兼用之,忆船山曰:“得志于时而匡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志虽诐,智虽僻,操行虽矫,未有通而尚清狂,穷而尚名法者也。管、商之察,庄、列之放,自哲而天下且哲之矣。时以推之,势以移之,智不逾于庄列,管商之两端,过此而往,而如聩者之雷霆,瞽者之泰、华,谓之不愚也而奚能!故曰‘哲人之愚’,愚人之哲也。然则推而移嵇康、阮籍于兵农之地,我知其必管商矣;推而移张汤、刘晏于林泉之下,我知其必庄、列矣。王介甫之一身而前后互移,故管商、庄列,道岐而趋一也。一者何也?趋所便也,便斯利也。‘小人喻于利’,此之谓也。”王安石之用商韩而好老庄,曾国藩之用申韩而以老庄为修养,兼用之矣,无非趋所便也,申韩便于治人,无所斟酌,老庄便于修身,无须谨严。
至于大禹,道统圣人,岂可与墨子并称哉?墨虽尊禹,实非禹伦。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禹俭于饮食,而诚敬于鬼神,平时穿着不恶衣食,至于祭祀礼服则注重华美。宫室卑,而兴修水利甚伟,非墨子一概节俭,而为俭啬也。孔子知禹,墨子不知禹,学之偏也。大禹重祭祀,衣礼服必须华美,则于丧葬亦必重盛,岂如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葬礼太俭而反人情矣。
大禹平时节俭,于重要场合事情,则不节俭,大方而无惜,墨子则一味节俭,无论何事皆节之,非善学大禹者也,孔子善学禹者也,不耻恶衣恶食,而于祭祀也甚重,食不厌精,听乐,三月不知肉味,其艺术之情操精神,为圣之时者,岂墨子可及哉!曾国藩以禹墨并称,不知禹也,抬高墨子矣!大禹兴修水利,毫不节俭,不惜任何费用,此为保护人民也,保人不惜财!祭祀,衣华美之冕服,所以重礼也,为祭祀之诚也。若墨子着敝衣祭祀,何以重礼?何以为诚?君子当俭则俭,不可执于俭。
曾国藩《与何廉昉》:“承询及欲购书目,鄙人尝以谓四部之书,浩如渊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耳。‘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二十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五子》暨管晏、韩非、淮南、吕览等十余种是已。‘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二十余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书,皆赝作也,皆剿袭也。”子书推崇韩非与《淮南》《吕氏》杂家之书,于此见之。
又《复李希庵 》曰:“鄙人尝谓古今书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书,不过数十种。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韩非、淮南、鹃冠,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编集众家之精以为书。本根之书,犹山之干龙也。”曾氏所谓本根之书,韩非,《淮南》、《吕览》皆在列,其为学之杂过于诸葛矣!
曾国藩问学于理学家唐鉴,博理学家之名,而实调和朱陆,《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曰:“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具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宗朱。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凡泾阳、景逸,黎洲、苏门诸先生近姚江者,皆遍摭其疵痏无完肌,独心折于汤雎州。雎州尝称姚江致良知,犹孟子道性善,苦心牖世,正学始明。……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陆王驳儒,杂于佛老,而曾氏称之,曾氏之驳,尤过陆王也。贬斥辟陆王之朱学者,谓不如汉学者,曰:“陈建之《学蔀通辨》,阿私执政;张烈之《王学质疑》,附和大儒,反不如东原、玉裁辈卓然自立,不失为儒林传中人物。”岂为程朱之徒耶?
又极称庄子,曰:“庄子《外篇》多后人伪托,《内篇》文字,看似放荡无拘检,细察内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钱珩石给谏日:‘尧、舜、巢、许皆治乱之圣人,有尧,舜而后能养天下之欲,有巢、许而后能息天下之求。’诚至论也。”夸庄子之书若天地,以尧舜与庄子寓言之巢许皆圣人,是谓孔子与庄子皆圣人耶?
再翻阅曾国藩全集,感觉曾国藩之学,非但驳杂,乃大驳杂,其为法家本质,又可谓杂学人物,所谓学宗程朱者安在哉?佛老,程朱之所辟,而曾氏则与儒并称,陆王,朱子之所辩斥,朱学者之所排,而曾氏务为模棱两可之说,韩非之险怪非圣,而曾氏推为本根之书,并《吕氏》等杂家之书推崇之。至于以老庄为体,以禹墨为用,孔孟之体用安在?称庄书若天地,则孔子置于何地?谓圣人之言为用,是以圣人无体乎?而异端老庄皆有体乎?凡此之类,不可胜举,以曾国藩为大儒,过高之誉,以为儒者,且使人不能无疑。而其述孔孟之言泛泛,引称老庄,则不能掩其崇慕之诚,而知曾某阳为儒者,阴为异端也。其为人之不仁,岂为其学术之不正乎?由此而言,曾某之为人,当否之,其为学,亦当废之矣。
清末理学家夏震武痛斥曾国藩曰:“天津之役,湘乡曾不敢以一语加于异族,法已垂亡而事事听其要求,其视管仲、狐、赵尊王攘夷之勋,不可同年而语矣。加赋抽厘, 聚敛苛于鞅、晏;就地正法,用刑酷于申、韩。以庄、老为体,禹、墨为用,词章、考据为归,择术驳于陆、王。合肥、南皮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世徒咎合肥、南皮之误国,而不知合肥之政术、南皮之学术,始终以湘乡为宗。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湘乡早岁自附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博理学之名。及功成名立,则亟亟焉唯词章、考据之倡,以仇视性理。出洋留学,杀人割地,为中兴首作俑焉。政术乱于上,学术坏于下,邪说横流,世道人心扫地以尽,率天下为禽兽夷狄,而中国将不可以复立,湘乡固不得辞其责矣。”岂非公论哉!人之议曾氏者,徒罪其人,而鲜有非其学者,今辨明其学术,非儒,为法家,为杂学,为异端,甚乃异端之不如,未有不仁,而学术正者也。为学驳杂,行事亦往往错乱无则矣。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陶扬鸿:辨曾国藩非儒家,本质为法家,或杂家(7053字)发布于2021-07-06 00:4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