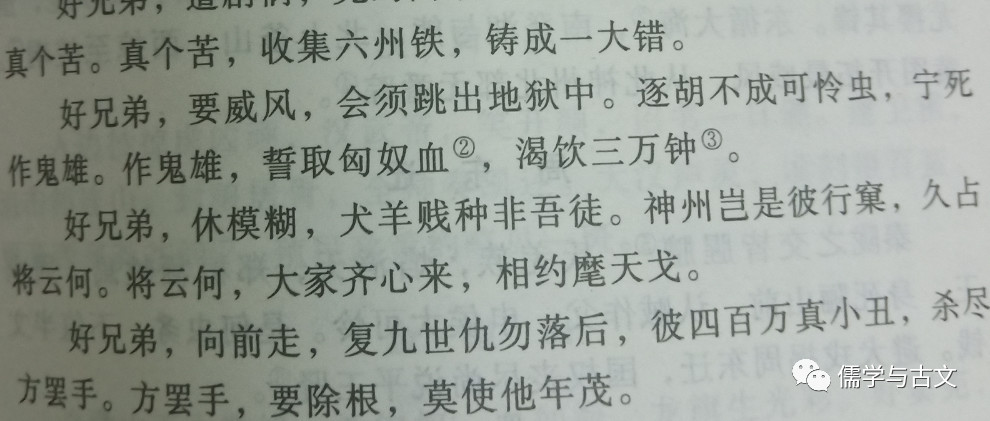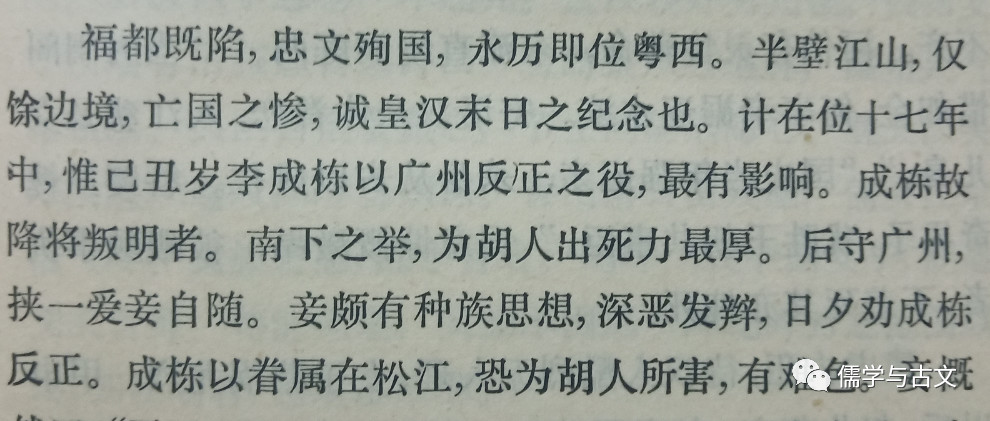韩非与老子关系颇重,道家重虚静,申韩法家亦贵虚静,而为帝王之权术,专为驭人用矣!老子流为申韩,何也?熊十力先生曰:“道家下流为申韩,非无故也。儒者本诚,而以理司化;老氏崇无,而深静以窥几。老氏则去儒渐远。夫深静以窥几者,冷静之慧多,恻怛之诚少。”老子一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启法家悍然为不仁之法,不仁之术矣!又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皆流弊不小。老子知仁不深,而轻视仁义,乃欲绝弃仁义。申韩皆学于老,取其南面君人之术而更加之以阴诡惨刻,遂成秦之暴政,决裂三代之礼教,可胜叹哉!夫无仁体仁心,冷静之慧适资奸人暴者之用,而大有伤有于仁矣。道家本源不深,其弊固至此也。法家无本,而其毒尤烈矣。
以如下文句见韩非与老子之渊源之深: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
韩非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韩非曰: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
韩非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有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
君臣,义也。儒家以为君臣以义合,而在韩非眼里,君臣全成了势力,以势合,他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臣是惧怕君主势力才不得不事。君臣之间不能信任。不能信人,只能威之以势,以权术相驭,在韩非之学,就是法术势,没有义。此其重术势之故也,而于术尤重。
就是夫妻之间也不能信任,他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儒家的推诚之道在韩非哪里是根本没有的,韩非看世道政治非常黑暗,因此反对仁义慈惠,认为只有法术势才有效。
韩非以人性好利,他为君主安全这样着想:“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与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因此对妻、子,大臣都要小心防备,曰:“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晕围於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
韩非还直说:“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君臣之间就是互相计算的,“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因此要“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申韩法家就是不好处看人性,所以提倡严刑峻法。
韩非是尚法不尚贤,重术不重道,然而韩非所讲的术,也不是一般人能学习的,胡亥自小习于韩非之书,看他引用韩非之言驳李斯,为人君当享乐的借口。刘禅也自小受申韩之教,按刘备对刘禅遗诏曰:“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刘备被称为仁君,三国正统之君,却以商君书,申韩之偏邪惨刻之书教子!然而胡亥弑于赵高,刘禅降于司马,申韩之效,又焉在哉?有些智商的君主,学习申韩,阴惨刻薄寡恩矣。其有智者如曹操,杨坚,武曌师之亦不长久。用申韩而得令名者,不过刘备,诸葛亮耳!王道易易而久,虽有庸君,能温仁守成,亦能安而不亡,霸术繁难而促,虽有雄君,亦难免于亡。
再看看韩非喻老,对老子南面之术的利用发挥,如老子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章,韩非曰:“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邦者,人君之辎重也。主父生传其邦,此离其辎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主父之谓也。”
韩非又曰: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矣。简公失之于田成,晋公失之于六卿,而上亡身死。故曰:“鱼不可脱于深渊。“
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则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是胶鬲贤而费仲无道也。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文王举太公于渭滨者,贵之也;而资费仲玉版者,是爱之也。故曰:“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老子很多话被韩非利用发挥为权谋诈术了,老子之机有以启之。
司马迁把老子和韩非列为一传是有深意的,申韩皆源于老子,韩非吸收了老子的南面君人之术,将之发扬光大,愈深愈暗。法家变得阴暗,不得不说老子有以启之。道法并崇者,不足怪,崇道者崇毛,也不足怪。申韩是硬性的恣肆,老庄是软性的恣肆,其为恣肆,一也。佛教能进入中国,因为接近道家,马列能进入中国,因为接近法家墨家。
道家常谈无为,法家也讲无为!申韩慎到皆源于老子,仔细看其书可见。
申不害《大体》曰: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富者,人臣之事也,非君人之道也。
又曰: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固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
慎到曰: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巳。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
韩非《扬榷》曰: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叁伍比物,事之形也。叁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根干不革,则动泄不失矣。动之溶之,无为而攻之。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上不与共之,民乃宠之;上不与义之,使独为之。
道家讲虚静,法家也讲虚静。
韩非《解老》曰: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无术者,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虚,则德盛;德盛之为上德。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
韩非如此发挥老子的虚静无为,发扬道家的无为,就是无不为,独裁统治!看似什么都不做,却把什么都控制好了。虚不是为了虚,虚是让人摸不透,不让人知,意无所制,而实皆制之。这是法家的术,术是无为的,看似无为的,是隐性的,法是有为的,是显性的,术示人以无为,强调严刑峻法,而无不为,什么都干涉。老子的无为无不为,就被韩非如此发挥为阴深的帝王权术了。
韩非《主道》: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
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韩非笔下,君主装得神秘莫测,什么事都不做,却让群臣悚惧而莫敢不从。无为真是一种权术啊。“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这种权术对君主很有利啊,无为而治,有功,就称颂君主之贤,无功,就把臣当替罪羊!真高明,但不道德啊!
王船山很疑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众怒之不可犯,众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为至今而不绝邪?志正义明如诸葛孔明而效其法,学博志广如王介甫而师其意,无他,申、商者,乍劳长逸之术也。……任法,则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则天下逸而人主劳。”申韩者,专利人主者也。逸己劳人,任法不尚贤。
儒者为何要距申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只是因为申韩严刑峻法,还有申韩的险暗,提倡一些阴谋权术,坏人心术,一些君主政客看了这书,学了这个,就拿这套去控制人,去整人。先儒距之,而未公开其权术,今可公明之。而批判老子,也是老子透露了些机秘,使申韩得发挥利用之,启申韩之不仁,开申韩阴险之术。
老子之流为申韩,如: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飙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对于老子的术,朱子,船山都看出了,朱子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谷。”所谓谿,所谓谷,只是低下处。让你在高处,他只要在卑下处,全不与你争。他这工夫极离。常见画本老子便是这般气象,笑嘻嘻地,便是个退步占便宜底人。虽未必肖他,然亦是它气象也。只是他放出无状来,便不可当。
问“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说话都是这样意思。缘他看得天下事变熟了,都於反处做起。且如人刚强咆哮跳踯之不已,其势必有时而屈。故他只务为弱。人才弱时,却蓄得那精刚完全;及其发也,自然不可当。故张文潜说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於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变诈刑名。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船山又曰:伊尹曰“咸有一德”,据纯德之大全而言也,故曰:“德二三,动罔不凶。”不可生二以与一相抗衡,生三以与一相鼎峙也,明矣。又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非散殊而有不一也;又曰“无自广以狭人”,非博取而有不一也。是故道,非可“泛兮其可左右”也,非可“一与一为二,二与一为三”,三居二之冲,“冲而用之不盈”也。诚“泛兮其可左右”与?师左则不协于右,师右其不协于左矣。“诚冲而用之不盈”与?将虚中以游于两端之间,自广以狭人,天下之德非其德矣。老氏以此坏其一,而与天下相持,故其流为刑名、为阴谋、为兵法者,凶德之所自生,故曰贼道也。夫以左右无定者遇道,则此亦一道,彼亦一道。以用而不盈者测道,则方此一道,俄彼一道,于是而有阴阖阳辟之术,于是而有逆取顺守之说。故负妇人,嬖宦寺以霸,焚《诗》《书》,师法吏而王。心与言违,终与始叛,道有二本,治有二效,仁义亦一端,残杀亦一端,徜徉因时,立二以伉一,乘虚择利,游三以乱一,乃嚣然曰:“凡吾之二三皆一之所生也”,而贼道者无所不至矣。老聃之幸不即为天下乱也,惟其少私寡欲知止,不以天下为事耳。不然,又岂在商鞅、李斯下哉!
我们来分析老子一些话:
老子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家不尚贤,法家也不尚贤,为何不尚贤,就是为了使民不争,不争,安稳好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是只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而在精神上让人民空虚,在意志上让人民脆弱。商鞅的弱民理论盖出于此。商鞅《弱民》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 结果是让人民“无知无欲”!这样的人民多好统治?无知,不知争取权利,无欲,不会威胁自己统治。就是有智慧的人亦不敢有所作为。
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大学讲新民,提升民智,而老子则以为善治者,不是提高人民的智慧,而是让人民变得愚蒙,人民难以治理,是因为他们智慧多,智慧多,就想法多,因此老子要反智,“绝圣弃智”。开启了法家的愚民,商鞅曰:“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老子曰绝学无忧。
老子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圣人讲无私,是各成其私,老子讲无私,则是成其私,相似而实大不同!无私的目的是为了成他的“私”!不敢为天下先,后其身,他只在背后搞事,不以身犯,而坐收利益,很滑头。这话就是帝王之术啊!法天,是帝王法天,如天一样神明伟大,“不自生,而能长生”,他不自己去处理事情,让手下去做,而安稳无患。
老子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这话被申不害“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发挥利用。
儒家亲亲尊贤,道家不尚贤,儒家劝君主以身作则,君为臣纲,道家则劝君主隐藏自己,虚静无为,法家也是,儒家主张光明正大,开诚布公,道家,法家则讲神秘,诡秘,不可示人之术。道家无为,是少做事,法家无为,是让君主不要做事,什么都让臣下去办,但老子说无不为,又开启法家的 密法了!道家,法家讲主逸臣劳,哪会让君主以身作则?
庄子曰: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
君主如龙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玄默如深渊一般沉静让人不测,发作则如雷霆之威使人畏惧。
庄子又曰: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馀;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彫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
看来无为,就是好利用天下啊!君主无为,臣下有为。在这方面,道家和法家何其相似!
看看汉初道家司马谈就这么介绍道家统治的高明: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後,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其抑扬儒道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司马谈这句话,指出了儒家道家的不同,正如我所言。司马谈贬儒,批评儒家让君主为天下表率,就是我说的以身作则,这样使君劳臣逸。司马谈的批评恰恰证明,儒家是约束要求君主最严的,不是为君主服务的,而是要君主为天下服务的,所以君主不能安逸,要多勤政。尚书讲无逸。
一些人指责荀子流为申韩,其实荀子是纯正的儒家,和申韩大不同,他反对阴秘之术,主张君主为天下仪表。荀子曰:“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君主要为万民表率,上梁不正下梁歪,反对道家法家这种说法批评,曰: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
荀子又曰: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这和老子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针锋相对!儒家要明之,道家要愚之,儒道相反也。
和韩非的“君无为于上,臣悚惧乎下”,也是一种对立,荀子反对那种阴谋权术,让臣下害怕自己。
儒家君臣之间是温情脉脉,君臣如父子,或如师友兄弟,而道家,则君主显得神秘莫测,岂可亲?法家,则更诡秘莫测,如雷电鬼神之可畏,岂可爱?
朱子想象三代君臣的亲密关系,感叹秦尊君卑臣以后,不可见矣!这是道家法家的影响,他们搞那种神秘诡秘的君人南面之术。道家法家其实是一两面的,道家贤于法家,惟其少私寡欲,不尚刑耳。
秦用申韩之术,却二世而亡。
秦始皇居住隐秘,史载: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阳宫。
他儿子胡亥也读申韩之书,赵高就劝二世居住深宫,不要与群臣相见,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而二世最后被赵高逼弑而无人救。
真是君以此制臣,臣亦以此制君!君主还是要光明正大的好,玩神秘,迟早会出问题。
现代新儒家马一浮也指出老子的流弊:周秦诸子,以道家为最高;道家之中,又以老子为最高,而其流失亦以老子为最大。 吾谓老子出于《易》,何以言之? 因为《易》以道隂阳,故长于变。 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这个道理,老子观之最熟,故常欲以静制动,以弱胜强。 其言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此其宗旨。 在退处无为自立于无过之地,以徐待物之自变,绝不肯伤锋犯手,真是全身远害第一法门。 任何运动他决不参加,然汝任何伎俩,他无不明白。 禅师家有一则机语。 问:二龙争珠,谁是得者? 答曰:老僧只管看。 老子态度便是如此。 故曰: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他看世间一切有为,只是妄作,自取其咎,浅陋可笑,故曰:不知常,妄作凶。 他只燕然超处,看汝颠扑,安然不动,令汝捉不到他的败阙,不奈他何。 以佛语判之,便是有智而无悲;儒者便谓之不仁。 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 把仁义看得甚低。 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是自然之徒,天是道之徒,把自然推得极高,天犹是他第三代末孙子。 然他却极端收敛,自处卑下,故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老子所谓慈,与仁慈之慈不同,他是取其不怒之意。 故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 所谓俭,与治人事天莫若啬之啬意同,是收敛藏密之意,亦不是言俭约也。 不敢为天下先,即是欲上民者必以言下之,欲先民者必以身后之之意。 后起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他只是一味下人,而人莫能上之;只是一味后人,而人莫能先之。 言器长者,为气之长,必非是器,朴散则为器。 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故谓之长。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唯其下物,乃可长物。 老子所言朴者,絕於形名,其義深密。 故又曰: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朴字最难下注脚。 王辅嗣以无心无名释 之,愚谓不若以佛氏实相无相之义当之为差近。 惟无相,故不测一切法,无相即是诸法实相。 佛言一切法,犹老子所谓器。 言实相,犹老子所谓朴。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犹生心取相也。 相己無相,故曰神器。 诸法实相,故名朴也。 )此皆言弱者道之用也。 又曰: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 此皆言反者道之动也。 此于《易·象》消息盈虚,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之理,所得甚深。 然亦为一切权谋术数之所从出。 故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但较后世权谋家为深远者,一则以任术用智自喜,所以浅薄,老子则深知智术之卑,然其所持之术,不期而与之近彼。 固曰:以智治国,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知其两者亦稽式。 (王辅嗣训稽为同,犹今言公式。 盖谓易忘之迹皆如此也。 )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玄德深亦,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惟其与物反,所以大顺,亦是一眼觑定反者道之动,君向潇湘我向秦,你要向东他便西。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 他總與你反一調,到臨了,你總得走上他的路。 因为你若认定一条路走,他便知你决定走不通。 故他取的路與你自別,他亦不作主张,只因你要东他便西,及至你要西时,他又东了。 他总比你高一着,你不能出他掌心。 其为术之巧妙如此。 然他之高处,惟其不用术,不任智,所以能如此。 世间好弄智数用权谋者,往往失败,你不及他深远。 若要学他,决定上当。 他看众人太低了,故不甚爱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刍狗者,缚刍为狗,不是真狗,极言其无知而可贱也。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他虽常下人,常後人,而實自貴而賤人,但人不觉耳。 法家如商鞅韩非李斯之流,窃取其意,抬出一个法来压倒群众,想用法来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人人皆入他李某中。 尽法不管无民,其实他所谓法,分明他所谓法,明明是他私意撰造出来的,不同儒家之天秩天讨,而彼自托于道,亦以众人太愚而可欺了,故至惨刻寡恩,丝毫没有恻隐。 苏子瞻说其父报仇,其子杀人行劫。 法家之不仁,不能不说老子有以启之。 合隂谋家与法家之弊观之,不是其失也贼么? 看来老子病根所在,只是外物。 他真是个超客观,大客观的哲学,自己常立在万物之表。 若孔子之道则不然,物我一体,乃是将万物折归到自己性分内,成物即是成己。 故某常说:圣人之道,己外无物,其视万物犹自身也。 肇法师云:圣人无私,靡所不己。 此言深为得之。 老子则言:圣人无私,故能成其私。 明明說成其私,是己與物終成對待,此其所以失之也。 再举一例,更易明了解。 如老子之言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孔子则云: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作,复,是以物言。 恒,感,是以心言。 老子连下两其字,是在物一边看。 孔子亦连下两其字,是在自己身上看。 其言天地万物之情可见,是即在自己恒感之理上见的,不是离了自心恒感之外,别有一个天地万物。 老子说吾以观其复,是万物作复之外,别有一个能观之我。 这不是明明不同么。
道家,法家的心都比较冷,道家是冷静,法家是冷硬。其道是纯客观的,其法术是纯机械的,没有道德意义。道家阴柔,法家阴狠,道家贤于法家处,制人不欲伤人耳,法家制人又欲伤人,束缚人于刑罚之中。道家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使人麻木,亦足以销人之真元,而人不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老子之机深矣!
老子有权,是执中无义,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老子无适无莫有矣。没有这个义,所以不是君子。“大道泛兮,其可左右”,纵横于两端之间,无为而无不为。
朱子好学深思,深知老子之术。伯丰问:“程子曰'老子之言窃弄阖辟'者,何也?"朱子曰:"如'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是它亦窥得些道理,将来窃弄。如所谓'代大臣斫则伤手'者,谓如人之恶者,不必自去治它,自有别人与它理会。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曰:"此正推恶离己。"曰:"固是。如子房为韩报秦,撺掇高祖入关,又项羽杀韩王成,又使高祖平项羽,两次报仇皆不自做。后来定太子事,它亦自处闲地,又只教四老人出来定之。”又曰:“汉文帝曹参,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肤,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将去。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它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
阴鸷如秦,强暴如楚所以不敌高祖,善用老氏之术也。
孔子无可无不可,乃通变之道;老子无为无不为,乃机变之术。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其直;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尘,是其曲。直则诚,曲则伪。孔子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只是择善避不善。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似之,以不善为资,有幸灾乐祸之意。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不患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圣人之达也。老子曰:知我者希,则我贵,异端之傲也。孔子曰:以直报怨,以徳报徳,圣人之平也。老子曰报怨以徳,异端之矫也。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劝学,老子曰:绝学无忧,与劝学相反矣。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圣人之不离群,而求同道也,老子曰:“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纯纯。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淡若海,漂无所止。众人皆有已,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则故意与世俗大众异,欲超群而立于群之上。
孔子曰: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老子则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孔子只是诚,善善恶恶,老子却说,不善的人,也要善待,得善,无是非矣,其实只是伪。为了得善而已。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此亦君人南面之术,欲为人上,则先下人,欲居人前,则先后人。不敢为天下先,见先前之弊,而资之夺之,而无害。游于上下前后之间,而全其身。看似不争,而使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道家的不争,目的是“莫能与之争”
老子之术虽深远莫测,然终不敌圣人之诚。
道言玄,儒言明,老子曰:“玄之又玄。”《大学》 曰:“明明德。”荀子曰: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玄者,何为也?天下莫能知,不俾人知。明者,明于天下,使天下皆知之。孔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圣人无隐。
诚则明,诚则化,诚能尽性,至诚可以前知,诚者成己而成物,至诚无息。荀子之为纯正儒家,亦曰养心莫善于诚。荀子曰:“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
道家讲道,其实讲的多是术,术者无恒,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儒家虽不明言道,而其实皆道也。术再高明再玄妙,终有偏处,失处。船山指出老子之弊:“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故于圣道所谓文之以礼乐以建中和之极者,未足以与其深也。”用术虽逸,而非常安,用道者,常安。道无不周,术有所限。以柔制刚,可对猛人,不可对养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而无馁之君子。
道家讲权谋,儒家也不是不讲权谋,不讲阴谋,讲阳谋,孔子曰:“好谋而成。”是圣人未尝不谋也,圣人贱阴谋耳。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圣人不轻言权,必在可以共学适道与立的基础上言权。
圣人察变,于常道中察变,圣人通变,通权达变,老子之术,机变耳。圣人万变不离其宗,终为常。异端变化莫测,则为反常。儒家崇正,道家尚奇。
道家法家之术是制人,让人服从,儒家之道是服人,使人心悦诚服,其别大矣!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陶扬鸿:论申韩等法家源于老子,老子之机为阴谋权术之祖(12910字)发布于2021-07-06 01: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