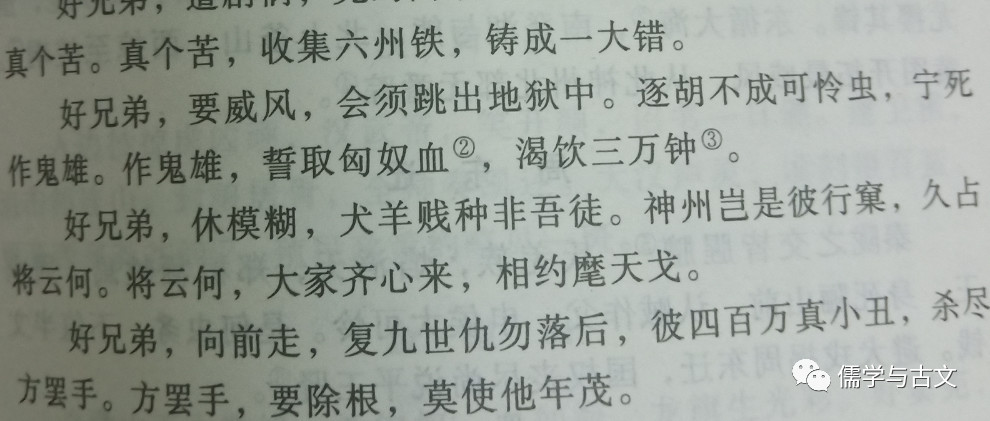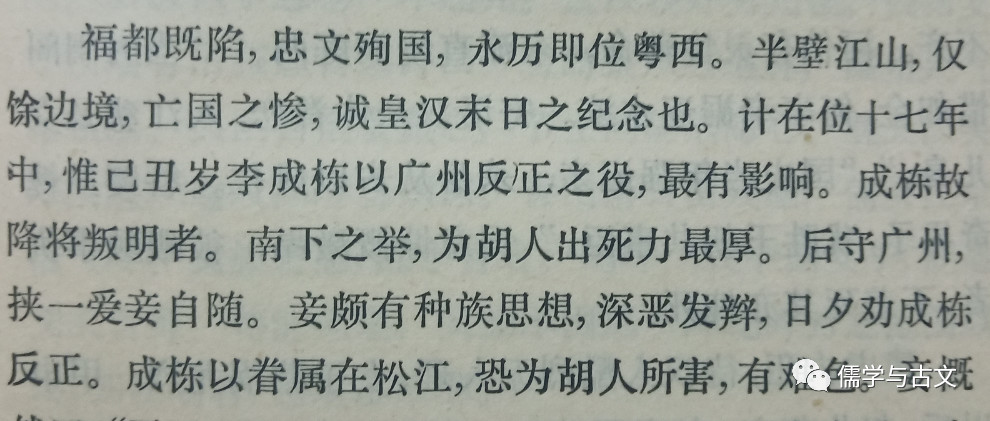有网友悟真者谓余曰:学问深奥的是君子文,辨论是非的是小人文,不学无术的是蛀虫文。希望人人博学。
余曰:小人乃辩是非?辨是非者君子,颠倒是非者小人。荀子曰:“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又曰:“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应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辩杨墨执一之失,折告子仁外之蔽,斥许行同耕之伪,辨墨者为二本无分。当此异端横行,邪说歪理蔓延之时,君子安能沉默无辩?辨偏邪之理,明中正之道,君子之任也。君子于大是大非前必辩,惧大义之亡也,大义不可不严;于似是而非处必辩,虑理之乱也,至理不可不明。
当今需要如孟子,王船山这样富有雄辩的儒者。异端横行,歪理充斥,不能无君子之雄辩以距之也。杨墨盛于战国,孟子辞而辟之,孔道以明。宋儒言孟子有英气,谓英气甚害事,孟子一书多辩论,颇露锋芒,英气之所在也,英气于学道有妨,而攘斥异端,放淫辞,息邪说,须如此英气。孟子当战国异端横行之时,不得不如此,使孔子生于战国,亦不能无辩论,惟孔子辩论更全而已。所谓冲和温润圆融,于仁也,义则严厉斩截方正,不可模棱两可,不辨是非。子温而厉,亦非一味温和。而其曰:“见义不为,无勇也;非其鬼而祀之,谄也!”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亦岂非斩截之言?一味温和者,乡愿也。 君子好善恶恶,其于善人善言,温煦如春风,仁道以和而亲;于恶人恶言,严厉如夏日,义道以严而敬。仁如春生,义如秋杀。仁道须广,义道须严,仁道不广,则有偏党;义道不严,则有姑息。韩愈曰:“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于仁言之。仁义之人,其言亦凛然也,霭如而可亲,凛然不可犯。有人知仁不知义,则胥成迂缓软弱,能包容而不能分辨,则只为糊涂肤浅。 君子之仁言霭如风之和煦,君子之义言凛然日之光明,其仁言为生气,非疲软之气,义言为正气,非戾杀之气。凡仁义本于中正,必以中正用。中则有立,正则无失。
仁本刚以柔用,义本柔以刚用。仁不本刚,则妇人之仁,沾沾之惠而已,所斥妇人之仁者,只凭感情用事,随所感,而不知性理,仁义是情,更是性,一般人只知情,鲜知性,温和慈善,是个老好人,而不可许为仁。而仁不以柔用,人亦难以接受。或以严刑成民之仁,适以激之反而已,仁以宽,成康所以刑措百年为盛治,未闻以严行仁者,季康子欲戮一不孝以善风俗,而孔子驳之,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父子讼之不善也久矣,是则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无矣。不教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诛也……今仁义之凌迟久矣,能谓之弗踰乎?”仁者行教化,劝人以善,不教而杀谓之虐。义本柔以刚用,有人打着以有道伐无道,大义灭亲的旗号,却是滥杀无辜,戕害同枝,不本柔道也。圣人之伐无道,本其恤民之仁;君子之不得已灭亲,本其安国之心。非为快快之怒耳,惟凭快快之怒,一怒不可止,则长乐杀之气,而为不仁矣。故义必本于柔,养其怒,而不妄发,发之中节。以刚用,义以诛强暴,果断诛杀强调,不可姑息也,惟以刚用,而义伸其浩然之气,显其明明赫赫之威,立其坚贞不可移之大节。 余又谓悟真: 辩论是非为小人文,则孟子、朱子、王船山皆为小人文矣!岂有此理哉?然则君子不辩,惟小人辩乎?辩亦不可不分也,岂可一概否定?
悟真曰: 我等非君子,此好彼差,圣人也违,非小人乎,何来辨哉,王阳明大儒乎,王船山君子乎,孔子教主乎?
余曰:余等不敢以君子自居,然须以君子自勉。人当有为君子之心,不可曰我不想做君子,亦不愿为小人,欲中立于君子小人之间,则乡愿而已,而或恐终不免为小人。学问深奥者未必为君子,君子未必学问深奥。醇正质实者为君子,君子必醇正质实。基本义理不明,何谈学问深奥?
悟真曰: 君子和君子文又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余曰:君子文醇正质实,非必学问深奥。君子文醇正质实,不临深而为高,不堆砌以为富。 余作《文章论》,自然心问曰:依你之见,则世间好文何在?
悟真谓曰: 在于你自己心底深处, 余曰:空话。谓自然心曰:凡达情,载道之文皆好文,如六经,语孟。文必宗经述圣,经者,文之原也,圣者,道之中也。
悟真谓余曰: 没有别人的协助,辨论再历害也是空话,应该务实不务虚。
余曰:辩论怎么要协助了?辩论不在厉害,在正与是,辩论不求胜人,期在明理。君子不务虚,亦不务实,而是务本。观兄之言,理多舛谬。
悟真曰: 人人务本,也不一定是非不断,批这批那,辨论无休。
余曰:有些人爱故作高,其实是空话,已落空无,而离道矣。如佛者有谓无心,程子曰只可谓无私心,不可谓无心。陆子静说不要有意见,以意见为邪,为非,朱子就斥之,曰意见非皆邪,皆非,要说没意见,只能说没私意见。如君又说不要辩论,而君子有所辩,有所不辩,非皆不辩也,大是大非,岂可不辩,无谓谩骂攻击,何必辩哉?君子为理而辩,非为辩而为辩,为理而辩则是,为辩而辩则非,辩以明理则是,辩以胜人则非,辩仁义则正,辩功利则邪。岂可不分是非正邪,而一概否定辩论,而以不辩为妙?君现在就与我辩论辩与不辩,岂非自违其旨?以不辩为高,大是大非处亦不辩,何以为君子?颠颠是非黑白,不辩,何以为人?以不辩为妙,人皆能不辩,岂不辩皆妙哉?在其何所辩,何所不辩。此皆贵无贱有,而不知无有无之是,亦有无之非。无私心,是也;无心,非也。非要是非不断,也非要批这批那,辩论不休,只求辨明义理而已。余亦不喜无意义之辩论,无谓之批判。
悟真曰:王安石以自然规律哲学行变法之事,深知百姓苦难,不怕丢官,可见思想超前,观其言辞包罗天地,万物合一,最后的隐居生活,脱离事非,我觉得也是圣人。
余曰:以王安石为圣人,可谓妄誉。王船山批王安石为小人,虽然过激,然安石于君子之道,固有缺矣。脱离是非者未必为圣人。观君之言,义理多浅薄舛谬,望君多读圣贤之书,充实义理,提高思辩。君既以不辩为妙,又何违不辩之旨,累与吾辩此。君多留言于我,我未回复,今辩者,诚有不容已也。没批佛,代表什么,皆爱好,思想无所宗主,只是爱好,未诚心研之,学之,体之,则知之亦浅矣。
孔子曰:“余之于人,谁毁谁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余之于人,谁毁谁誉,自孔孟以后,义理之不可不明也。善哉船山先生之言曰:“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为,匹夫匹妇之与知,圣人莫能违也。然而君子之是非,终不与匹夫匹妇争鸣,以口说为名教,故其是非一出而天下莫敢不服。流俗之相沿也,习非为是,虽覆载不容之恶而视之若常,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则恶不知惩。善亦犹是也,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阂,而天良在为;非秉日月之明以显之,则善不加劝。”余之辨是非,亦秉此旨。天下公是,不必喋言其美;天下公非,不必繁言其恶。流俗习以为尚,而不知其恶,则明正其非;流俗漠然已久,而不知其美,则当表彰其是。或似是而非者,辨其非;实是而见非者,明其是。 又论是非,为义也,于仁则不可论是非,如于父母兄弟夫妻不可论是非,论是非则恩薄。君子于是非有所论,有所不论,义君是非,仁不论是非,为公论是非,不为私是非。非只论是非,亦非如异端之泯是非。异端曰天下无绝对之是非,而不论是非,所谓无绝对之是非,小是小非,大是大非则为绝对。泯是非,以是非为争,然公是公非不可泯,泯之则人不知所从矣。 是非有公私,公则明理,私则启争。天下有公是,不可非;有公非,不可是。今有人毁岳飞,为秦侩翻案,则是颠倒是非。君子论是非,只为明理明道,非标新立异以哗众取宠,党同伐异以争门户闲气。
为此,遂作《原辩》文:
庄子曰:“圣人议而不辩。”非不辩也,大道明,是非未混,无须辩也。辩论生于是非,是非纷纷,不得其定;是非混混,不得其别;是非颠倒,不得其正,而有辩论。观乎《论语》,孔子亦有辩论矣,如子张以为达者,为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孔子以为闻也,非达也,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路以正名为迂,而孔子斥其野,以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疑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死为不仁,孔子以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亦以管仲不死公子纠,而又相桓公为不仁,孔子以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岂如匹夫匹妇之为谅,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或问以德报怨何如,盖有主张以德报怨者,孔子反问何以报德?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子路与季氏谋伐颛臾,以为不取,后必为子孙忧,孔子斥其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以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远人不服而不能来,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而谋动干戈,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宰予疑三年之丧,孔子不直与之辩,而问其食稻衣锦安否?予曰安,孔子则曰汝安则为之,君子则食不甘,闻不乐,居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以其非君子也。出而叹予之不仁,岂无三年之爱于其父母?此不辩之辩也。不与之辩,而辩在 其中。长沮,桀溺耕,孔子使子路问之,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讥孔子之救世为徒劳,劝其隐居避世也,孔子亦不直与之辩,而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斥其与鸟兽同群,而己非斯人之徒也,亦不辩之辩也。圣人之辩也,约而达!
六经之辩希,孔子之辩约,道一世治,是非明于天下,无庸多辩。至于战国,礼乐愈坏,是非愈乱,百家蜂起,而诸子各逞其雄辩,思以其学治天下。而其辩亦有别,孟子之辩正,庄子之辩奇,墨子之辩诬,公孙之辩诡,苏张之辩夸,商鞅之辩强,荀子之辩文,韩非之辩刻。而孟子最能继孔子者也,其学最正。雄辩滔滔而不诡于正,辩杨墨执一之失,折告子义外之蔽,斥许行同耕之伪,辨墨者为二本无分。与齐宣王辩,使宣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好辩名。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诸侯放恣,处士横议,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则君子恶能不辩?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其志也大,其心也公,则其辩也正,岂同苏张纵横以取富贵禄位之私哉!
战国人君多竞于利,孟子甫见梁惠王,则问何以利吾国,孟子则以大夫亦问何以利吾家,士庶人问何以利吾身,上下争利则国危,流极于篡弑,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千取百,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止。仁义则无此弊。其言危矣,欲以震其昏心,警其利欲也,斥利欲之害,则显仁义之无不利也,孟子之辩,何其卓伟!至于以好战责梁惠王所以虽尽心而不得民,劝齐宣王反本,发政施仁以得天下之人,则无敌于天下,孰能御之?又辨独乐与众乐等,辩益恢宏矣。
此与侯王之辩也,辩仁政也;与士人之辩,则辩学理矣。陈相舍陈良而从许行,欲使滕君与民并耕,孟子反问其何不自织?陈相曰害于耕,耕者,农之事也,君与民并耕,孰治国?百工之事不可耕为,则治天下者岂独可耕为乎?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治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以明工之不可不分。又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谓耕之外,尚有更重者,圣人忧民之无教,圣王忧天下之不得人,尧舜不耕,而治天下,民受其教,天下得其人,自有其耕,何忧于耕哉!不忧其大,而忧其小,是不知忧也。又曰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弃中原之正教而从南蛮之偏方,是用夷变夏也。孔子没,门人服丧三年,子贡复独居三年,何忠于师也。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奉之,而曾子以为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韩愈所谓“世无孔子,不在弟子之列”,有若岂及孔子哉?而陈相师死则遂背之,于师不忠也;从南蛮之教,于道不知也。下乔木而入幽谷,悖也。且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其斥许行之小道可谓详且明,醇且肆矣!
告子以仁义为矫糅,谓性为杞柳,义为桮棬,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驳之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仁义固有,非待矫糅,矫糅之,则亦戕贼之矣。告子又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谓不可以一偏盖全,而以性如湍水之无定也。人性之善,如水之就下,顺之也,自然也,本能也,搏而跃之,激而行之,可使过颡在山,有致之者也,非水之本性也,以明人性之善。不以水之或跃,而疑水之就下;不以人之或恶,而疑人之向善。
告子复以食色为性,仁内义外,孟子亦以白马秦人之喻折之。观孟子与告子之辩数矣,告子才高,而其辩则近理也,弥近理而愈乱真,则不得不多为之辩。于世所流行性善恶混,性无所谓善恶说,孟子又曰乃若其情则可为善,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谓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固之有之也,不思而已。其为恶者,陷溺其心也。天下之口相似,耳相似,目相似,口相似,心岂不同乎?心以理同,然则人之性亦同矣,岂或善,或恶哉?又以牛山之木为喻,人以斧斤伐之,牛羊又从而牧之,斩其萌蘖,人以为未尝有材,此岂山之性也?山之为荒,伐牧之也;人之为恶,陷溺之也。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善虽人性固有,亦须培养也。其论人性可谓不惮其烦矣。非好论性也。盖性不明,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天下不治,性者,穷本极源之学。若以人性为恶,则为恶者不惭矣,皆为恶也,不过顺其本性耳;若以人性有善有恶,则为恶不惧矣,各有善恶,恶所难免也;若以人性可善可恶,则善不足慕,恶不足耻矣,性无所定,则生无所从也。孟子惧之,而言性善,力斥告子矫糅之论,义外之说,言性善,则知人性之尊,知人性之尊,则自尊,而勇于为善,耻于为恶矣,孟子性善之说,岂非有功于名教哉?
任人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而难曰必以礼乎?孟子直指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为诡辩,驳之曰:“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以其人之说还驳其说,可谓高明矣!世之诡辩者以此谓礼之不足重,而启逐利蔑礼之俗,孟子驳之,可谓正矣!
又与弟子论舜之怨慕,不告而娶,尧舜禅让,伊尹、孔子之行事,以辨世俗之诬,为圣贤辩护也,则不暇一一说之。凡孟子之辩,一为明仁政,二为闲邪卫正,三为辩诬,四为论性。大雅君子之辩也,宏而实!
孔子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荀子曰:“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又曰:“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应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圣人之辩,明其大体,士君子之辩,析其几微。小人之辩,混其轻重,乱其是非。圣人之辩全,君子之辩正,小人之辩诡,不可不分也。或以不辩为高,曰辩者皆为争意气,辩论是非皆为小人,岂非空言相矜,以偏盖全,并诬古今圣贤哉!谓圣人议而不辩者,道明世治也,见世乱道微,异端横行,邪说诬民,非毁正道而不辩,何忍乎?非可沉默而沉默之,不仁也;可辩而不辩,不智也。故君子必辩,辩道之正偏,理之是非,闲邪卫正,经世明道。此孟子所以不得已于辩也。辩之善者,正一世之俗,回天下之惑;辩之利者,教一国之民,理天下之政;辩之雄者,愧小人之心,夺奸人之魄。
当辩而不辩,若孔子不与子张辩闻与达之别,则人多以闻为达,而自欺者多矣;不与子路辩正名之要,则人以名教为迂,而犯分者多矣;孟子不与陈相辩耕与教之轻重,则人以衣食为道,而逐利者多矣;不与告子辩人性之善,则人以恶为自然,而无耻者多矣。尧舜之明帝,孔子之圣人,伊尹之大贤,为世俗所诬而不辩,则人以尧舜孔伊为口实,而为小人者多矣。故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知其不得已,则体其仁心矣。
非若曲士之辩,为辩而辩也。田巴之毁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其辩也,不若不辩,不合道也,有害于世也。鲁仲连折之,使终身杜口,堂堂正正之辩也。小人为利而辩,曲士为辩而辩,学者为真理而辩,君子为明道而辩,不可不辨也。至若有清汉学家之辩,争门户,妒道真,而反宋儒,毁程朱,其心也私,则其辩也多诬,兼曲士小人之辩也,君子恶之!曲士之为辩而辩,则务以胜人;小人之为利而辩,则务以损人。或以不辩为高,皆默而不辩者,乡愿也,正邪而皆是之,是非而皆混之,君子小人而皆媚之,不辩以显其高,而不露其破绽,亦不得罪于人,其为己也善,为术也巧,而心何凉薄也!人不见其非,则不以为恶,而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以紫乱朱,以郑乱雅,似是而非,欺世盗名也!君子远之!
附:
或谓余曰:你对中国正统思想极其挑剔,却对群中的西方思流尽情放纵,也确实让人失望。华夷之辩,不会仅仅只是说说的吧。
余曰:好的思想,虽是西方的,亦当接收。坏的思想,中国的异端,亦何可不辟之!于民族为华夷之辨,于思想为正学异端之辨,异端有中国之异端,有外国之异端,有百家之异端,有儒门之异端。何况,吾之儒群多讲儒学,西学很少吧。群中心远,飞龙在野皆对儒学有较深较细之研究。现在醇儒很少,我觉得你的思想很驳杂。然贬斥鲁迅,吾见有更驳杂者与我辩论,乃孔子鲁迅并论为圣人。今人大多思想价值观驳杂混乱,寻其醇正者少之又少。
曰:为了打败内部敌人,索性引入外部敌人,把内部彻底毁掉,可以么?
余曰:吾尝以儒家有三辨,华夷之辨,义利之辨,人禽之辨,皆作论释之。今更加一辨,正学异端之辨。后有暇,作异端论。整顿内部,非毁掉内部。和良戎,非引恶戎。异端出于孔子,自宋兴理学以来,多言之。孟子距杨墨,贾董批商韩,程朱辟佛老,牟宗三斥马列,今有余东海批鲁迅,辟异端乃儒者一贯传统。而宋儒之辟异端,主要辟佛,以佛之言愈近理而弥乱真。亦以排斥外来文化过度侵略,使本土文化式微也。
曰:当年东林党联虏灭寇,知道么?
余曰:不知,吾知抗清义士孙奇逢为东林党出身,还有黄宗羲。
曰:你看看,东林党就这么几个有真才实学的,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么?那些东林党坑皇帝,坑武将,简直坑到死,你居然视而不见。
余曰:我基本支持东林党,其中虽有混进去的小人,而大多为君子。可读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东林学案》或孙奇逢的《理学宗传》。
曰:大多为君子,而且还是好人呢,那种专办坏事的好人。这样的君子越来越多,嘿嘿。
余曰:办坏事非好人,好人不办坏事。你这是逻辑颠倒。
“今天下之言东林者,以其党祸与国运终始,小人既资为口实,以为亡国由於东林,称之为两党,即有知之者,亦言东林非不为君子,然不无过激,且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终是东汉党锢中人物。嗟乎!此寱语也。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昔绪山、二溪,鼓动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设教,可谓之标榜矣。东林无是也。京师首善之会,主之为南臬、少墟,於东林无与。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奄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於域中,延於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清议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议臧氏之窃位,议季氏之旅泰山,独非清议乎?清议熄而后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红本,故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碍砥柱也。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黄宗羲
曰:你自己看看是谁没逻辑,东林党你还基本认同了。
余曰:明之不遽亡,华夏之复起,犹东林之节义为支撑鼓励也,明末三大儒王船山、黄宗羲等犹承东林之遗风也。
曰: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儒,不是说儒真的是个毒品,而是后来的儒生越搞越过分,禁锢了人的思想。现在我感觉你也开始慢慢禁锢自己的思想了。
余曰:因为你们都不了解儒学,你也只是个儒学门外汉。还没有踏进儒学的殿堂,至于里面究竟是什么,能清楚么?就好比你逛街,看到一家酒店,至于酒店里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人你并不了解。
曰:你这话能骗我吗?我不说精通儒学,起码知它大概。你说的那个儒学,是你自己编织的理想国。
余曰:我所学的儒学,是真实存在的,我所崇敬的历代大儒也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宗教神话,乌托邦,是真实的文化生命,道体,人格。所述皆承先圣先贤,为历史记载,学林公案,非如异端韩非之杜撰,庄生之寓言。
曰:而且我尤其讨厌你割裂百家的联系,把儒道法总是要对立起来,其实质是造成文化割裂和思想禁锢。你要知道,儒道法只是一体多用,一体三面而已,你搞一个孤立的儒家,是不能成功的。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越来越喜欢自命清高,国家也就越来越乱。汉朝儒家还自己也学学其他的学问,所以办事情很靠谱,唐朝其实也这样。到了重文轻武之后,儒家就自命清高,不可一世了,搞个事情就非要对着经典,一字一句的扣,打个仗,还要讲仁义,治流民,让他们不造反自己安心饿死,这简直只有傻子才会干的。说的形象点,就是教条主义!
余曰:你学的中国文化多是小道异端,还未进入中国文化中心之所在,对儒家正学研究得太少。
曰:你还要说这个小道异端,本身这种说法就是儒生自己定义的,你凭什么说我是小道?我还说你儒生是小道呢。你这么干,就是割裂,就是追名逐利。而且我可以说,你这么干,不会发展儒道,而是让儒道灭绝。因为你搞一家独大,在我们这个并不是儒家一家独大的世界里,只会让人民更加憎恶儒家。为什么近代那么多人反儒?就是因为它一家独大。
余曰:未进入中心,未达本源,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只在一隅,而进入中心,基本可窥全豹。四书五经,不用说,理学书籍,建议读周子通书,张子正蒙,胡子知言,二程遗书,四书集注,近思录,理学宗传,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还有船山遗书,船山遗书主要读周易内外传,尚书引义,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思问录。
曰:周之前,除了易经(如果不算儒家注解过的易经,易经也没有),其他的都不存在。你可以说商没有大道吗?就是算到春秋战国,那时候华夏的思想也不仅仅只是四书五经。你就专门把它们剥离出来,不就是私门独重么?居然还说他们就是大道,这符合罗辑吗?
余曰:异端也有可取之处,异端与邪说有别,异端是偏,邪说是离。宋明儒有些排斥异端太过,以为邪,王船山把老庄、申韩、浮屠三大害亦有激也,吾之于异端,非同宋明儒之排斥,乃为统摄批判也。基本儒门之外的都是异端,余东海有斯言,吾同之。凡不符合中道者,皆异端,符合中道者为正学。如华夏斥四方为夷也,儒家为中道,判其他为异端,亦未为不可。虽然,中国之内之亦有夷狄,儒门之内亦有异端。或为夷狄迁入中国者,或染夷俗而弃华风者;或为外儒而内异端,或浸染异端而偏离圣道者,王船山所谓有老庄之儒,有申韩之儒,有浮屠之儒,今则有马列之儒,皆儒门异端也,而佛家则称佛家之外的学问为外道。而佛家则称佛家之外的学问为外道。基督教亦判别教为异端,或为邪教,耶教对异端是用武力镇压,暴力排斥,而有宗教战争,儒家不然,对异端进行学术辩论,或行教化。
曰:儒门之外的都是异端,你这本身就是儒生一家之言,凭什么说服别人?
余曰:现在人多崇尚多元,吾则以一元统多元,多元则乱,一元则独,一元统多元,一不孤,而多不乱,带领多元更好发展,而正学者不入异端,异端者不入邪说。佛道无儒为之主,则走得愈偏,而引发邪气祸乱,齐梁隋唐是也。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天地之运行,江河之流逝。吾非在说服人,只是判教。人各有所尚,学佛者以佛为最高,学道家者以道家为最高,吾亦不非之。然观其所尚,亦知其志趣见识矣。
曰:你凭什么说道家不能统领其他家呢?又或者儒家不能统领其他家呢?还是因为你儒生自己的判断。儒家倒是统领了其他家,最终有了两次亡天下,这如何说也?我从来不信胡洋的文化,这是其一;我也从来不觉得诸子百家哪一家最高明,这是其二。其三,我也从不说儒家坏得一塌糊涂,反而也认为儒家有他可取之处。
余曰:吾虽与道家多有辩论,且颇反感一些道家的傲慢,然在心目中还是比较高看道家的,不及儒家中正,而于百家为重矣。你是中立,无所宗主,是杂家。关于杂家,借鉴当代儒者余东海的说法:杂家的特点是博采众家,兼容并蓄,“于百家之道无不综贯”。杂家有两种,一种对各种文化体系一视同仁,主张“文化无高低”;一种则有一定的文化倾向或立足点。立足于佛,为佛门杂家,如李贽、南怀瑾。
立足于道,为道门杂家,如淮南王刘安,其编著的《淮南子》一书糅合了阴阳、墨、法和部分儒家思想,主要的宗旨是道家。《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归入“杂家”类,准确的说应该称为道家杂学。那些号称“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的道家,大多实为道门杂家。
立足于儒,为儒门杂家,简称杂儒。杂儒首先是儒家,这是他们的基本立足点,也是他们高于一般杂家和各种异端外道的关键。但他们学识驳杂,立足不稳,常常游移不定,这是他们成不了醇儒的原因。儒门杂家之作称为儒家杂学,如《吕氏春秋》。历史上三大儒门杂家是诸葛亮、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更是儒门第一大杂家。”
曰:你觉得管子是哪家?
余曰:管子近法家,是正宗法家。我比较认可。非商韩可比。
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可是管子提出来的,你觉得他不是儒家么?
余曰:管子亦异端,商韩颇有些邪。儒者所批,亦多为商韩之类的法家。
曰:墨子也是异端,杨朱也是异端,所有人都是异端,就儒家是正道,而且这话还是儒家自己说的,你觉得你作为一个不是儒生的人,你自己信么?
余曰:衣食足而知荣辱,船山驳之。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言凡民,不可言君子也。士有恒心,而有恒产。民无恒心,因无恒产。且有人为富不仁,富而无礼者亦有之矣。经济高涨,而道德下滑之国亦有之。儒家内部也有异端,并非只针对儒门之外。如中国之内亦有夷狄。
曰:说白了,你的道理就是,我们儒生说儒家是大道,是正道,所以它就是大道,正道:反之,我们儒生说其他家都是异端,所以就一定是异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儒生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自己看看你的逻辑,跟桀纣有区别么?就是一种独夫民贼的形式了。
余曰:此非个人感觉,乃是理见得如此。然则孟子,程朱,船山皆为独夫乎?正学异端之辨不可不严,如华夷之辨不可不严,君只知华夷之辨,不知正学异端之辨,未深于学也。热血有余,理智不足。关于此,吾以后会有系统之文章书籍论之。大略言吾所见。此非一言能尽也。君曰不以为儒家坏得一塌糊涂,亦有可取之处,则儒家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先存偏见,以儒家为坏也,没坏得一塌糊涂,君还是偏向百家,儒家只是有可取之处。此乃承近代以来对儒家之偏见。只是比反儒派略好一些。主张百家合一者大多看轻儒家,偏向百家。呜呼!淡化正统,强调偏统旁枝,岂能复兴中国文化乎?
曰:你说我先对儒家一家存偏见,可是你却是对除了儒家的所有家都存偏见,那么谁的偏见大呢?而且我没有说儒家坏额,你可是把儒家之外的所有人当阶级敌人斗的。正统,本身就是你儒生自己定义的,你却把你自己的一家之言强加给别人,强行升级为大道,你觉得合适吗?
余曰:此不可不辩也,儒家正学,百家异端,人当厚所当厚,薄所当薄,尊其所当尊。如乡愿,与君子交好,亦与小人友好,乡愿不去挤对君子,可对君子比较凉薄,而对小人则颇热情。然则乡愿贤乎?君子必远乡愿,斥小人,而敬君子,岂君子偏哉?义之不得不严也!以吾把儒家之外所有人当阶级敌人批斗,则是污蔑。可能君对我多有误解,因此脑海里就把我当做一个独夫,君已对我心存偏见,以恶意揣测,尚何言乎?君学虽驳杂,不辨正邪,吾犹不欲以恶意揣君,以为非君心之不良,盖见理之不足,于义之辨不明也。至于吾之言,亦不欲强加人。各言所见,各从所尚耳。崇佛老者,吾未尝令其弃佛老而从儒也,心有所尚,非令能夺。君之好兵道,吾何尝令君专学儒家耶?亦只劝君读些圣贤书而已,君不听亦可,何尝强君?惟愿君思之而已。
曰:你把商韩和蛮夷并论,尚以为不如,这还不是阶级斗争吗?都变夏为夷了。这还是我恶意揣测么?
余曰:商韩之法术,君子所深斥,亦常人所讳言。比之为夷,非过也。杞为夏禹之后,春秋尚夷狄之。
曰:好了,你又要对法家搞阶级斗争了。
余曰:然则孔子之狄杞亦为阶级斗争耶?吾亦只针对商韩之类的法家。管晏则较认可。孟子之距杨墨,亦为阶级斗争耶?船山虽大讲华夷之辨,然亦曰中华亦有败类,夷狄亦有贤者。凡中国的必是,凡外国的必斥,则不辨正邪而为模棱,一味排斥而为自封。论学术,岂可如此?吾只论理之是非,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何分内外。
网友对我的质难,和网友的辩论引发我更多的思考和欲辩明之话。有些理不辩不明。吾尝言儒家有三辨,华夷之辨,义利之辨,人禽之辨,皆作论明之。今则再加两辨:君子小人之辨,正学异端之辨。自孔子以道德分判君子小人,而异端之词亦出于孔子,宋兴理学以来多言之。以后有时间亦作文专论之。
论华夷,就被人说为狭隘民族主义;论正学异端,就被人说为狭隘儒家。彼等以吾为狭隘,而倡多元,百家平等,乃以商鞅为伟人,韩非为圣人,吾则以彼等驳杂,是非正邪不辨。
华夷之辨乃为保持民族之尊严,不为他族侵侮;正学异端之学乃为保持学术之纯正,不为异端污染。此为严谨,非狭隘,严于民族立场,谨于文化风俗。严于大是大非,谨于似是而非。圣人谨严于华夷之辨,而圣母必欲泯之;君子谨严于正学异端之辨,而乡愿必欲混之,安了可不辩乎?必欲以为狭隘,则孔孟程朱船山诸圣贤,皆狭隘乎?大是大非,正邪之必分也;似是而非,朱紫之必辨也。正邪不分,则乾坤倒矣;朱紫不辨,则颜色乱矣。
华夷且不论,且说正学异端。吾以符合中道者为正学,不符合中道者为异端。此乃判教,学问到一定,则须判教,以判别精粗美恶,正邪醇驳。正学之为正学惟其大中至正,异端之为异端惟其偏詖驳杂。异端亦有高明之处,错于偏;小道卑下,滞于陋。皆有可取。邪说则完全悖离正道,君子必摈斥之,无可取矣。正学,如孔孟程朱张王等,异端如老庄列佛禅杨墨马列等,小道邪说且不指。
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不否定异端,而不赞同专治异端,专治异端,则远离正道,而入淫邪,异端流行太过,凌驾于正学,则为社会风俗之害,如老庄之于魏晋,佛之于齐梁,马列之于go。孔子曰:“虽小道,亦有可取,致远恐泥。”孔子亦不否定小道,只是太过钻研小道,滞于形迹,安于卑陋,而不知性道,以入高明。小道强调太过,则圣贤之道不明,而为鄙陋。牟宗三曰:由清代知识分子而有民国知识分子的鄙陋。熊十力正是反其鄙陋而立其高明。
谈正学,异端,有人说我独尊儒家,搞一元独大。独尊要看独尊什么,独尊圣人大道,为何不可独尊,亦非我去独尊,实为圣人之道,特尊于异端之道,理上见得如此,非以私意抬之也。而圣人之德特尊于人;天子之位,特尊于臣民。同一理也。国有元首,学亦有正统,以不乱也。且独尊一词出于佛书,佛书言释迦刚出生,就走几步,指天划地而言:“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儒典未见独尊一词。
我也非搞一元独大,乃以一元统多元,有人倡多元,而多元乱,今人价值观之所以多混乱也;有人要一元,而一元独,秦之焚坑,纳粹之独裁也。以一元统多元,分判正学,异端,大道,小道,以正学统异端,以大道统小道,而不乱,亦不孤。通俗地讲,让各家学问,各种学问站在应有的位置。而非正学异端,大道小道并立,而为驳杂,而将异端小道凌驾于正学大道之上,则为颠倒,君子必辨也!社会也重视分工,家庭重视尊卑长幼,学问岂可无分乎?
彼等曰包容,吾以前亦曾言包容,今强调分辨,诚以今人多主多元,价值观混乱也。夫包容,仁人之心也,今辩学问之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似者辨之,正者崇之,邪者摈之,岂可齐是非,乱朱紫,混正邪,而皆包容耶?彼等所倡多元,所谓包容,其实是肤浅苟且,肤浅,则不辨精粗;苟且,则不分正邪。肤浅由于卑陋,见识不足;苟且由于懒惰,立场不定。人不可无立场,使自己思想有主,而不混乱。有人以立场为狭隘,立场也要看站在什么立场,圣人也有立场,圣人站在人道正学立场,绝不站在异端立场。没有立场,则无恒之小人,可与为善,亦可与恶,脚踏两只船,乃为广大耶?非道德苟且,则思想价值观混乱耳。有人好言融合,合一,而实多拉杂附会,不辨精粗美恶而混合之,无视差异而强合之。此岂博大哉,驳杂耳!君子贵博不贵杂,所谓博者,综合众长,采纳众善,取精去芜。如朱子、王船山之学皆富综合,非同异端俗学之拉杂,吾所推崇也。统同而贞异,非混同而泯异也。辨异以统同,非立异以不同也。合者,仁也,分者,义也,只合不分,是混同,只分不合,是割裂。
——二零一八年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陶扬鸿:原辩(14612字)发布于2021-07-06 01:0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