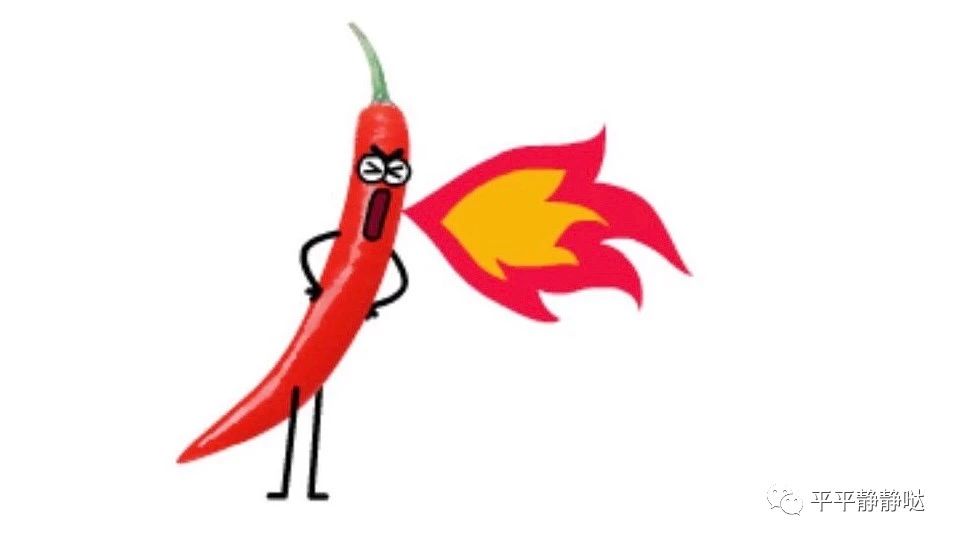余曰:近世文革,苏联大清洗,汝乃不闻乎?且儒术已用数千年,而马列方用数十年即生大弊,而谓马列胜于儒术,福泽苍生乎!君何盲眼瞎说也!沙皇已退位,而列宁犹将沙皇一家尽数枪杀,何其残忍也!不但其学有疵,身亦有过。 故马列其宜降为方术,而不可复为官学;儒家当复其正统,而不可继居下流。
彼曰:儒之不适中国,清即例证,苏之清洗,不过是民族性格所致,亦无伤于马列,而君以儒家为正统,视毛邓为何人,视三千万共产党烈士为何物?
余斥之曰:呜呼!儒家自古而为正统,以清之败政而毁儒,将以食栗死人而不吃食栗乎?然汝将无视文革之惨耶?其与苏联大清洗何异?毛,枭雄也,邓,政客也,非圣贤也,何能与周公孔子比?三千万共士,又何能与华夏数千年英雄壮士比? 且儒之用也有数千年,清乃数千年之后,清表虽尊儒,其实毁儒,欲儒为满清背黑锅,其论不公,其心亦不可问!
答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儒家亦然,天地无古今,稼穑亦古矣,将谓今不稼穑耶?中华文明以何为主?儒家也,承先王之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程朱依次相传。 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常道不分古今,古今一也,世虽变,时虽移,而儒家常道仁义礼智不可无也。儒家常道,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岂谓世变时移而可易哉!易者其法也,不变者其道也。儒家,中华之正统也;马列,夷狄之异学也。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以夷变夏者也。”舍中华之正统,用夷狄之异学,其欲以夷变夏乎?而恶可以夷变夏哉!而戕及中国文化,毁灭道统,罪百于桀纣,恶十于桓魋。吾等师古之精意,非师古之迹也,守先圣之道,非守古之法也。新出于旧,不可舍旧而开新;今源于古,不可裂古而循今。割裂传统,轻蔑古圣,此文革之祸所由生也!犹不知鉴,数典忘祖,趋变昧常,以异学凌正统,用夷狄变华夏,使中国文化果亡,虽有中国人,而奚足为中国哉!文化之亡,足以使民族万劫不复也!若灭种亡国,非可以咎吾儒也。西人有言:“欲灭其民族,先亡其文化。”希腊、罗马皆自弃其文化而亡也!西班牙毁印地安文而使其不复也!种灭国亡,由文化之亡,而与文化何咎哉!执古者昧今,循今者趋俗,儒家日新不已,岂可以古今限之!君劝我虑此,吾劝君亟宜返本,勿为夷狄异学所惑,自本自根,而可承前启后,大放异彩,多读儒典,究国史,无为俗论所囿,而何诋正学,颂异端乎?
——二零一七年
无产阶级革命谓余曰: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读儒家语录,信奉儒家思想,每天一心一意想要做君子做圣贤,那时的我遵循所谓的圣人教诲,从来不说谎,对父母毕恭毕敬,而我的学习也总能拿第一第二,但是却没有人陪我游戏玩耍,自己整天除了一个人看书就是一个人发呆。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当时是多么无知可笑,以为学了一些儒家语录后,自己就是君子圣贤而别人就是只能在我之下的愚昧之人。直到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才发现我已经严重脱离实际了,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愚昧的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要去都会去追求儒家的所谓的君子圣贤的境界。儒家所谓的君子小人实际是按自己标准划分。从某些角度上看,儒家讲的是治民而非民治,可今天的社会,更多的是民治,而不是统治者治民。受过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总有一天会陷入矛盾之中的。毛泽东小的时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称自己是个马列主义者,但他一生引用的儒家经典语句要比马列经典语句多,然而最终他却要打倒孔夫子。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也承认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我现在是讨厌儒家的。我相信有一天陶兄你也会陷入这种矛盾之中。
余答曰:君自小接触儒学,令吾甚是歆羡,叹我出身农民,非书香之家,到十八岁才接触儒学,虽然十五岁就读《孟子》,然彼时沉迷文学,只是把《孟子》当文章看,未做学问研究。这个时代,从小接触经典者,实为幸运,大多是成年后才接触经典,有的到四五十岁才能读经,与之聊天,叹接触之晚,然犹学之不懈,不以年老而废学也。自从就接触儒家经典,可不珍惜学习之时间乎?君自小而学儒,终而厌儒,笑往日之痴,是不善学儒,学儒不深也,学儒不深,而涉他学,则以儒学为浅薄无用。 儒学重立志,孔子十五志于学,宋儒以圣人为志,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宁学圣人之不及,不以一善成名,此宋儒志趣之高也,虽不及圣人,而为君子贤哲,宋儒学问之醇,德行之正,修身之严,为后儒所不及,余甚敬之,仰之,何敢訾议之?君自小即志于圣贤,可比二程,二程十五岁就脱欲学圣贤,君小学就欲学圣贤,比二程还早,可惜志不定,半途而废,其执德不固耶?以为圣贤终不可及,学之甚苦,则弃之而轻松安乐,学圣学而不安乐,盖拘迫太过,拘迫太过,则又厌之乃至弃之。孔子曰:“恭而无礼则劳。”学不可过也。吾学儒未有如此拘迫,故心安体泰,悠然自得。君信道不笃,心不定,则易为外物所牵,学之未成,又以所学为非,反诋毁之,岂儒家之非耶?所学之过也。不反思自己,而以归咎所学,岂不迂哉! 然则君之自小立志为圣贤,非真立志也,浮慕其名耳。真立志者,定于内,举世非之不为沮,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岂牵于外物哉!窃以君之立志,慕于其外,一时之头脑之火热,无本于内,孟子曰:“原泉滚滚,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君之学儒,出于一时之热情,如雨露之润地,经日则消,是谓无本。然则何以固本,朱子曰格物穷理,陆子曰发明本心,理既穷则志愈定,心既明则有所主,志定不为异学惑,有主不为外物牵。为学,程子之言最密,曰:“涵养在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二者不可偏废,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发。”人心有所放,独为涵养,很难操持,穷理致知,益之以学问,义理明则本心愈固,学问以辅德性,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道学岂可相离?君之半途而废,盖于义理未明,观君之言,可知于理浅薄,君之学儒,只学到皮毛,至于其里,非君所知也,若谓窥其堂奥,更非君所能至。
学者要志于圣贤,而不可以圣贤自居,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居圣则非圣。立志不让尧、孔,为学为人则不敢自是,此君子之谦德也,非如异端之伪,谦者常存自慊之心,不以为足,则修身为学不有一日之息,终日乾乾,精进不已,以至于贤,以至于圣。虽至于圣贤,犹不敢自足也,犹日日反省,惩忿窒欲,改过迁善,小心警慎。曾子临终曰:“《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至死方息,先贤之于为人,慎之如此,此曾子所以能继孔子之道。若有自足之心,以圣贤自居,不复学习进取,而轻藐他人,则圣贤经典,先儒语录,适足为长傲遂非之资。君能省此,是矣,而不知为己学儒不当所致,非经典长汝之傲,汝心自傲,而经典适为长傲之资也,《尚书》所谓自乱于威仪,非酒色乱汝威仪,任耳目之官,而从其小体,本在己心之不清,何可咎物哉?本在己心之不明,何可咎书哉? 所谓君子圣贤,儒者之志也,理想之标准也,为学者言,岂教天人人学为君子圣贤耶?孔孟,程朱教天下人皆学为君子圣贤耶?因財施教,随財成就,诱劝之,激励之,而不勉强之也。儒者言治,以德治为主,辅以法治,非可民治治民概之。德治则以人治人,改而止,不以己治人,彼自治之,以己治人,则有强人之所不能,而为刻薄,以人治人,随其分而无勉强,此治之至也。
毛小时虽受儒家影响,然吾观其早年文稿,于义理较为浅薄,学之不深,则为异学所惑,反诋此学为腐朽无用。其晚年之打倒孔家店,正为其大过,何引之为偶耶?君受儒家影响,亦表面,其间义理,君所不明,若明,何为厌儒,有厌儒之心,则是君心之浮躁,愿好好学习,去此浮躁。昔熊十力早年亦詈六经,中年归儒,君今所走之岐途,愿能走回正路。 吾于儒信之愈笃,卫之愈诚,十八岁接触儒学,以儒家为重要之文化,未尝究心于此也,二十始以儒家为主,为安身立命,后于儒家义理知之愈多,更欲以阐扬儒学自任。虽然,吾不敢自足,学之不已,至老不息,吾以此为生命,以此为归宿,自信无人可夺也。
——二零一八年
或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公平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也,也配称君子?富国强兵不及法家,经世致用不及墨家,儒家不过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余曰: 礼不下庶人,不以礼求庶人,刑不上大夫,以廉耻养大夫,齐之以刑,则士大夫苟免而无耻,先王以君子之道待士大夫,以人治人,何言公平不公平?民有可由不可知,道之可行不可言,说之则民不喻也,岂为愚民?后生妄生曲解,徒见其无知耳!儒家之用,治国平天下,致太下太平,民丰物阜,文盛俗美,成康刑措百年,岂止富强而已哉!法家唯务富强,不修道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图近利而不顾后患,大害随之,当为警诫,何可称哉!墨家绝迹于秦,墨者多死,己且不存,况能经世乎!
法家乃真为愚民,商鞅曰:“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又禁民迁徙。驱民于农战,而以民与国对立,曰:“民弱国强,国强则民弱。”民愚民弱,则易使也。为使国强,不惜刍狗百姓,酷烈奴使其民,唯法家为然。
又曰:本末倒置,齐国当时士大夫无耻,才处以极刑,以正朝纲,开齐国清明吏治。道之可行不可言?笑话,小政在朝不在民,大政在民不在朝,人民对邦国强盛的政策有很强的辨识能力,儒家不务实际,空谈大道,荀子儒法双修,人性之恶,必待师法以后从正!没有法家的令行禁止,光靠道德,能束缚犯罪?秦二世赵高屠杀能臣大吏,庙堂之上被换了一批庸碌之辈,这与功成进爵都商君法背道而驰,秦二世的秦朝商君之法面目全非,蒙恬蒙毅屈死,冯劫冯去疾枉死,这些正才全死光了,谁来维持秦法?你没读过秦史,不学无术,空谈大道!墨家绝迹?墨家技艺流传于世,天下多的是墨家人,机关设计,建筑之学不是墨家?你住的房子都是墨家设计的。
余曰:本末倒置者汝也!重刑不重礼,重法不重道。士大夫无耻,则当以礼乐教化,礼乐养其廉耻,岂以刑威之?如此则益苟免无耻,秦之刑法益重,而无耻之士益多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千古通论也,尚礼不尚刑。天下智者恒少,愚者恒少,士大夫且然,况民乎?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产之为政,民且欲杀之。儒家虚实并务,礼乐之虚以劝善,刑政之实以治恶,岂如法家偏于刑政,而以礼乐为无用哉!礼治之于未乱,法治之于已乱。先礼后刑,先以礼乐教化,后以刑法惩罚,未以礼乐教化,遽施刑法,孔子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也。秦之赵高得以专权乱政,指鹿为马,无人敢言,由秦之无君子也。其无君子,专任刑法而无教化也。秦法严,君骄恣,莫敢谏,李斯不以正谏,乃曰灭仁义,绝谏诤,丧心昧理至此!李斯、赵高皆法家也,唯法家出如此小人恶贼!
善哉苏子瞻《志林》曰:“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及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故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
墨家绝迹于秦,墨守陈规而学说无发展,沦为刺客而人才无继承也。唯技艺流传而已,器耳,君子不器,儒家之全,六艺兼通,天人相贯,岂偏于一器哉!建筑之学,一技也,岂墨家独有?世界建筑,人类所居房子,皆汝墨家所为乎?无墨家,无建筑?无墨家,无房子?建筑房子远在墨家之前,西方中亚无墨家,皆有建筑之学,皆有房子,而攘为独有,岂不鄙哉!岂不狂哉!
又曰:儒家夸夸其谈,奔走七国而无一国用之,可见其无用!孔子喊杀少正谋,可见其霸道独横!法家富国强兵,儒生骂之虎狼苛政!墨家非攻兼爱,孟子骂之无父绝后!医农工商,民生之学,孔孟贬为细支末技!纵横外交,儒家骂之妾妇之道!骂遍诸子百家,器量之小令人惊愕!你儒家为何物?你儒家不学无术,不务实际!自封君子!专营权术!以恭维君权至上为能事,不近百姓!不务民生!以君子之道掩盖其求官丑态,正如娼妇处子!婊子牌坊!
余曰:孔子治鲁,道不拾遗,齐人以鲁用孔子必霸而间之,夹谷之会,兵不血刃而使齐退回侵鲁之地,堕三都,平定公山不狃、叔孙辄之乱。孔子弟子子贡一说,存鲁破齐灭吴霸越,改变天下格局,虽苏张纵横不及也。冉求为鲁将,破齐军,曰兵法受之于孔子,与孙子并称之吴起亦受学于曾子。魏文侯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礼段干木,不战而退秦师,灭中山,为三晋最强。鲁仲连谈笑退秦军,孰谓儒者无用哉!
至于用与不用,命也,君子传道也。明末大儒王船山曰:“屈其道而与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与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竞。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善哉斯言!天下有道,则用天下之才;天下无道,则储天下之用。若商鞅之屈其道,以求用于天下,使秦称强,势既显矣,位极人臣,而六卿忌之,身遭车裂之刑,而毒及百世!岂非利在而害亦伏者乎?是不善用天下者也。东林党以其道与天下亢,排击阉宦,痛斥士之陋习,而起党争,死者甚众,弊未因革,国未加治,岂非身危而道亦不竞者乎?满清乘衅入寇华夏而莫之能御,惟临危一死报君王,是不知储天下之用也!呜呼,此其用于排击异己,而何不用之抗击满清!孔子知王政之不行,而修六经以授徒,传之万代,道统之赖此不坠,后之贤君得用其道,华夏之能延续至今,斯夫子之光也!船山知此,故隐于船山,著书立说,以待来兹之用,而辛亥革命因船山之说以覆满清,国共合军以驱日寇,是善储天下之用也。
君子知进知退,进则登庙堂以治国,退则为人师以教民,或修书传世,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也。进非为功名富贵,自居于万民之上,不体民间甘苦;退非为全身远害,隐居于山林之中,不问世间是非。君子不苟进也,不厌退也。若商鞅、苏秦苟进以取富贵,害亦随之,惨遭车裂;陈仲、焦先之厌退而避世人,终生无用而已,死同草木。 当君子不得其用,君子储存其用,以为后来者之用,以为他人用。有圣贤,觉其功业无闻,为无用之人,世俗笑其愚不可及,而不知其能量甚大,其所储存之用足为后人之资。非必登朝堂,建功立业方为用,教书育人或著书传世,为国家培植栋梁,撒播文化种子,何尝非用?孔子、朱子、王船山、熊十力是也。君子直道而行,不屈其道以迎合世主世俗。孟子所谓“大匠不为拙绳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不能因为世主不接受己之政治理想,遂改变初衷,以浅薄之实用迎合世主,虽得富贵,而吾道亦损,人格亦卑,若商鞅以帝道说秦孝公,孝公不听,遂以王道说孝公,孝公不听,乃以霸道说之,遂得其用,位极人臣,商鞅虽取功名富贵,使秦称强,而招多人之怨,不免车裂,秦国亦因此急功近利,国家虽强,然民俗日败,强之数世耳,而其灭亡,宗室子弟为赵高、项羽杀戮殆尽,亦何惨乎?不本于仁义而逐于功利,其功之所以成也,亦其所以败,利生于其外 ,而害伏于其内,当其成,天下莫与争锋;当其败也,求为匹夫而不得;其利也,雄于诸侯数世,其害也,不保其子孙。若近世胡适则为屈其道媚世俗,废文言,行白话,标普及之名,而实损中国文化,坏中国道脉,彼因此声名骤盛,为大众追捧,然有识之士皆鄙其浅薄,愈至后来,胡适之学说文章注意者鲜矣,更多人识其浅薄。贪一时之名,而终贻万世之谤;缴一时之利,而终毁千秋之业,可不以为诫哉?
至于孔子诛少正之诬,吾早已辨之:孔子诛少正卯之诬久矣,始于《荀子》,司马迁仍其谬,《家语》亦书之,吾尝作文辨之曰:太公诛华仕,孔子诛少正卯之事,法家之徒杜撰之,太史公载之,世人多信之,后儒以此辟异端,法家以此除异己,反儒派以此诟孔子为专制,甚矣其谬传之久也!今可破其诬矣。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察实据而诛少正,岂合孔子之本心?又《论语》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圣人不贵杀也如此,岂有秉政七日而杀少正?春秋,大夫于贵卿尚不可擅杀,况孔子与之同为大夫哉!孔子不至如是之狂也。按孔子诛少正,先秦惟《荀子》、《孔子家语》载之,其他书不见,《荀子》宥坐篇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姜太公诛华士在《韩非子》有记述,曰:“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居士二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饮,无求于人也。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周公旦居鲁闻之,遗书急发之:“夫二子,贤者。何以杀贤?”太公望曰:‘二子不仰君而食,无求于人。爵禄无以劝,刑罚无以威。无益于君也,是以诛之。’”其他书无此记载,太公佐武王伐纣,伯夷叔齐阻之,左右欲杀夷齐,太公劝止曰:“义士也。”夫太公起兵伐纣尚不诛阻拦之夷齐,而当齐侯反欲戮无辜之华仕?此必韩非寓言也。诸子著书,莫不托古圣贤以立说,孔子常征引之,盖孔子之名大,而借其名以宣扬其学也,安足为信?法家杜撰太公诛华仕以诬太公,又杜撰孔子诛少正以诬孔子。 今按《左传》及其他史传皆无孔子诛少正卯之记载,孔子为政,堕三都,平公孙叔辄而已,未有杀人也。孔子曰善人为邦,胜残去杀,况孔子为圣人哉!而以杀为治乎?圣人,神武而不杀也,秉政七日,即诛大夫,酷矣,岂圣人之行哉?《荀子》曰子产诛邓析,而观《左传》则为郑驷诛邓析而用其刑,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皆不见史书记载,子书托之以为名耳,孔子名大,亦托于孔子。周公诛管叔,管叔结武庚为乱也,是数子,未犯法,岂为乱哉?可同论乎!先王君子不以言语罪人也,尧舜立诽谤之鼓而治,周厉王弭谤而放,秦禁偶语而亡,孔子圣人,岂违先王之道,而与暴君苛政同其谬哉!以少正言伪而辩,则杀之,不亦甚乎?以辟异端,吾闻以言论辟之也,未闻以杀戮辟之也,孟子距杨墨,程朱辟佛老,辞而辨之,非杀其人也,不能折其说而杀之,人不服也,天下所非也,实为暴也,适彰己恶耳,圣人岂若是之狂悖乎?吾固知法家托孔子以为名也,诚法家之诬孔子也,何儒者亦有信之者乎!先王君子之诛人也,待其有罪,人皆以为可杀,察其可杀而杀之,少正之罪,未显也,曰心达而险,而不见于事也;曰行辟而坚,而未害于人也;曰言伪而辩,而未犯于法也;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亦不见于律也。君子诛当其罪而人心服,此五者,岂使心服哉?罪名不显,人心不服,诛之适受恶名耳。诛不当罪,授人以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之杀孔融,曰不孝;司马昭之杀嵇康,亦曰不孝,罗织不孝之辞,然岂足以服天下哉?人胥以为冤,而曹马为天下谬也。观乎《荀子》所载孔子诛少正之由,未免牵强而捕风矣,是不足以服少正,尤非鲁人所许也。孔子之尚仁,固无如此之暴;孔子之圣,固无如是之狂;孔子之智,固无如是之愚。异端之诬孔子也,儒者何为信之?当辨之。
法家告奸株连腰斩车裂之法,诚为暴政。墨家兼爱,伦理淡薄,故曰无父无君,未咒其无后也。医农工商,儒家未尝轻也,孔子弟子子贡从事于商矣,孔子有非之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言张仪、公孙衍也,仪诚险诈之人,心术不正,故孟子不齿。孟子距异端邪说,扬圣人之道,功不在禹下,汝小人何知?妄肆诋毁?至于汝所骂不学无术等,实同犬吠,泼妇骂街,何足辩哉!
——二零一九年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陶扬鸿答反儒派(8390字)发布于2021-07-06 01: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