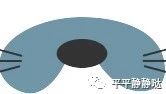韩愈原道谏迎佛骨等辟佛文流传天下,士人莫不读之,影响大矣,后世儒生师之,佛门中亦有改辙者。佛徒衔之惧之,恶之者,编退之死后下饿鬼道以诅之,曰谤佛者得恶报也,其巧者则造谣诬退之晚与僧大颠交,易节信其教矣,而以谓世人曰:“辟佛之坚如韩愈者,亦信佛矣,是圣教之移人如此之深也,不如愈者,而犹欲蹈其前辙哉!”佛徒之为诞妄矫诬者如此,而无知者信焉,儒者当为辨诬,于韩公晚年书信《与孟尚书书》及柳宗元一书信而知佛徒之诬,无须多辨矣。特录韩柳书于此:
韩愈:
与孟尚书书
愈白:行官自南回,过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书数番,忻悚兼至,未审入秋来眠食何似,伏惟万福!
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某之祷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圣贤事业,具在方策,可效可师。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诗》不云乎“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传》又曰:“不为威惕,不为利疚。”假如释氏能与人为祸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惧也,况万万无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类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祸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灵。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诬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间哉?进退无所据,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且愈不助释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说。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故曰:“能言距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倡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
籍、湜辈虽屡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获承命,惟增惭惧,死罪死罪!愈再拜
案:于韩愈此书可见,佛徒之编造其信佛,于韩愈生前已流行矣,愈已自辨,而佛徒犹欲诬之,至今不易。而韩愈此书辟佛犹严,比原道谏佛骨表更明言佛之害,可谓笃于正道,为防深矣。推尊孟子,谓佛老之害大于杨墨,辟异卫正,虽万死不恨,何其自任之重也!言之如此彰明,如此严重,尚可诬乎?
柳宗元: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韩退之与予善,尝病予嗜浮屠言,訾予与浮屠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予,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屠。”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馀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屠游以此。
今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为其道,以养而居,泊焉而无求,则其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其亦远矣。李生础与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此人寓退之,视何如也。
案:柳宗元为韩愈之友,同尚古文,而韩愈辟佛,宗元佞佛,愈颇不满,常批评规劝之,又与书责之,而柳氏则以佛之说有与圣经合者,非庄列申韩之险怪比也,是不知佛说愈精,其害更过庄列申韩。愈近理而害道愈甚,人不易辨,如“紫夺朱,郑声乱雅也”。不知圣人之道,而以异端有合也,惑于佛氏深矣。韩愈之“以其夷也”,非谓夷狄之无善类也,华夷之防,华夏为本,不以夷狄之法乱华,甚至喧宾夺主,变夏为夷也。季札吴之公子,泰伯之裔,与周同宗,岂如释氏出自天竺之为远裔,吴之贬为夷者,政俗近于夷也,季札乃能特立,使鲁观周乐,赞叹之甚深不已,能出幽谷而迁于乔木矣,其为华夏圣裔,慕于华夏礼乐,而与释氏等论,是不知类矣。
谓韩愈罪佛之迹,而不知其内,剃发而髡,无夫妇父子之伦,其外如此,则其为内者,亦岂不颠倒错乱哉!迹非而心是,是分心迹为二,心迹一也,诚于中而形于外,外之不是,则其于中者岂无谬哉!言其清高不爱富贵,乐山水而嗜闲安,过于世俗之逐利相轧,此远于污俗而逐于高明也。然高明之害也过于污俗,污俗之害,人多知之,高明之害,人不知之,反推而尊之。陈仲子之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而孟子非之,离兄而绝母妻,无人伦也,释氏更悍然毁性绝伦,以其小者,而信其大者,恶可哉?愈之不排庄列申韩,而辟佛者,当时盛行者佛,其为惑尤深也,所关者天常。
韩公之自辨而更辟佛之害者如此,其友柳氏之述其不满其佞佛者如此,守正斥邪甚诚,终身不改,佛徒之诬其晚年信佛者,可以休矣!可以休矣!
韩愈之于僧,盖如孟子之对墨者。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苈,又从而招之。”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而以“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见孟子于异端之严,然距其说也,非距其人也,人之智不及,易为异端所惑,距其说,异端之惑人者减,未能距其说,而徒距其人,惑者相继,岂胜距哉!“归斯受之者”,孟子于异端之宽也,人之有觉也,一旦悟杨墨之非,而信儒家之为正,归儒,则受之而已,受而教之,相与共扶正道,此仁也,智也,既归正道,既往不咎,何复咎前之迷于异端而犹距之束之哉!而能教异端之徒以归正道,岂不尤贤乎!非如耶穆之教,恶异教而摈斥其徒,杀戮其徒也。吾儒之辟异端,辟其说而已,学说为天下之本也,本治而末移。则韩愈之辟佛,而复与僧徒交者,岂言行之不一,或始辟而终信哉?韩愈所恶者,佛说也,非僧徒也,辟佛而交僧,孟子追放豚之意,欲导异端之徒归正道也,诗人孟郊之弃佛而归儒,是其效矣。惜乎柳宗元耽迷之深,不能导之于正也,然不以其崇异端而易其朋友之好,其量亦宏矣,知人学有分也。
又案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曰: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 ,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 ,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以与之游乎?扬子云称 :“在门墙则挥之 ,在夷狄则进之 。”吾取以为法焉。(韩公交僧人之意,盖欲取其行是,有儒行者而交之。)
浮屠师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午凡有行,必请于搢绅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贞元十九年春,将行东南,柳君宗元为之请。解其装,得所得叙诗累百余篇章非至笃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无以圣人之道告之者,而徒举浮屠之说赠焉。夫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彼见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乐闻其说而请之。如吾徒者,宜当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语之,不当又为浮屠之说而渎告之也。(其欲以正道告佛徒,以导之入儒门之意明矣。送浮屠之文,无非扬儒抑佛,谓浮屠者有慕于吾道,则当以吾道之精粹告之,岂可复以其所学佛说语之?与僧徒所传公慕佛法,并杜撰公与大颠书,称慕请问者,何相反也!于此益知佛徒之诬矣,儒者胡为不辨而信之?)
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然。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亲亲而尊尊,生者养而死者藏 。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午万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体安而气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书之于策,中国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为而孰传之邪?夫鸟俯而啄,仰而四顾;夫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脱焉。弱之肉,疆之食。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此语亦斥佛之无本而何传,隐刺其为禽兽之道,斥佛徒沐圣人之恩,而忘圣人之道,当知所从来。)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为者,惑也;悦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实者相不信也。余既重柳请,又嘉浮屠能喜文辞,于是乎言。(其欲引之入儒门之意又见矣!谓当弃乎故而即乎新,故者为佛,新者即儒也。而吾辈为儒者,当以实言告之。)
此文实表孟子追放豚之意,韩公辟佛大节,始终一贯,非徒辟佛,又欲明先王之道以告之,拉之入门,变释者为儒,岂可诬哉!岂可诬哉!呜呼!使儒者皆能如韩公教化异端以归正道,则吾道自然昌明,异端自然消息,又何必如前之所为“火其书,庐其庐,人其人”哉!于此见韩公辟佛之法较之前高明,绝非易节折于异端也,正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兵不血刃而降其众,岂不犹愈于杀乎?韩公言学,于异端如此之严,待异端之徒,则如此之宽也。
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韩昌黎集》卷三曰:此篇一起,为第一段。先将自己与浮屠作序之故轻轻脱出,见得与平日辟佛教自是并行不悖,立身最占地位。中幅,辟去众人序诗百余篇,为第二段。扫倒众人,方好自出议论。后幅,告之以圣人之道,颂以圣人之功,为第三段。得此表章,方见得自说异于众人处。末作一结,五句各自一意,一意各自一结,穷神之笔。
爱新觉罗·玄烨《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五曰:昌黎力排释氏,而为浮屠赠言,如此正《原道》中所谓“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也”。
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四曰:文畅浮屠也。其周游天下,本欲倡明其教,如今日所谓大和尚使天下人崇信皈依耳。即请诸搢绅先生咏歌,亦不过取重于宰官文人,为之护法标榜,使天下人坚其崇信皈依之念耳。柳州喜与僧游,宜为之请。然昌黎一生大本领,全在辟佛,岂能作此等委曲文字。故开口分出儒墨是非,而以名行之异,虚虚发出不轻绝人之意。转入文畅身上,硬坐他喜文章、慕圣道,吾儒不当以浮屠之说赠送,当以圣人之道开示。铺张胪列,说出圣人无数好处,皆文畅所不乐闻。但说到禽兽之弱肉强食,而人得以养生送死,伊谁之功,实皆世俗未曾想到之语。篇中自“民之初生”至“中国之人世守”句,乃《原道》篇节文,至所谓“弱肉疆食”等语,即《原道》篇中所谓“古无圣人,人类灭久”之意。余以闽蕃之变,下狱籍产,常叹王灵不及,受种种苦,则践土食毛,无日可忘君恩,浮屠独未之思耳。是篇较《原道》篇尤为警策,皆从孟子好辩章,“无父无君率兽食人”等语脱化出来,真有功世道之文也。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卷六曰:此篇文字,能当面骂人而人不知,由善用提笔也。“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似泛举,一言不涉文畅。举出圣人与佛氏针对,见得学圣人者非禽兽夷狄,则对面之人,与圣人反者不消说矣。抬高尧、舜诸圣人,说得酞挚,淡淡一证以浮屠之所传,使觉异样冷隽。文笔之变化陆离,到极处矣《古文辞类纂选本》卷六:此篇文字,能当面骂人而人不知,由善用提笔也。“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似泛举,一言不涉文畅。举出圣人与佛氏针对,见得学圣人者非禽兽夷狄,则对面之人,与圣人反者不消说矣。抬高尧、舜诸圣人,说得酞挚,淡淡一证以浮屠之所传,使觉异样冷隽。文笔之变化陆离,到极处矣。
附诸儒评论韩愈:
薛文清《读书录》曰:切不可随众议论前人长短,要当已有真见,方可。唐之韩子,乃孟子以后绝无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虽博爱三品之语有未莹者,然大体明白纯正,程子所深许,朱子又为考正其书,诚非浅末者可得而窥也。后学因见朱子兼论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责备贤者之意,遂妄论前贤若不屑为者,其可谓不知量也甚矣。当韩子之时,异端显行,百家并倡,孰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为相传之正统?又孰知孟轲氏没而不得其传?又孰知仁义道徳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释氏濵于死而不顾?若此之类大纲大节,皆韩子得之遗经,发之身心,见诸事业,而伊洛真儒之所称许而推重者也。后学因见先儒有责备之言,遂勦拾其说,妄议韩子若不足学者。设使此辈生韩子之时,无先觉以启其迷,无定论以一其志,吾见沦于流俗,惑于异端之不暇,又安敢窥韩子之门墙哉!故论韩子之得失,在周程张朱数君子则可,苟未及数君子,皆当自责自求,殆未可轻加诋议以取僭妄之罪也。
薛文清《读书录》曰:性理之学经周程张朱诸君子发挥如此明白,当时亲炙者尚失其意,而韩子生于道术坏烂之余,无所从游质正,乃能卓然有见,排斥异端,扶翼正道,遂有立于天下后世,真可谓豪杰之才矣!
陈几亭曰:我辈生程朱之后,晓佛之失不难,况圣世功令,以儒辖释,天子从无隆重邪教者,则距邪益不难。唐承五代之后,人主涕泣瞻拜,举世几无复人心,前此又从无阐破禅病者。退之绝无依傍,粗粗守正,便是千载人豪。试想他是何等心肠!何等识见!何等胆量!所以程子极力推许,断不得目之以文章之士。
陈几亭曰:退之骨气严正,子瞻襟怀洒落;退之重大颠以理,子瞻狎佛印以滑稽。退之生平辟佛,皆以福田,未深究佛理也。当时天子崇尚异端,海内风靡,而退之独立不波。晚遇大颠,想其人实实参悟,不以福田为心,较寻常学士大夫,傍儒理而无所得者,反有胜焉。好学者人人可资,人人取益,不得于同类,亦何间于缁流? 遂与往来商订,无足怪也。子瞻性喜恢谐,而《外纪》所载,佛印谑言尤秽亵无人理, 殆释氏之狡童,儒宗之蟊贼乎?岂得与退之珍重大颠同日而道?
陈几亭曰:韩文公继亚圣,启程朱,厥功诚伟。
张元谕曰:阳明云韩子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此过当之论也。程子称原道之作,其识大。朱子称退之不易及。西山真氏谓《原道》诸篇语道德必本于仁义,而其分,不离父子君臣,其德不过礼乐刑政,饮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权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复明者,韩子之功,实万世之公言也。至力排老佛,尤非诸子所及。史称孟子距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千余载。拨乱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非过誉者矣,岂文士而已哉!文中子言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醮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是犹以老佛为可宗也,而谓退之去文中子远甚,不亦过乎!
王阳明《韩昌黎与太颠坐叙》曰:退之与孟尚书书云:“潮州有一老僧,号太颠,颇聪明,识道理。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因与来往,及祭神于海上,遂造其庐。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颠,其大意不过如此。而后世佛氏之徒张大其事,往往见之图书,真若弟子之事严师者,则其诬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与人不可以不慎也。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陶扬鸿为韩愈晚年信佛辨诬,以韩愈与柳宗元书信为证(六千五百多字)发布于2021-07-06 1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