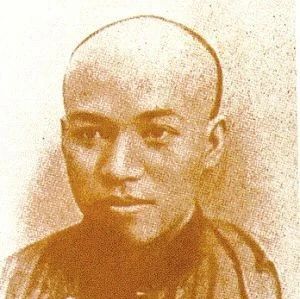梁启超,博学而无识者也,观其《历史研究法》书曰:“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一一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传世最古之史书也。宋儒谓其‘寓褒贬,别善恶’,汉儒谓其‘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两说孰当,且勿深论,要之孔子作《春秋》别有目的,而所记史事,不过借作手段,此无可疑也。坐是之故,《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之徒,犹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弒。(《礼记·明堂位》文。)又如狄灭卫,此何等大事,因掩齐桓公之耻,则削而不书。(看闵二年《穀梁传》‘狄灭卫’条下。)晋侯传见周天子,此何等大变,因不愿暴晋文公之恶,则书而变其文。(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条下《左传》及《公羊传》。)诸如此类,徒以有‘为亲贤讳’之一主观的目的,遂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又如《春秋》记杞伯姬事前后凡十余条,以全部不满万七千字之书,安能为一妇人分去尔许篇幅,则亦曰借以奖励贞节而已。其他记载之不实不尽不均,类此者尚难悉数。故汉代今文经师,谓《春秋》乃经而非史,吾侪不得不宗信之;盖《春秋》而果为史者,则岂惟如王安石所讥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顾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而其义亦随之而晦也。自尔以后,陈陈相因,其宗法孔子愈笃者,其毒亦愈甚,致令吾侪常有‘信书不如无书’之叹。如欧阳修之《新五代史》,朱熹之《通鉴纲目》,其代表也。”
浅甚妄甚!可不驳之!自梁启超倡新史学,而中国历史乃惟求客观真实,不能以历史经世教化,惟成客观之物,而不能内化于吾心,不能置吾身于历史中,以为实践,则历史成不相干之物,乃历史之堕落,则梁启超不能不深负其咎也!而敢妄议孔子乎!孟子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何也?孔子固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于乱臣贼子之恶,则秉笔直书!何以见之?《左传》载赵穿弑其君灵公,而孔子《春秋》则书赵盾弑其君。则以赵穿弑君,为赵盾所指使也,赵盾为主谋,赵穿帮凶耳,犹成济之助司马昭杀曹髦也。而流俗以赵盾为权贵,弗敢道其恶,归罪于穿,以为掩饰,孔子则直书之!不惧得罪晋国权贵也。呜呼!使无《春秋》,孰知赵盾之恶哉!而传乃益之曰为法受恶,犹为之隐也,是孔子罪人也,而何责孔子之讳?太史公著《史记》正继孔子直书之道!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知孔子者也。
且启超之浅薄无知也,岂知《春秋》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之义哉!儒家之道,亲亲尊尊尚贤。爱其亲而不忍言其恶,孔子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所以为亲者讳也;尊其君而不忍公其丑,鲁昭公娶孟氏而孔子不曰不知礼,所以为尊者讳也;尚其贤而不忍著其过,齐桓公灭项而不书,所以为贤者讳也。史者,非徒记叙也,实有微言大义在焉,若徒记叙,则亦账薄耳,而史亦何足贵哉!启超之视史也小,而徒以为记叙客观之事实耳,其所见者小也。不为亲者讳,则亲亲之恩薄矣,而父子或相怨;不为尊者讳,则尊尊之礼降矣,而君臣或相疑;不为贤者讳,则好贤之诚衰矣,而贤人不足式。
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且不详论,且论为贤者讳。贤人者,所以为世法式也,其行高,其德劭,其功大,然非圣人不能尽善尽美,贤人亦有过失,若著其过失,则或以小疵而掩其大美大功,而人以贤人不足法矣,其不肖者则以为口实矣,岂非圣人之遗憾哉!齐桓公有尊王攘夷,一匡天下之功,而有灭项之过,迟救卫之失,春秋明其功而略其过,以王道衰,惟桓公能匡天下,今若著其过失,则恐掩其大功,而孰有能如桓公之尊王攘夷乎?春秋之为贤者讳者,此也。明其功,略其过,表其行,隐其心,所以劝善,苛责其不尽,显明其幽隐,则孰复乐为善哉?晋文公之召周襄王,讳曰“天子狩于河阳”,亦以晋文公有攘夷,救天子之功,夷夏大义也,攘夷救君,大功也;以臣召君,其迹甚逆,比于夷夏大义,救君大功则为小,春秋明其攘夷救君之功,而略其召君之逆,审轻重,亦为贤者讳也。春秋,经也,文字甚简,若夫事之详细,义之彰明,则三传见之,孔子传之弟子也。何诬颠倒其实?
讳者,非掩之也,略之不显耳。《汉书》之于董仲舒,列传详叙其天人之策,和亲之议载于匈奴传。《后汉书》于光武帝,帝纪详叙其定天下之功,信谶之失载于诸臣传,本传本纪明其功,不著其过,过则微叙于他传,善继《春秋》,为贤者讳也。董子大儒,而有和亲之失;光武中兴之主,而有信谶,迫死大臣之过,若著于其传,则人或以董子为腐儒,光武为昏君矣,而其表彰六艺,中兴汉室之功,何以明哉!此岂作史之意乎!春秋之为贤者讳,劝善之苦心,与人之恕道也,后世浅薄学者不知,乃为轻诋,可谓无知无畏,侮圣自是也。
春秋为贤者讳,又责备贤者,如子文之为楚贤臣,而责其弗能正楚之僭。为贤者讳,所以尊贤劝善也;责备贤者,所以勉其尽善也。不以小过而疑贤者之善,而功不安于小成,善不止于小善,勉而复进,孔子称管仲之仁,又责其器小,与其功,而贵于王道也。与之,法也,责之,道也。隐讳之,仁也;直书之,义也。彼梁启超之浅学,恶能知之!而诬宗法孔子愈笃者,其毒愈甚,并诋欧阳、朱子,可谓坐井窥天,不知天之大也;以陋心疑傍圣贤,不知圣贤之深也。可笑不自量耳。
又因文见道,以文载道,文之大者,启超何疑耶?文者,道之枝叶,道者,文之根本。君子有道,则有文,本大则末宏,根深则叶茂也。有道则诚,何为不诚无物,道文两败俱伤?为文而文,文之奴也,而何以为贵?近世自所谓文学改良革命,美曰文学独立自觉,而文不以载道为命,多以文为游戏而相娱,以文为技术而弄巧,且者炫文以博名,鬻文以牟利,合流俗之所好,应时局之所制,久习于伪,而何有于诚?启超贵之,君子不贵也!为文而文,文之奴也;为物而文,文之贼也。然则何以为文?有所为而为者,皆意也,有意则伪则私,无所为而为者,道也,乃诚乃公。君子心以为文,自然而发;道而为文,本天而作。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驳梁启超,论为贤者讳发布于2021-07-06 10:4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