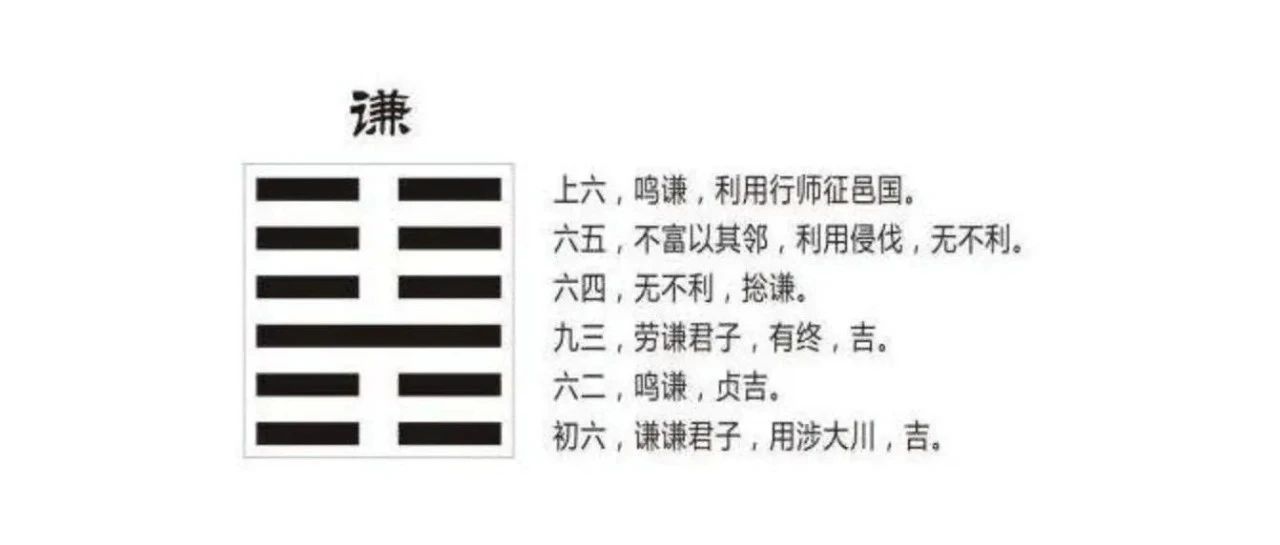吾作《代孔子驳盗跖》文,有网友曰:罪满天下,誉满天下,不亦大人乎?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有复何辩乎?春秋无义战,盗跖之言,庄子伤末世耳,刺借儒术求显达耳,孔子诚非此辈,而后世借儒术谋稻梁者皆以孔丘为精神木偶,不亦讽乎?
余曰:此岂庄子作乎?其文辞也粗鄙,其思想也浅薄,党邪丑正,悍然诋毁历代圣王,射天笞地,肆无忌惮,而其丑化孔子,辱孔也甚矣!乃汉初妄人之伪作也。列于《庄子》千年而无人驳,近代多以此反儒反孔,吾久欲驳之,今幸作成此文也!
明末大儒王船山《庄子解》亦曰:《让王》以下四篇,自苏子瞻以来,人辨其为赝作。观其文词,粗鄙狼戾,真所谓“息以喉而出言若哇”者。《让王》称卞随、务光恶汤而自杀,徇名轻生,乃庄子所大哀者,盖於陵仲子之流,忿戾之鄙夫所作,后人以庄子有却聘之事而附入之。《说剑》则战国游士逞舌辩以撩虎求荣之唾余,《渔父》、《盗跖》则妒妇詈市,[]犬狂吠之恶声,列之篇中,如蜣螂之与苏合,不辨而自明,故俱不释(不足释也)。乃小夫下士,偏喜其鄙猥而嗜之,(海上有逐臭之夫,世有好低俗者,近世小说《大秦帝国》假小人张仪辱骂孟子,网上亦有好而赞之者),“腐鼠之吓”,不亦宜乎!
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此言非为盗拓开脱,旨在降偶像之神坛,绘肉食者之面目耳。道德仁义为权位所饰耳,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织而衣,不耕而食,仗世袭之周礼,久居天下之公器,久借天道之公德,而孔子为肉食者做教科书以役民,此庄子之所轻也。倘盗跖大事可成,焉知孔丘不为盗丘?
余曰:吾言盗跖篇,非言此也,此言出于胠箧,虽愤激于战国之篡弑,而愤激之过,亦有为盗贼开脱之嫌,以为彼之窃国者且侯,吾窃人之财有何不可?对于胠箧篇,吾尝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源于老子也,意似深刻,实则偏颇。三代以下无圣人,大盗何尝少哉?周之世,田成子窃齐国,而秦以后之世,王莽篡汉,魏、晋、宋、齐、梁、陈、五代皆篡窃之主也,比于衰周,岂有少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岂其然耶?圣人死,大盗愈多矣!大盗窃圣人之道,窃仁义,窃礼乐,窃其迹耳,其精意,岂能窃哉!田成子窃齐,国不过两百年,而子孙俘于秦以饿死;王莽窃汉,不及后而诛;魏、晋、宋、齐、梁之窃皆卜世甚促,岂能望隆周盛汉之长哉!呜呼!绝圣弃知,圣道不明,如五代末世,无望仁义之王,假仁义之霸者亦无,有立之强者亦少。乃人人群起相争,为帝为王,盗贼之多,莫过于此,大盗固无,而小盗如牛毛之多,其乱极,又岂能忍哉!不欲圣人之道明于天下,然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当何言?盗贼窃圣人之术,亦畏圣人之道,则为恶有所忌而不敢肆意,夺取有所惭而不欲公然。如无圣人之道,圣人道晦,固无所窃,亦何所忌哉!沦夷为禽兽之世矣!盗贼假圣人之术,非圣人之过也,盗贼何所不假,假刀以杀人,刀之罪乎?而乃欲掊击圣人,殚残天下之圣法,启秦之暴政,五四之矫激,文革之决裂,坏井田,菲薄五帝三王,焚诗书,批孔批儒,破四旧,而文化几于浸灭,人道夷于禽兽,流毒万世,乃与申韩同恶,庄生之言,尚谁欺哉!”田成子窃仁义,杀其君而篡齐,内无诛,外无讨,庄子叹仁义为人所窃,庄子不忧仁义之不明,而忧仁义之被窃,其忧也末矣。自东迁以来,王道衰,诸侯力政,篡弑相寻,桓文假仁义而霸,宋襄公亦欲假仁义图霸而成,败于楚,而有人犹称宋襄公之知礼义。宋昭公无道,宋文公行惠于民,收人心,杀昭公而篡。齐君失政,田氏亦行惠于民,收人心,至于田常杀简公而篡,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无公道矣。仁义之不明也,五霸之假也,宋文、田常之伪也,皆非仁义之真也。朱紫之相近也,斥紫非可以并斥朱也;草禾之相似也,锄草而非可以并锄禾也,辨之也。恶奸雄之窃仁义而绝仁义,岂不愚哉!非以止盗也,益乱耳!宋文、田常之窃仁义,所窃者,仁义之粗耳,仁义之精意,岂能窃哉!禹汤文武之仁义,岂能窃哉!故只能窃国,而不能窃有天下,窃不过十世,而不及殷周数百年之久也。而宋文、田常之窃国,虽得民心,当时不敢非,而后人皆谓之篡,大是大非无能乱也。且宋文、田常之篡,害于上而不及下,民安之,彼犹知仁义之利,而伪施恩惠于民以利民,不敢暴民也,不犹愈于乱天下使不得安,残民以逞之暴君盗贼乎?又可见宋文、田常伪行仁义,且能有国,若本王道之诚,以德行仁,则无敌于天下,可以王矣,孟子所以屡说齐梁之君行仁政也。
彼奸雄以道德仁义为饰,犹可有为也,犹能为治也,彼犹畏于名义而不肆然为恶,且故为善事以悦人心。若名义无畏,悍然为恶,不更可惧乎?至孟子之世,攻城杀人盈城,攻野杀人盈野,嗜杀戮而无恤于民,秦之暴政,则苛刑重役以刍狗天下之民,道德仁义无所饰矣,仁人之所伤也。孟子以不嗜杀人者为能一者,非如文武仁德之君也。不织而衣,不耕而食,汝织而衣乎?汝耕而食乎?织者,工之事,耕者,农之事,通货财,商之事,教育文化学术治理,士大夫之事,四民各有业也。行周礼,居公器,为公德,有何不可?开私学,有教无类,教三千弟子,诲而不倦,如此其勤也,为肉食者役民乎?不偏于何人也,传大道也,启民智也,为天下也,为万世也,下夫小人以卑陋之心测圣人,岂不可鄙乎?秦虽一统天下,焚书坑儒,而孔鲥藏《诗》、《书》,秦不能焚也,儒家尊于汉,秦不能能灭也。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反孔,不可谓不狂也,而岂足以损孔子日月之明哉!天下自有公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亘古及今而皆存也!
君曰后世借儒术谋稻梁者皆以孔丘为精神木偶,后世固有借儒术以谋富贵者,其为人之卑也;借孔子以文其私者,其心之伪也。孔子所谓小人儒,则当辨儒术之真,明孔子之道,孔子辨君子小人也,谓子夏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也。而不辨,使行其伪,儒为所乱,圣为所污,乃疾小人儒而咎于儒家,咎于圣人,批孔反孔倒孔,岂不过哉!岂不悖哉!
人皆有偶像,偶像亦为人利用,君子辨之耳,真可为偶像,则尊之,不可为偶像,则黜之,偶像之真伪,辨之。而胡乱打倒偶像,曰解放人心,曰追求自由,行无所师,言无所法,私欲横纵,群魔乱舞,真如末世矣!
庄子惴惴恐道术之被窃,而绝圣弃知,攘弃仁义,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仁义被窃,则弃仁义,货物被窃,则弃货物乎?粮食被窃,则弃粮食乎?因噎废食,不可也;因被窃而废所用之物,岂不愚哉!庄生忧之过也。庄生欲防窃,而曰:“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遯。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呜呼!圣人公物于天下,不藏也,圣人之治,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礼乐之化也。凡有所藏,则有所私,藏天下于天下虽巧,孰如公天下于天下之为大哉!所以被窃者,据为私也,孔子谓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示以公,无得而窃也。苟为私,此愈藏之,彼愈窃之,虽藏之愈深,而窃之益巧,不胜防也。饮食器具,百姓日用之常,圣人公之;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君子存之,圣人尽之,何忧于窃哉!
庄子愤仁义礼乐之被窃,是也,而弃仁义,毁礼乐,则过矣。彼欲防己之学术被窃,曰“藏天下于天下”,然其所谓真人,流于神仙术士,暴虐无道之嬴政亦以真人自居;恬淡无为,后世之士以为逃遁之辞;逍遥通脱,魏晋名士藉以放荡;重生贵己,懦鄙之夫以之苟且自私;学庄而过者,至于诋侮圣贤,荡弃礼法。庄学亦不免被窃也,而流弊愈甚!近代更假之以反孔反儒,祸尤烈矣!立言而不折中,荒唐之言而启妖诞,恣纵之说而长放肆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无防被窃也,慎己之立说也。
曰:盗跖篇以窃国者之恶甚于窃财者,伤世之语,岂为强梁开脱?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大道仁义智慧,美则美矣,过尤不及,物极必反,阳极必阴。老子所谓绝圣弃智,即绝巧智,去刻意,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子以卫道者自居,稍有意见,则谓之狂流,其攘臂之态跃然可见。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君子狂流,相去若何,盗拓孔丘,相去若何?残生伤性,处其薄不处其厚,处其华不处其实,其一也。孔子若丧家之犬,困于陈为蔡,凝滞于物,不谙于时,逆势而为,失之刻意;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之自由换儒门之富贵,三纲五常,上下尊卑,繁文缛节,为之刻意。绝圣弃智,绝尽刻意,天行有常,人本有性,见素报朴,返璞归真,大道至简,顺天时达人性,混混闷闷,仁义何为?圣人何为?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所谓三皇五帝生于长夜乎?人之为人,时势自然,岂圣人之功?圣人不死,彼愚民愚妇不自救,待圣人救于水火之中,于奴隶期翼主恩,乞丐望人施舍何以异?圣人不死,有圣人之准,纷纷嚷嚷,彼盗他篡,彼夺他争,强为之害之争之,何如人人自救,圣人不存,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乎?恶乎知圣人乎?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故藏金于渊,藏珠于渊,藏富于民,利而不害,为而不争顺乎天道,达乎人心,不拘一世之利益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自己处显,何为藏而私之?以子之言,孔子曰民可使之由之,不可使之知之,不亦藏乎,亦为私乎?
余曰:此出胠箧篇,非为盗跖篇,汝未读《庄子》乎?自苏子瞻以为皆辨赝作,汉初学庄而至极端病态者所作也,君何信之?徒为矫激谩骂,王船山以其粗鄙狼戾,吾未见其伤世也,妒妇骂市,则觉之矣。此篇以盗跖辱骂圣人,非但为盗贼开脱,且毁道德也,淫邪甚矣!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彼岐道德仁义为四,强分先后,固不知仁义也,仁义所以成道德,仁义者,道德之实也,其可二哉?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固有之,何谓大道废而后有仁义哉?原于天,而不能无仁,原于地,而不能无义,为人,而不能无智。老子何为反智哉?而以大伪出于智慧,而绝圣弃知乎?何其悖也!船山谓其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知老子矣。呜呼!秦焚《诗》、《书》,仁义亡矣;魏晋崇虚诞,智慧隐矣,老子之言,尚谁欺哉!君言仁义不可过,夫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仁过,不失为厚;义义过,则流为刻,申韩之尚刑名也。老子直曰绝圣弃知,虽曰绝巧智,亦恶能绝之,其为权诈,欲夺故与,岂不更巧哉!夫见异端非毁正道而不卫,不忠于道也。君辱臣死,正道被毁,儒者之耻也。善恶有别,圣狂有辨,孔跖不同,安可混之?如此,则为善为恶,为圣为狂,为仁为盗,皆无甚异,则善不足为,恶不足惧,圣不足称,狂不足訾,仁不足慕,盗不足耻,世道乱矣!
君子求仁而已,求仁而得仁,又何憾?困于陈蔡,命也,孰无困哉?以舜之仁孝,而不容于嚣父傲弟,且欲杀之,舜之困也;以汤文之圣,汤系于夏台,文王拘于羑里,汤文之困也;齐桓公逃于莒,晋文公逃于翟,辱于曹,桓文之困也;勾践辱于会稽,臣于夫差,勾践之困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亦何困也!比干忠谏纣而死,箕子佯狂,岂可责之残生损性哉?命也。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虽死何憾?而激励风俗,未为无功也。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往皆顺,一受挫则折,何足以成大业哉!项羽之百战百胜,一败于垓下则亡,无困境以磨之,而不能持其败也。舜之困于父弟而帝,汤文之困于桀纣而王,桓文之流亡于外而霸,勾践困于会稽而灭吴称霸,伊尹、百里奚之困而为王霸之佐,孔子困于陈蔡,而体天人之道,文王拘于羑里而演《易》,孔子困于陈蔡而有十翼之作,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下蚕,而成《史记》,孔子虽不成王霸之业,而修六经,教三千弟子,以继往开来,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而责其凝滞于物,不谙于时,逆势而为,失之刻意,岂不鄙哉!是不知人生之顺逆,不体圣人之用心,而何足以责孔?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不忍天下之仁也,非愚也,非刻意也。不可为,势也,为之,理也。天下大乱,虽不可救,而忍视之不理乎?虽不能救,终强于漠然视之,随其乱而乱久不止也。国欲亡而犹力挽之,臣之义也;父欲死而犹欲求医之,子之孝也;朋友不免而犹欲济之,君子之义也;天下大乱而匍匐救之,圣人之仁也。王船山曰:“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也。语相天之大业,则必举而归之于圣人。乃其弗能相天与,则任天而已矣。鱼之泳游,禽之翔集,皆其任天者也。人弗敢以圣自尸,抑岂曰同禽鱼之化哉?天之所生而生,天之所杀而杀,则是可无君也;天之所哲而哲,天之所愚而愚,则是可无师也;天之所因而有之,天之所无因而无之,则是可无厚生利用之德也;天之所治而治之,天之所乱因而乱之,则是可无秉礼守义之经也。……夫天与人之目力,必竭而后明焉;天与之耳力,必竭而后聪焉;天与之心思,必竭而后睿焉;天与之正气,必竭而后强以贞焉。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裁之于天下,正之于己,虽乱而不与俱流。立之于己,施之于天下,则凶人戢其暴,诈人敛其奸,顽人砭其愚,即欲乱天下而天下犹不乱也。功被于天下,而阴施其裁成之德于匪人,则权之可乘,势之可为,虽窜之流之,不避怨也。若其权不自我,势不可回,身可辱,生可捐,国可亡,而志不可夺!”鸿尝以为船山此言,驳斥自然任天说甚精,老庄尚自然而贱人为,举而委之于命,曰:“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孔子则知其不可而为之,不可,势也;为之,理也。礼乐之崩坏,人心之蛊,世之乱,国之亡,虽势不可回,而圣人以不忍之心为匍匐之救,虽不能挽其狂澜,而存仁义之心于天地,公天理于后世,以激励后人,终胜于任之而不为也。况可为而不为哉!任天之说是废人道而之于禽兽也。 孔子之悲天闵人,悲礼乐之崩坏,忧生民之不宁,匍匐东西而救之,沮溺嘲其徒劳,接舆诮其德衰,彼为逃遁,皆不知圣人之心也。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某不与易也。”则已斥其为鸟兽之道矣。周之不可复兴,命也;知不可而为之,性也,而亦命也。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岂为不知命而徒劳者乎!庄生以无可奈何,则安之若命,而圣人岂能安哉!天不与圣人同忧,而圣人忧天下之所忧。孔子周游列国,道皆不行,而孔子之德何尝孤哉!教授三千弟子,知之者有颜回,尊之者有子贡,继之者有曾子也。至于汉代,董子劝孝武折衷孔子之学,身虽抑于一时,而道伸于万世!孔子之努力也,吾代之对盗跖曰:“安知吾道不兴于后世哉!”君子尽其道耳,成于不成,天也,为不为,在我也。至若沮溺之隐,接舆之狂,庄生之独,欲期之旦暮,而固难求于旦暮也,名隐而道孤,谁复知乎!
董子治春秋,三年不窥园,可谓精矣,为人廉直,不为权贵所喜,而排为江都相,事王以道,王敬之。后言灾异,汉武帝且欲杀之,岂如商鞅、李斯之流逢迎人主之欲,而博取富贵乎?曰伸天以屈君,以道责君,欲抑君权也。其学正也,特言灾异多,杂于阴阳而不醇耳。然董子,固君子也,为当时群儒冠,非吾辈所可訾议也。 三纲五常,人伦人道也,此吾作有《三纲五常论》,汝可看之,此不详言。孰可无上下尊卑?乃天秩也,非为人之刻意。繁文缛节,后世之弊也,非可咎董子。绝圣弃知,绝尽刻意,恐智慧亦绝矣,天有常道,而人不可同于天;人有性,当修身养性,存心尽性。而文明必欲向前发展,岂可倒退?天之不息也,日月风云多有变化,富有日新乃为盛德。混混闷闷,固可无忧虑,而麻醉自己,则成颓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不可须臾离也,圣人者,人极也,言而为天下法,行而为万世师,庄子后来亦服孔子定天下之定也。
朱子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极称孔子之圣,昭垂万世,如日月之明,非曰无孔子,则万古为长夜也。《中庸》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其喻尤大矣!岂曰孔子为天地,无孔子不可覆载?圣人者,众人之耳目也,泰古之时,三皇五帝为之耳目;三代以下,孔子为之耳目,若无三皇五帝与孔子,则无华夏如此文明矣,圣人领袖群伦,指导群生也。圣人非为救世主也,为天下之明也,非手援天下,以道援天下,天下之大,人之多,非可尽救也,孔子曰:“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圣人教人以仁义礼智,使之相爱相敬而相救,且自救也。圣人处万民之中,而深体其疾苦,与之相亲,岂自居万民之上,使民感恩跪拜乎?所以教人自立自强,岂如乞丐望人施舍乎?君之言也何鄙!天下无准,各有是非,汝以为是,我以为非,汝以为善,我以为恶,乱矣,圣人为人立标准以定之也,而所立之标准非为一己之造作,顺乎天理人情也。圣人制礼乐,正使人不争也;兴庠序,正教人自救也。凡世必有进,今之天地不同古之天地,天地犹有变化,况人世乎?而可返于丛林,与禽兽同居?常曰自然,此岂不逆自然乎?庄子既曰立仁义,而有窃仁义者,欲攘弃之,则藏金珠利器,亦有窃金珠利器者,则又何藏哉!何不毁之?苟兴礼乐,人皆忠信,利器又何不可示之有?利器可长保为私有乎?若礼乐崩坏,人心多不古,虽固守之,亦难免篡弑之祸。问孔子曰民可使之由之,不可使之知之,不亦藏乎,亦为私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强与民说也,岂为藏哉?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于《代孔子驳盗跖》文答网友发布于2021-07-06 10:4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