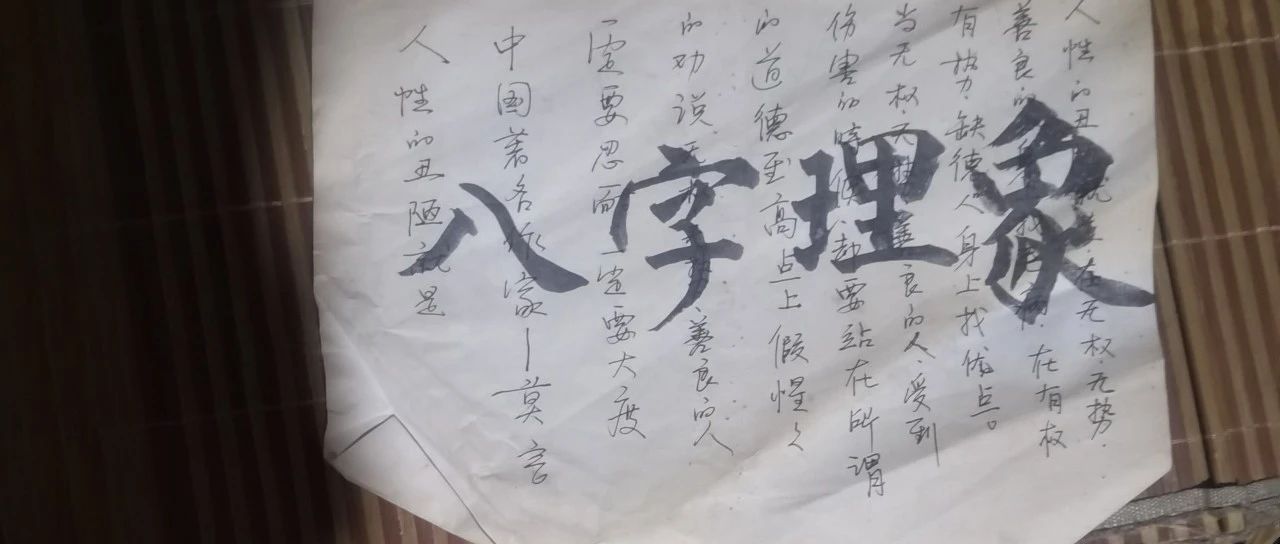摘 要:宋明期间,译者主要聚集于丝路地带、译馆与译经院所在地、文化中心地三个区域。丝路地带是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汇碰撞地区,民族语佛经译者和汉籍译者因此大量涌现。译者集聚于译馆及译经院的原因在于——统治者为创制与推广本族语言文字,高度重视民族语翻译,加之政权巩固与治世所需,提倡翻译儒家经典,民族语译者和儒学译者于是涌现。译者集聚于文化中心地的原因在于,在当时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文人志士和外国传教士大量聚集于文化中心地,从事科技翻译,科技译者因此大量涌现。宋至明三大译者集聚地形成原因折射出译者分布与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地域内异质文化交汇程度越高,译者集聚程度相应越高。
关键词:译者的地域分布;文化交汇;丝路地带;文化中心地

1. 引 言
自从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以来,文化的沟通者——译者顺理成章成为翻译界的研究热点。按照研究理路,译者研究大体分成三类:1. 译者的翻译人生与翻译方法的梳理与提炼,如贝拉德—奥泽罗夫等(Beylard-Ozeroff et al 1998)、李德凤等(2018)、伍兹沃斯(Woodsworth 2018)。2. 译者翻译行为的社会文化解读,如贺爱军(2009,2015)、贝克(Baker 2010)、德利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 & Woodsworth 2012)、周领顺(2014)、雷夫叙姆(Refsum 2017)、任东升和朱虹宇(2019)。3. 译者的地理分布规律探究,如贺爱军和王文斌(2012)、李亮亮和贺爱军(2014)、高敏和贺爱军(2018)、贺爱军(2018)。

以上三类研究,或对译者档案钩沉索隐,或利用西方翻译理论解读译者的翻译行为,或聚焦于译者行为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三类研究提炼出不同历史阶段的译者数量与地理分布规律,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但美中不足的是这类研究探究的“是什么”而没有进一步阐明“为什么”。换言之,这类研究仅仅止步于译者的分布规律研究,而没有深入挖掘规律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缘由。本文以北宋至明朝的译者地理分布规律为研究对象,深入开展“为什么”研究,即探究北宋至明朝译者地理分布规律背后的社会文化理据。
2. 宋至明译者的地理分布规律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的语言文化现象,发生于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于特定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贺爱军 2018:57)我们统计发现,北宋至明朝译者共有464人,分布于丝路地带、译馆及译经院所在区、文化中心区。这三个地带构成了宋明期间译者的生发地与活动区。

按照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中心地的形成受制于市场、交通、行政三原则。不同中心地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和中心性(克里斯塔勒 2016:29)。“中心地”原理说明了中心地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以及对区域形成的影响。翻译作为典型的文化活动,翻译区域的形成与翻译中心地的文化特性关系密切。一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形成一定的文化圈。“文化源地是文化圈的核心地区,文化扩散地区是文化的受容区”(周尚意,等 2004:135)。宋明时期是中华民族多种文化交融的活跃期,译者在促进不同民族语言沟通、文化扩散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是宋明时期翻译活动生发的根本原因。依据“中心性”体现中心地特征这一原理,我们推导出文化中心地与译者地理分布之间的关系。某一地区文化交汇程度越高,文化交流越频繁,译者愈趋集中。宋至明文化交汇地及译者集聚地见图1。

图1. 宋朝至明朝文化交汇地及译者集聚地
丝路地带、译馆及译经院所在地、文化中心地构成了宋明时期主要的文化交汇地,其地理位置不同,文化中心性及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不同,导致了译者的集聚程度有所差异。
3. 多民族交融与文化交汇:丝路地带译者的集聚缘由
丝路地带是宋明时期中外交流的核心地区,多个民族聚居于此,多种文化在此共存,翻译活动因此十分频繁。五代十国以降,辽、宋、金、西夏多民族政权同时存在。辽国建立后将内蒙古赤峰作为行政中心,境内契丹族与西部、西北和北部地区的党项族、回鹘族、汉族等往来频繁。金灭辽后,女真族散居至辽地和汉地,在与他们杂处共居中,女真族人接受并学习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西夏的党项文化则以甘肃、宁夏为中心,与汉、回鹘、吐蕃文化交流融合。西藏在元朝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藏传文化从而与其他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而蒙古、藏、回、满、汉等族文化在明朝时交流频繁。丝路地带地处边疆之地,而边疆之地往往也是文化交融之地,多种语言和文化在此交汇与交融,从而“成为译者生发的摇篮”(Hung 2005: 49),构成译者集聚的重要原因。凭借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和朝气蓬勃的边境文化,丝路地带成为北宋至明朝之间首要的文化交汇地。多种文化交汇与交融,营造了民族语言、文化交流的浓郁氛围,促进了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唐蕃古道沿线的民族语佛经翻译活动,也激发了丝路地带的民族语佛经译者和汉籍译者的大量涌现。
3.1 多民族佛教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民族语佛经译者的生发
丝路地带多民族佛教文化的交汇促使民族语佛经译者大量涌现。与五代十国以前佛经翻译不同,民族语佛经翻译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翻译重点,这一结果的形成得益于丝路地带丰富的多民族佛教文化。

首先,丝路地带多种佛教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语佛经翻译的盛行。宋明之间,丝路地带的佛教包括回鹘佛教、西夏佛教、藏传佛教,而新疆、甘肃、宁夏、西藏各地民族佛教相互借鉴,共同促进。新疆地区尤其如此,吐鲁番、昌吉和喀什等地佛教兴盛,并随着回鹘、契丹、蒙古、汉等民族迁入新疆,回鹘语、蒙古语、察合台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汉语开始通行,民族语佛经互译活动蓬勃开展,多民族语佛经译本数不胜数,民族语佛经译者成批涌现。

其次,多民族佛教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佛教中心的形成,而佛教中心往往也是佛经译者的集聚地。宋明之间,丝路地带沿线形成两大佛教中心,相应产生了两大佛经译者群。第一个是回鹘佛教中心,以高昌(今吐鲁番)、北庭(今吉木萨尔)为中心的回鹘国历时四百余年,期间佛教盛行,产生了数量不菲的回鹘语佛经译者。龟兹的回鹘佛教同样发达,形成了高昌、北庭、龟兹、哈密、敦煌、张掖等回鹘佛教重地(王红梅、杨富学 2015:19)。频繁的民族语佛经翻译活动催生了众多翻译名家,如宋朝的北庭人僧古萨里,精通古汉语、古龟兹、梵语、突厥等多种民族语言,贡献多部佛经译作。喀什人马合穆德·喀什噶里,回鹘人括鲁迪·桑伽失里,西夏人白智光、白法信,元朝的北庭人安藏、全普庵撒里,畏兀儿人迦鲁纳答思,回鹘人本雅失里等人受多种佛教文化的濡染,从事佛经翻译,译经成果丰硕。公元9至15世纪,回鹘人翻译了大量的佛教、摩尼教、景教典籍。唐末至明初,回鹘人已将《大藏经》中的重要经典译成了回鹘文(杨富学 2003:269)。如频繁而规模宏大的回鹘文佛经翻译造就了一批民族语佛经译者。

第二大佛教中心是形成于西夏时期的河西、陇右地区。佛教自北凉以降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形成了甘、凉、肃、瓜、沙等佛教中心。党项族受汉、回鹘、吐蕃、契丹等族佛教信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其交流甚密。佛经汉译的兴盛促进了西夏文佛经翻译活动,“西夏遗存佛经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依据中原汉传佛经翻译的西夏文佛经;另一类是根据梵、藏文新译的”(孙伯君 2007:307-308)。可见,佛经的西夏文翻译成为当时西夏翻译活动的重点,译者包括汉僧、藏僧和党项族僧人。汉僧有周慧海、赵法光,藏僧有格西藏琐布,党项族僧人有西玉智圆、鲁布智云等。他们以宁夏为翻译中心地,构成了西夏文译者主体。两大佛教中心聚拢了回鹘文和西夏文佛经译者,也成为丝路地带的译者生发地。

再者,藏传佛教的兴盛是丝路地带佛经译者生发的重要因素。后弘时期(公元978年以后),藏传佛教融合了本土元素,在多康、阿里等地得以复兴。元朝时藏传佛教传入内地,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快速发展,达至顶峰,促进了汉、藏、蒙多民族佛学交流。阿里、日喀则、拉萨位于边疆之地与唐蕃古道沿线,内外沟通便利,成为佛经译者的集聚地。这些地区既有利于外族译者阿底峡、作信铠等入藏传播和翻译佛经,也方便了藏族译者八思巴、扎巴俄色等人对外发扬藏传佛教。丝路地带各民族用本族语翻译佛经,致力于发展本民族佛学文化,也促进了回鹘语、西夏语、藏语译者的生发。
3.2 汉文化对西域的熏陶:汉语典籍译者的涌现
如果说佛教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助推了丝路地带民族语佛经译者的生发,那么悠久灿烂的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则成为汉语典籍译者生发的重要原因。丝路地带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频繁,汉籍翻译成为他们学习汉文化的重要途径,汉语典籍译者因此人才辈出。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肇始于先秦,于唐朝达至顶峰,历经宋、元、明而经久不衰(王聪延 2015:119)。隋唐以来,天台宗、禅宗、净土思想等汉传佛教在西域地区深入传播,畏兀儿(即维吾尔)地区尤其显著,大量的汉语文献得以翻译成回鹘文。公元9世纪中叶后,中原文化与丝路地带少数民族文化频繁接触,回鹘、畏兀儿佛经译本直接来源于对汉本佛经、中土僧人传记和灵应冥报故事的翻译,如《玄奘传》《净土宗创始人慧远传》《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等。译者僧古萨里精通汉语,译作丰厚。宋以后,汉文化对新疆回鹘民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几乎涵盖古代回鹘精神文化所有领域”(杨富学 2003:374),丝路地带艺术形式无不受汉文化濡染。元朝时期,丝路地带的儒学文化愈益蓬勃发展,而此时畏兀儿人大举内迁,接受了汉地文化的熏陶,成就了一批儒学名士。同时,他们以译者身份向中原传播畏兀儿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如安藏世居别失八里,自幼学习浮屠法,同时谙熟儒学,将《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译成蒙古文,亦都忽立兼修儒、释、道,从事回鹘文翻译,舍蓝蓝翻译《华严经》《楞严经》等汉文典籍。

丝路地带同样是北宋至明朝之间口译者的集聚地。他们多为战事所需或完成朝廷对西域管辖的使命,往来于此。以中亚和西亚为翻译地的译者有7人,其中以成吉思汗西征的随军翻译身份到达这些地区的就有耶律阿海、田镇海、阿里鲜。阔儿古思在成吉思汗长子术赤镇守花剌子模时担任翻译,爱薛作为译者,多次出使伊利汗国。明朝的马里麻和迭力月实曾出使撒马尔罕。总之,正是在汉文化与西域地方文化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民族语宗教译者、汉语典籍译者、口译者大量涌现。
4. 政治中心地:译馆与译经院译者的集聚地
如果说丝路地带构成了宋至明译者的首要集聚地,那么地处政治中心地的译馆与译经院则构成了宋明时期译者的第二集聚地。宋至明初,历朝政府在政治中心地设置了许多译馆和译经院,吸引了译者集聚于此。及至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带着大量宗教典籍和科技知识,来到京都,同时统治者为加强京都的文化职能,制定政策吸引译者和各种文化资源。正是在这些举措的激励下,政治中心地变成为了翻译的兴盛地和译者的生发地。

宋明之间,统治者们通过设置译馆及译经院,招纳民族语译者和儒学译者,设置译史官,开启了佛经典籍的翻译。宋朝设译经院太平兴国寺,“(译经院)成。诏天息灾等各译一经以献,择梵学僧常谨、清沼等与法进同笔受缀文,光禄卿汤悦、兵部员外郎张洎参详润色之”(李焘 2004:523),译经院集聚了众多译者,由梵学僧人和士大夫组成,如天息灾、法天、施护等;梵学沙门参与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职责;译稿完成后经由士大夫担任的润文官进行润色刊定。辽朝君主耶律隆绪、耶律倍和大臣萧韩家奴等亲自翻译,成为了卓有成就的汉籍译者。政治中心是辽朝译者活动的中心,辽朝在州以上官署中设置译史,如国史院、翰林院、枢密院等,“统和元年(公元983年)四月,枢密院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脱脱,等 1974:110)。西夏设高台寺、承天寺作为皇家译经院,译者以西夏文佛经译者为主,如帝师波罗显胜曾将禅宗典籍译成西夏文和回鹘文。金朝的尚书省、弘文院、礼部等负责译校经史,译者如国史院的徒单子温等。元朝宣政院、中书院、翰林国史院设译官“怯里马赤”“必阇赤”“译史官”等,多由士大夫担任。明朝设有四夷馆、会同馆、历局,文人志士和传教士为主要翻译人员。这些译馆或译经院从而成为宋至明译者的聚集地。

此外,宋至明时期,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不充分,统治者出于思想治世所需,设置了大量的译馆和译经院。这些译馆和译经院从事多语种翻译,满足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相互借鉴,也成为译者生发的渊薮。
4.1 民族语言文字的创制与推广:民族语译者集聚的依据
宋明之间,翻译是少数民族政权创设和改革文字的中介。统治者为了创新与发展本族语言文字,主张借鉴吸收其他民族语言文化成果,民族语言翻译因此而兴盛。如金朝建国前并无女真文字,在破辽过程中,不少契丹、汉族文人被俘,女真贵族主动向他们学习语言知识,“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陈佳华,等 2007:107)。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本国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脱脱,等 1975:1684)。金朝为推广应用女真字,解决女真学课本问题,着手翻译汉籍(马祖毅 2006:219),金朝六部等机构中设立了大量的译史官,如吏部令史杨克宗、行台省译史张九思等。西夏本无文字,党项人内迁后,通过翻译,掌握了汉文和藏文。元昊精通藏文和汉文,他借鉴这两种语言,依据西夏语特点创修西夏文字,并命野利仁荣演绎成12卷的西夏文字。高僧和当权者构成了当时的西夏译者主体,高僧译者如周慧海将《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译为西夏文,当权者译者如神宗遵顼、惠宗李秉常等。元世祖为统一民族文字而创制新文字,授命八思巴主持。八思巴与畏兀儿人文书奴等,融合藏、梵、畏兀儿、蒙文的特点,创制出“八思巴字”(或称“蒙古国字”),用于书写蒙古语,译写各种语言。为了推行蒙古国字,元大都建立了国子学,学员经考试担任学官或译史。忽必烈还多次下令以新字翻译汉籍、佛典(热扎克,等 1994:151-152)。少数民族政权通过翻译来推行本民族文字,强化了译者的作用。“译者在传递文化的同时,也促进语言本身的演变”(Delisle & Woodsworth 2012: 21)。正是在通过翻译创设与推广民族语言文字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民族语译者。
4.2 政权巩固与治世所需:儒学译者的集聚理由
翻译也是古代统治者推崇信仰、巩固政权的文化手段。宋至元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笃信儒家文化,重视培养儒学译者。如辽朝的辽兴宗命耶律庶成将汉语典籍《方脉书》翻译成契丹语,“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陈佳华,等 2007:36)。金朝金世宗大力倡导女真人学习儒家文化。为了使不懂汉语的人学习儒学,他特设译经所,命人翻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脱脱,等 1975:185)。西夏统治者则同时贯彻佛教和儒家思想。元昊秉持儒家理念,借用中原王朝政治制度,通过翻译贯彻儒家信仰。仁孝时期宗室濮王仁忠、舒王仁礼、宰相斡道冲,精通汉文和西夏文,用西夏文翻译《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类林》《孙子兵法三注》等。蒙元帝国“为了巩固本族统治和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了大规模的官方有组织的翻译活动”(王宏印 2017:23)。蒙古族人进入中原内地时,不通汉语,为了学习汉文化,忽必烈特地任用翻译人才如赵璧、王遵、马充实等儒士。赵璧受命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典译成蒙古文,供忽必烈阅览,并作为教授蒙古学生的教材。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设京师蒙古国子学,“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这对儒学在蒙古族中的传播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罗贤佑 2007:56-57)。儒学有裨政治,成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治世的推崇对象,而他们推动的儒学经典翻译则促成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儒学译者的生发。
5. 文化交汇与西学东渐:文化中心地译者的集聚
宋至明译者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动态趋势。宋元期间,译者籍贯地和翻译地主要分布于西部和北部地区,而到了明朝,南方的译者数量增多,译者中心地实现了南移。就宋至明之间的译者数量而言,则发生了由北多南少到南多北少的转变,其原因在于文化交汇中心的历史转移。宋、辽、金、西夏时期,丝绸之路是文化的交汇地,宋至元,北方政治中心是文化交汇地,及至明朝,南方地区则逐渐成为文化枢纽与中心。文化交汇地的地域变动是译者地理分布变化的根本缘由,也是宋至明译者分布由西部地区转向北方地区,再到南方地区的根本理据。

明朝时期,南方是多数译者的出生地,如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王岱舆、赵士桢、伍遵契、周希令等,也是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地,如利玛窦、傅汛际、艾儒略、罗明坚、苏如望、郭居静、潘国光、卫匡国等,他们集中于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福州、广州等南方城市,从事宗教宣传与科技翻译。

明朝译者地理分布规律可从文化交汇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得到解读。首先,译者的地理分布受到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宋至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反复多次的民族融合与分离、战争与和平,总体上是由北向南的民族迁徙,京城和中央的政治经济中心南迁东移的复杂而缓慢的过程(有时候是激烈的,断裂性的)。这个阶段作为民族典籍形成的文化基础,充分体现了民族生态和地域文化的特点”(王宏印 2017:21)。之后,南方文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中国文化重心逐渐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成为文化中心地。

其次,明朝中后期,中西文化碰撞,对文人志士的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使他们乐于吸收西方文化,实现救国强国。“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实学思潮逐渐兴起,究其原因,既有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可循,又有外部新的时代要素的推波助澜”(王静 2018:38)。一批批西方传教士携带大量的科技书籍,来到中国,与当朝士大夫合作,开展译介,如利玛窦“携其所印书册甚多”,汤若望个人藏书3000余册,金尼阁返华“携带7000余册。书籍见顿香山澳,俾一朝得献明廷,当必发仪部及词林,与西来诸儒翻译雠订”(陈卫平 1992:55)。蜂拥而至的西方科技书籍正投文人志士的所好,成为他们实现翻译救国的材料。如李之藻“体认西方科学的长处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学’价值之后,投身于译撰、刊刻西学图籍、播引西方学术治学活动”(王力军 1994:85)。徐光启以“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之务实态度不断完善《几何原本》的翻译(王静 2018:97)。西方传教士如傅汛际“著有《寰有铨六卷》《名理探十卷》,并与李之藻同译为亚利斯多哲学之一部分”(徐宗泽 1949:370)。伏若望“终身在浙江传教,著有《助善终经》《善终助功》《五伤经体规程》”(徐宗泽 1949:374)。这批译者集中于南方中心城市,从事科技书籍的译述,成为明朝时期的译者主体。
6. 结 语
丝路地带、译馆及译经院所在地、文化中心地构成了译者生发的渊薮。丝路地带民族文化交汇,民族交流频繁,民族语佛经译者、汉语典籍译者与口译者咸集于此。宋明之间历朝统治者为加强文化统治、发展民族语言,在政治中心地设置译馆和译经院,译者因此大量集聚。宋明期间文化交汇地不断南移,及至明朝,南方的文化中心地变成了译者的主要集中地。多元文化交融是翻译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枢机,宋明译者三大集聚地的形成,彰显了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对译者地理分布的深刻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翻译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及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AYY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Baker, M.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in the war zone: Narrated and narrators[J]. The Translator,2010 (2), 197-222.
[2] Beylard-Ozeroff, A., Králová, J. & B. Moser-Mercer. Translators' Strategies and Creativity[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3] Delisle, J. & J. Woodsworth.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4] Hung, E. Cultural borderlands in China’s translation history[A]. In Hung, E.(ed.).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Studies in History, Norms, and Image-Projection[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43-64.
[5] Refsum, C. When poets translate poetry: Authorship, ownership, and translatorship [A]. In Alvstad, C.,Greenall,A.K., Jansen, H. &Taivalkoski-Shilov, K. (eds.). Textual and Contextual Voices of Translation[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7:101-118.
[6]Woodsworth, J. Gertrude Stein and the paradox of translation [A]. In Woodsworth, J.(ed.). The Fictions of Translation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8:31-48.
[7] 陈佳华,等. 中国历代民族史:宋辽金时期民族史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 陈卫平. 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 高 敏,贺爱军. 明末至晚清译者的分布规律及其探源 [J]. 中国科技翻译,2018(2):59-62.
[10] 贺爱军. 鲁迅“硬译”的文化解读 [J].上海翻译,2009(4):70-73.
[11] 贺爱军. 晚清至“五四”的译者形象变迁及其缘由探源 [J].外国语,2015(3):83-90.
[12] 贺爱军. 浙江翻译传统及其对当下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启示 [J]. 中国翻译,2018(2):57-61.
[13] 贺爱军,王文斌. 浙籍译家群的生发及其缘由索隐[J]. 中国翻译,2012(2):38-42.
[14] 李德凤,贺文照,侯林平. 蓝诗玲翻译风格库助研究 [J].外语教学,2018(1):70-76.
[15] 李亮亮,贺爱军. 明清译者的构成及其地域分布[J]. 上海翻译,2014(1):74-77.
[16] (宋) 李 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17] 罗贤佑. 中国历代民族史:元代民族史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8] 马祖毅. 中国翻译通史(古代卷)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19] 热扎克·买提尼牙孜,等. 西域翻译史 [M].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20] 任东升,朱虹宇. 沙博理与葛浩文之不同:制度化译者行为视角[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2):55-66.
[21] 孙伯君. 西夏佛经翻译的用字特点与译经时代的判定 [J]. 中华文史论丛,2007(2):307-326.
[22] (元)脱 脱,等. 辽史(第1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 (元)脱 脱,等. 金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85,1684.
[24] 王聪延. 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及其作用 [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19-124.
[25] 王红梅,杨富学. 元代畏兀儿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
[26] 王宏印. 典籍翻译:三大阶段、三重境界——兼论汉语典籍、民族典籍与海外汉学的总体关系 [J]. 中国翻译,2017(5):19-27.
[27] 王 静. 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 [D].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28] 王力军. 简述李之藻的治学观及其西学图籍 [J]. 浙江社会科学,1994(3):85-89.
[29] [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 常正文,王兴中,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0] 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49.
[31] 杨富学.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32]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3] 周尚意、孔翔、朱翊. 文化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贺爱军,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史与翻译家、翻译地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
侯莹莹,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史与译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