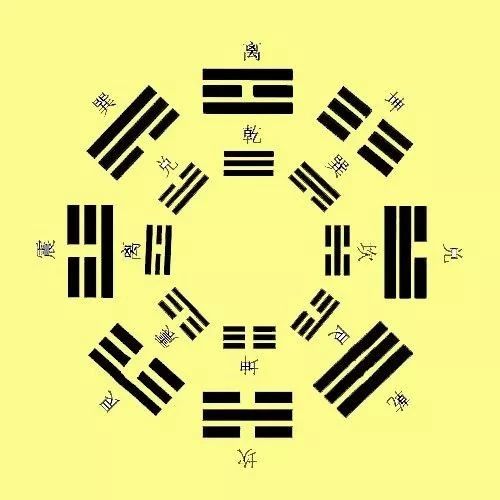摘 要:朱熹批评荀子的性恶论,但是两人在为学之道方面却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两人都主张由知识转向道德的路径,并且将“圣人”看作学习的目标和动力。“心”是连接知识和道德的肯綮。在荀子和朱子的系统中,首先,心都生而具备认知功能,而且是感官的主宰,能够辨别万物,认识万物的理义法则。其次,两人都在主张心性二分的基础上强调心对于性情的主宰作用,这使得人在进行道德选择和判断的时候可以依照其所认识的道德标准来进行,从而保证行为合乎道德。
关键词:荀子;朱子;心;为学;圣人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 :寻梦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自唐代韩愈将荀子排除道统之后,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们开始明确将荀子定性为“不醇之儒” 。程颐认为“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荀卿虽曰尊子弓,然而时相去甚远。圣人之道,至卿不传。” “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今且于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则条理分明,不待辨。” 一方面,二程和朱熹都是站在他们“性即理”的理论前提之下来看待荀子的人性论,因此认为荀子性恶之说破坏了其立论的大本。但另一方面,朱熹自己也说荀子是“论气不论性”,可见,理学所特有的二元人性论难说与荀子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说理学家们在批评指斥荀子思想的同时,又或主动或被动地吸收了荀子的思想。如康有为除了点出宋儒“气质之性”暗用荀子之说以外,他还从荀子和朱子都注重“学”以及注解传播经典的学术史地位看到了两者的相似性。
孔门后学有二大支,(孟荀),自唐以前,无不二子并称,至昌黎少抑之。宋人以荀子言性恶,乃始抑荀而独尊孟。然宋儒言变化气质之性,即荀子之说,何得暗用之,显辟之?盖孟子重于心,荀子重于学,孟子近陆,荀子近朱,圣学原有此二派,不可偏废。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犹群经皆注于朱子,立于学官也。二子者,孔子之门者也。舍门者而遽求见孔子,不可得也。
孟子,公羊之学。荀子,穀梁之学。孟子高明,直指本心,是尊德性,陆王近之;荀子沈潜,道问学,朱子近之。
为何康有为会认为荀子和朱子在重于“学”这一个方面有相似处呢?其相似处都表现在那些方面呢?这种类比有没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来说可以打破荀子之学缺席于宋代理学的迷思,另一方面,荀子和朱子都是潜心学问的大家,对他们为学之道的探讨无疑有助于学者学问之精进。
“学以至圣”命题的提出肇端于荀子,其《劝学》篇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后周敦颐在其《通书》中明确谈到“圣可学乎?曰:可。” 程颐也有类似说法,“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 陈来认为,“圣人可学”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特色,从教育的角度看,就是通过学习获得德性的发展。但知识与道德原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从属于事实层面的知识如何能够成就从属于价值层面的德性?这就需要在心上做一个转化,“以心体之,以身践之” ,因此探究荀子和朱子为学之道的重点必先探讨其对于“心”的观点,在打通作为道德与知识连接处的“心”之后才能研究两人为学的目标和方法。
一、荀子化性起伪与朱子变化气质
要学为圣人,必先克服自身的不完善。荀子和朱子都承认人有天生的欲望,但是荀子没有将欲望和人性分得太清,朱子借此批评“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而朱子虽然认为性即是理,性无不善,但是他却无法在理论层面克服纯善之理为何会导致违理之事的困境,因此他提出了“气质之性”的概念来做补充。而对于荀子“人性”与朱子“气质之性”的改造也就成为了学为圣人的起点。
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性”与“伪”被用来区分众人和圣人。他在《性恶》篇中说“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而区分“性”“伪”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学习礼义。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性者,本始财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
正如刘殿爵所说,荀子的这个定义并没有准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性,但是荀子确实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可以通过教养得到丰富和提高。相对于人性的探究,荀子更重视外在的礼义师法对于人性中“情”与“欲”的改造作用。顺人之情性,就会导致争端祸患,而如果以礼义化之,就会使得社会归于平治。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在荀子看来,“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 圣人不仅制作礼义,而且能够时时思考自己的所思所为是否合礼,待合礼之后,还能坚定不移地持守礼,从而达到即使“纵其欲”“兼其情”也能时时制焉于理,并且不会觉得勉强或难受。这种“人道之极”的状态也就合乎孔子所言“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了。
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故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无穷者,广之极也;圣人者,人道之极也。
因此,了解“礼”的知识也就成为荀子为学之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正如余英时所说“无论我们今天对儒家的‘礼乐’、‘教化’的内容抱什么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礼乐’、‘教化’是离不开知识的。” 而在荀子看来,礼是用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所以关于礼的知识其实也就成为了人的道德修养的一环。
朱子认为“性即是理”,“性只是仁义礼智” ,“所谓恶者,却是气也” 。而“气禀”是天生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天命与气是相互依存的,“天命之与气质,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 如果没有“气”,那么“理”就无处着落,孟子提倡性善,是“论气不论性”,其理论不够完备,而荀子的人性之所以会有“恶”的元素,就是因为他“论气不论性”,未见性之理,其性被遮蔽了。因此,与其责怪气禀遮蔽性理,不如用力克治,使得气禀合乎中道。可见,朱子人性论的落脚点还是在修习的工夫上,因为气禀既偏,则需要痛加工夫。他说,“若是气质不善,可以变否?”曰:“须是变化而反之。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朱子说“为学乃能变化气质耳。若不读书穷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计较于昨非今是之间,恐亦劳而无补也。” 在他看来,读书明理也是变化气质之途径,“读书所以明理,而明理者,欲其有以烛乎细微之间而不差也。故惟考之愈详,则察之愈密;察之愈密,则吾心意志虑,戛刮磨砺愈精。吾心愈精,则天下之理至于吾前者,其毫厘眇忽不齐,则吾必有以辨之矣。” 读书愈多,心对于事物之理就会了解得越透彻,这样在认识事物应对事物的时候自然就不会出差错。可见,变化气质的工夫也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学习的过程。
清儒戴震认为,荀子“化性”之说与宋儒“变化气质”之说是相契合的。
宋儒于性与心视之为二,犹荀子于礼义与性视之为二也。荀子以礼义为圣人之教,常人必奉之以变化其性,宋儒以性专属之理,“人禀气而生之后,此理堕入气质中,往往为气质所坏,如水之源清,流而遇污,不能不浊,非水本浊,地则然耳;必奉理以变化气质,使复其初,如澄之而淸,乃还其原初水也”。荀子之所谓礼义,即宋儒之所谓理;荀子之所谓性,即宋儒之所谓气质。如宋儒之说,惟圣人气质纯粹,以下即(实)〔质〕美者亦不能无恶;荀子谓必待学以变化此性,与宋儒〔谓〕必待学以变化气质,无二指也。
戴震这种类比是否成立呢?荀子的“礼”一方面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准则,“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者,节之准也。” “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礼也者,贵者察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 ;另一方面,礼是自然现象的规律所在,他说“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 陈大齐总结道,“荀子所说的礼,其范围至为广大,上自人君治国之道,下至个人立身处事之道,乃至饮食起居的细节,莫不为其所涵摄。” 如果从其涵盖范围来说,朱子的“理”似乎和荀子的“礼”是同一个意思 ,就连朱子自己有时也用“礼”来解释“理”,如他说“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 但是考虑到修习践履的下学工夫,朱子并不赞成“理”与“礼”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正如殷慧指出的,朱子在解释“克己复礼”和“约之以礼”的时候,如果用“理”来代替“礼”,“复理”、“约理”就会脱离现实精细的践履工夫,会导致学者们学无持守。反之,如果用“礼”来代替“理”的话,那么“理”也会失去其超越性的意义从而将修习局限于具体的社会道德实践而无法“上达”至“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天人合一”的境界。
需要注意的是荀子一方面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与“人”是相分离的,礼是圣人所生,但是他又说“礼”是“天地以合”的法则,可见在荀子那里主观领域与客观自然的界限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 这时候的“礼”和朱熹所提倡的作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其实是一个意思。这种对礼的一致推崇,也是荀子与朱子思想的相通之处。但要直接说荀子之“礼”就是宋儒之“理”则不甚妥当。
而至于荀子讲“以礼化性”和宋儒所推崇的“以理变化气质”都强调前者对后者的规范作用,强调两者的对立,而且“变化”的过程都要依靠学习、积累,在这些层面上来说,两者确有相通之处。但是荀子以礼化性论说的重点还是在于“礼”,甚至许多学者认为荀子讲性恶也只是为了让“礼”有施展的余地, 人根据“礼”去矫正情性、节制欲望,荀子认为欲望是人生而具有的,完全摒除和减少欲望都是没有意义的,人只能控制自己的心,保持心之 “中理”,以此来保证人的“所欲”“所求”合理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平治安稳。而“变化气质”的重点则应该是落在“气质”之偏上,强调尽可能擦除气质之蔽,这样很容易走向“以理灭欲”的极端,这是其不好的发展。
不过朱熹本人在谈到“气质之偏”的时候,其实也比较赞成先立一个大本,然后潜移默化地矫正其偏,“或问:‘气质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说偏了,又着一个物事去救他偏,越见不平正了,越讨头不见。要紧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处自见得。如暗室求物,把火来,便照见。若只管去摸索,费尽心力,只是摸索不见。若见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处,也自会变移不自知,不消得费力。’”
二、心是主角:荀子“以心治性”与朱子“心统性情”
朱熹和荀子都讲究心与性的二分,并且,心的主宰作用会影响道德判断,而只有当心自觉地依照礼义来进行道德取舍的时候,人的行为才会向善,这种自觉性又必须依靠心的修养工夫来达到。当心具有了这种自觉性的时候,人学习成为圣人才具有了可能性。
荀子人性论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那就是以“恶”为特征的人之本性为何能够意识到善的存在并且有选择善的倾向。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抽象为,在荀子的思想中“人如何获得道德的理解力以及去发展道德观” 的问题。这样,针对荀子人性论中的矛盾,我们就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人如何获得道德的理解力;其二,人如何发展道德观?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荀子到底是如何界定“道德”的?什么样的行为在荀子看来是合乎道德的。
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礼义者,治之始也。
礼者,人道之极也。
礼者,所以正身也。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荀子将“正理平治”看作评判善恶的标准, 要矫正人性之恶,必须明礼义、起法正、重刑罚,这三者中,又以“礼义”之明为中心。因为,礼,在荀子那里,不仅是社会治乱的评判标准,“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 同时,也是人类道德的终极目标,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可见,荀子界定道德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合乎礼义。
既然在荀子看来合乎礼义的即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人要获得道德的理解力,也就只需要去认识礼义,而发展道德观的过程也就是礼义践履的过程。荀子说“人何以知道?曰:心。” “道也者何也?曰:礼让忠信是也。” 可见,认识礼义的关键在于“心”,“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
事实上,心在人的认识过程中起者主宰者的作用。心是“天君”,“心居中虚以治五官” 。
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知而无说, 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
杨倞注释道,“征,召也。言心能召万物而知之。” 陈大齐先生的解释则更为具体。他说:“外界刺激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来斯受之而无所拒绝,却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以成知觉,其余则弃而不知。其所以有所取舍,出于心之召与不召。……释征为召,足以阐发欲知与不欲知之全完全操之于心。”
心不但是人身体的主宰,而且也是心灵的主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 心的认知和判断是完全自主的,但这种“自由意志” 并不必然保证心能做出合理的判断,从而使人的行为合乎道德,社会得到治理。
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
人性因为与人欲,人情这种驳杂的关系而时时呈现出下堕的倾向,而社会治乱的关键在于心对于情与欲的的把握是否“中理”。正如柯雄文总结的,在“荀子那里,我们发现了‘心’和‘情’之间更为明确的划分。‘心’有着不同于‘情’的主要认知功能。当这种功能被‘理’指导时,‘心’就能为‘情’的表达提供一种可靠的伦理指导。” 也就是说,只有当心“中理”的时候,人的情欲才能被治理,“心”与“性”别而为二,心通过对“理”的认识与把握来管束性情,“心之中理”是“以心治性”的关键。“理”和“道”在荀子书中,应为一物而二名,皆指客观的“礼义”而言。“人何以知道?曰:心。” 人心所认识的道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是以礼让忠信等为内容的道。“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所以“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 “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 只要心作出了正确的判断,那么,人的行为自然就会合理,就不会导致社会的祸乱。然而心怎么才能时时保证自己判断合乎礼义呢?人如何在认识礼义的基础上实践礼义呢?这就需要依靠养心的工夫了。
荀子“以心治性”是针对“性”所体现的为恶的倾向,心本身只是具有选择的能力,并不一定能进行合理的判断,荀子以“盘水”来比喻心, 心的选择完全依赖于外物的导引,如果导之以礼,心便能根据礼义来矫正人的情性,在这个路径上荀子和朱熹其实十分相似。朱子常说“心是管摄主宰者” ,但是他用镜子来比喻人心,他说“虚灵而能应万物者便是心。人心如一个镜,先未有一个影像。有事物来,方始照见妍丑。” 如蔡仁厚先生所言,“就朱子的思理而论,心之主宰也实只是管家之主,而不是当家的主人之主。” 徐复观先生对此解释得更为明晰,他说朱子的心是“勤俭成家的主宰,本无家当,只靠勤俭向外去找。” 可见,朱熹的心本身也不具备道德的判断力,这与陆九渊“心即理”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也和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体系不同,虽然具体到心和性、情的定义,朱熹和荀子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朱熹却与荀子一样,凸显心的认知功能以及主宰判断的能力,讲究心与性的二分,“谓性便是心,则不可;谓心便是性,亦不可。” 性理并没有内在于心,注重礼或理作为心之判断的依据。
朱子和荀子一样,将心看做是人的主宰。他说,“心,主宰之谓也。” “心者,一身之主宰。” “一身之中,浑然有个主宰者,心也。” “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 心还由于其生而具有的“知觉”和“思”而可以认识事物,并且理解事物的“理”。“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 。” “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觉,则是自心中有所觉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心则能思,而以思为职,凡事物之来,心得其职,则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心在明觉了“理”之后,就不会被闻见、人欲滞碍,从而可以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具此理而觉其为是非者,是心也。” “视听浅滞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测,故见闻之际必以心御之,然后不失其正。若从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则不为物引者,鲜矣。” 在此基础上,朱子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但是又由于“性”“理”不二的关系,“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 “性者,理也” “性只是理” ,所以朱子的心与性也应该是析而为二的,“心与性自有分别。灵底是心,实底是性。灵便是那知觉底。” “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处,又有析而言处。须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谓性便是心,则不可;谓心便是性,亦不可。” 心与性的区别还体现在,心有善恶的区别,但是性却全然是善的。“心是动底物事,自然有善恶。” “心有善恶,性无不善。” 心性虽有区别,但是就人而言,“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 所以心性“不可无分别,亦不可太说开成两个。”朱子非常赞成邵雍将心就比作性的的“郛郭” ,心就像城墙一样包围者性,也像皮包着陷,“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 正如钱穆所说,“人性只在心内,不在心外”,“具此性者为心,心便能收拾得住这性,检点这性,使之发生作用” 心性之间,既有区别又有会通,但总归心才是主宰,“心能检性,性却不能检心。心能包性,性却不能包心。”
在性与情的关系方面,朱子认为,“有这性,便发出这情;因这情,便见得这性。因今日有这情,便见得本来有这性。” 性与情的关系就像是形与影的关系,两者不可分离来谈,其区别只在于未发已发,以及静动的状态,他说,“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 “情者,性之动也。” 而针对胡宏以性为体,以心为用,以性为未发,以心为已发的观点 ,朱子认为,“直以性为本体,而心为之用,则情为无所用者,而心亦偏于动矣。” 在朱子的系统中,性情虽然互为体用,但是还有一个心始终作为贯统性情的总体。
“心者,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 “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 “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 “问:‘心统性情,统如何?’曰:‘统是主宰,如统百万军。’”,“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 通过心的主宰,性情被统一起来,以此为前提,朱子之心便可以兼顾体用、动静、已发和未发,“心贯乎动静而无不在焉。” “心则通贯乎已发未发之间,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
可见,在朱子和荀子的系统中,心都生而具备认知功能,以此来辨别万物,认识万物的礼义法则,而心对于性情的主宰作用又使得人可以在进行道德选择和判断的时候可以依照其所认识的道德标准来进行,因此,修养此心的工夫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养心工夫:荀子“虚壹而静”与朱子“主敬涵养”
荀子和朱子的心是连接知识与道德的肯綮,“心知”是人认识活动的开端,而如何保证心不受外物以及内在人欲、人情的干扰,维持心知的明白清晰,这就需要在养心上下工夫了。
在荀子那里,心是治理五官的天君,是一身的主宰,心还能思虑,人心的选择是否合理是社会治乱的关键。荀子说,“心也者,道之工宰也。” 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孟子说到心的主宰性时,即是心的仁义礼智来主导行为,这是可以信赖的。荀子说到心的主宰性时,乃是表示心对于行为的决定性,大过于其他的官能;但这种决定性的力量,并非等于即是保证一个人可以走向善的方向。”这是因为,“心的主宰性,是由其认识能力而来;心的主宰性之不可信赖,即是心的认识能力之不可信赖。” 现实中,人的心屡屡处于蔽塞的状态,“蔽于一曲,而闇于天理” 。
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为何万物都会成为心术的公患?王先谦解释“此其所知、所好滞于一隅,故皆为蔽也。” 周群振也说“盖欲、恶、始、终、远、近、博、浅、古、今等事物,就各自村子之当身而言,本来无所谓蔽,只因人心之印持或运作有所偏执,才会形成蔽。”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
既然知道心术的蔽塞来源于心的的偏执,圣人于是选择以“衡”为标准来“兼陈万物”。“何谓衡?曰:道。”这样,道,就成为了认识的标准。心只要认识了“道”,并且按照“道”来行事,心的主宰性也就以此而得以被信赖。这也是荀子经由知识的路径升华至道德的路径的关键所在。那么,心要如何认识道呢?荀子说: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壹;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
人通过虚壹而静的修养工夫来认识道。“虚”,在荀子看来,就是“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唐君毅先生认为,“荀子言心之虚,使人能‘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即言心以其能虚之故,便能不断更有所藏也。” 韦政通先生进一步将其申发为“心之无限制性” 。“壹”荀子解释为“不以夫一害此一”,久保爱对此的注解颇为新颖, “夫一,所好也。此一,所憎也。言不以所好之非,害所憎之是,唯义所生。” 久保爱认为荀子之“壹”重在祛除内心的成见,也正如谭宇权解释的“壹,即接受知识时,不以自己原有的知识排斥新来的知识。”只有在众多知识不互相干扰的前提下,心才具有了“统摄诸一之贯通性” ,反之,“心枝”则“无知”,“故知者择一而壹焉。” “静”与动相对,是“不以梦剧乱知”,杨倞解释为静心,“以静心思道,则万变无不察。”唐君毅先生也说,“此静实即同于用心之专注。心有所专注于物,则亦自能免于心之‘偷则自行’‘梦剧则乱’之妄动。然人免此妄动之后,即更能专注于物,以细察一物之内容。故曰‘静则察’。” 心通过“虚壹而静”达到“大清明”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如温海明所说,“所有的事物同时在心中呈现出来,事物所有的方面都为心一下子彻底了解,” 至此也就实现韦政通所言的心的“超越性” 。
荀子的“虚壹而静”保证了心可以达到“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的状态,而朱子的心,在其所具有的“虚灵”的特性和“知觉”的功能的前提下,讲究“主敬涵养”的工夫,亦可以达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状态。可见,二家言心的功能作用,也正相同。
朱子之心,有人心、道心之分。“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 ,“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 陈来先生总结为“道心指人的道德意识,人心指人的感性欲念。”
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义理难明而易昧,故微而不显。惟能省察于二者公私之间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厘之杂;持守于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顷刻之离,则其日用之间,思虑动作,再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
可见,“人心”之“危”在于其“易动而难反”,“道心”之“微”原因是“义理难明而易昧”。因此,要解除人心之危,守持道心之微,就“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也就是说要时时保持道心对人心的主宰作用。
事实上,朱熹非常重视心对于身的主宰作用,“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 ,主敬修养的工夫主要是在心上做,他说,“敬,是此心自做主宰处。”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世之本根也。” “敬只是提起此心,莫教放散。恁地则心自明。” “人当放肆怠惰时,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 “人常恭敬,则心常光明。”“敬非是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气象自别。存得此心,乃可以为学。” “敬则万理具在。” “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治。” 一旦达到了主敬的状态,那么人心自然就不会再被人的私欲所干扰而可以与理为一而成为道心了。
虽然人心是主敬涵养的主体,但如果只在心上下功夫,就会流于释老。因此,“朱熹主敬的涵养工夫始终突出强调内在的心性存养与外在的整齐严肃相结合” ,他说:
问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间断;一事有差,也是间断。”
问敬。曰:“不用解说,只整齐严肃便是。”
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
事实上,这也是朱子“内外交相养之道”的体现,人心常炯炯在此,则四体不待覊束,而自入规矩。只为人心有散缓时,故立许多规矩来维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
他认为修养工夫不仅仅需要依靠心之“常炯炯”或“常惺惺”来自入规矩,还需要考虑到现实中人心的散漫昏蔽,需要立许多规矩来常常警醒,检查,用以管束此心,引导此心符合“规矩”。朱熹的这种需要依靠外在标准来对心做权衡并且存养此心的做法,其实和荀子以“道”为标准并且依靠其来保持心的“大清明”的路径如出一辙。
人性被私欲蒙蔽,需要养心工夫使得心达到荀子的大清明,朱熹的明理全体的境界,这样,学习也就有了一个落脚点。心的这种主宰作用,为学提供了一个宰体,或者说是一个学习的器官,心在朱荀都有用心官来概括心,就是这个道理。一方面,养心的工夫保证了心可以达到大清明的状态,让心可以像筛子一样过滤接收的知识,另一方面,“心知”“心虑”也可以促进知识的内化,促进知识向德性的转化。
四、小结
朱熹批评荀子的性恶论,但是两人在为学之道方面却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两人都主张由知识转向道德的路径,并且将“圣人”看作学习的目标和动力。“心”是连接知识和道德的肯綮。在荀子和朱子系统中,首先,心都生而具备认知功能,而且是感官的主宰,能够辨别万物,认识万物的理义法则。其次,两人都在主张心性二分的基础上强调心对于性情的主宰作用,这使得人在进行道德选择和判断的时候可以依照其所认识的道德标准来进行,从而保证行为合乎道德。因此,养心工夫就显得十分重要。荀子主张“虚壹而静”,解除“心术公患”,使心不会“蔽于一曲”,有所偏执;朱子提倡“主敬涵养”,辨别人心道心,提倡“内外交相养之道”。
对两人来说,一方面,养心的工夫保证了心可以达到大清明的状态,让心可以像筛子一样过滤接收的知识,另一方面,“心知”“心虑”也可以促进知识的内化,促进知识向德性的转化。荀子和朱子都主张经验主义的方式求知,讲究循序渐进的为学,重视日积月累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又得通过“参省乎己”、“反身而诚”的工夫贯穿到主体的生命中,成为一种德行。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与德行也就得到了统一。此外,两人看到了 “效”仿圣人这一条教育的捷径,强调师法教化的作用。圣人之学一方面是先“为己”再“为人”,先“成己”再“成人”的学问。因此,成为圣人一方面需要完善自己的德性,荀子主张“化性起伪”朱子主提倡“变化气质”,都是为了使自己的“气象”更接近“圣人”;另一方面,两人都看到了“圣人”之“知”与“行”通常是不相分离的,因此为学既要“明理”又要“明伦”,既要“修身”又要“齐家”、“治国”、“平天下”。
荀子劝学, 荀子, 荀子简介,荀子修身,劝学荀子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学以至圣:荀子、朱子思想相通处在为学上的体现发布于2023-03-19 21:2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