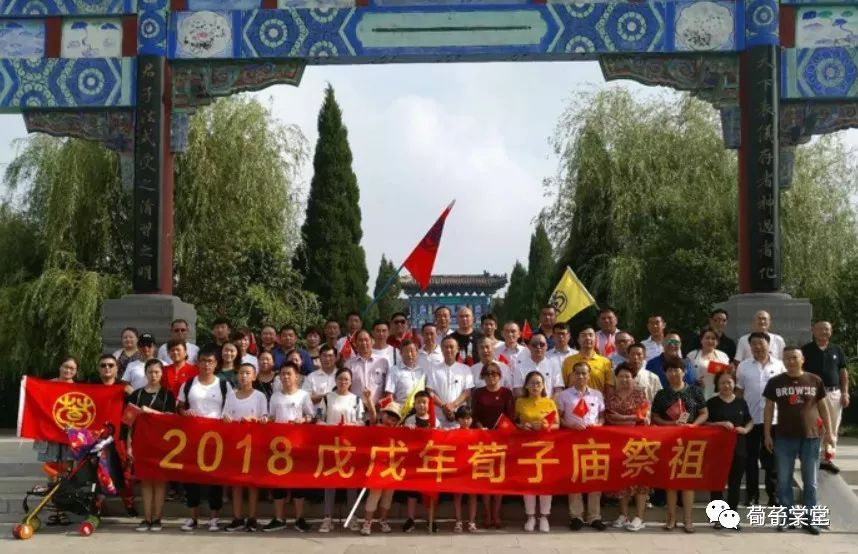摘 要:東晉王坦之以〈廢莊論〉為題,進行對莊學批判;到了晚唐,李磎著〈廣廢莊論〉,擴充深化王坦之的〈廢莊論〉。二者「反莊」之論,皆是一方面批評莊子思想的謬誤,一方面站在儒家立場,捍衛名教。從理論上來看,二者「廢莊」之論屬於無效的論證;但就思想史來看,卻有另一層深意。他們自覺地援引荀子學說,為儒家思想作辯護,在兩晉到晚唐的尊儒抑道的活動中,成為一股旗幟鮮明的主張。而他們的反莊之論,也不僅止於外緣性的否定莊學而已,更多的是針對當時思潮的若干主題進行反思與闡發。如王坦之以荀學的中道論進行儒道會通;李磎則進一步地以荀學論證莊子之非,從虛無、天人、性情論證成儒家學說。由此看來,同題之「廢莊」著作,不只「廢」道,還要「立」儒。在思想史上,呼應了晉唐以來儒學的發展,呈現出異於韓愈道統論的尊孟立場。
关键词:荀子;廢莊;中庸;天人;性情;道統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
收稿日期:2018-10-01
作者简介 :段宜廷,台灣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台灣政治大學中文博士。
一、緒論
思想史上有兩波重要的尊儒抑道思潮:一是魏晉、一是唐代。魏晉時期玄風熾盛,學術上以道家思想為主流;至唐代道教教義、理論得到空前發展,佛老盛行。道家的玄遠幽深,的確吸引了許多士人,然而道家道法自然、萬物自化,最終仍會走向排斥人為的路數,故以社會倫常為己任的儒家,自會批判道家。而「尊儒抑道」並非始於魏晉儒家,早在先秦時期,如孟子非議楊朱、荀子批評老莊就已經在維護儒家的道統了。不難發現,魏晉時期會通孔老,孔子成為了主要的詮釋對象;而中晚唐時期,則由韓愈的道統論,轉為尊孟立場。然而考察歷史,荀學在當時其實是一股很強勁的學術資源。我們從當時政治社會的變動及其思想趨向觀之,在士人崇尚「自然」的虛浮世風下,勢必會更加強調一個規範的世界、重禮的社會,因此可以合理推論,儒者需要借重荀學,以求撥亂反正,重建社會秩序。像兩篇著名的「廢莊」之論,就透露出「以荀廢莊」的意涵。即東晉王坦之以〈廢莊論〉為題,進行對莊學的批判;到了晚唐李磎著〈廣廢莊論〉,擴充深化王坦之的〈廢莊論〉。二者「反莊」之論,皆是一方面批評莊子思想的謬誤,一方面站在儒家立場,捍衛名教。
儘管王坦之並沒有明確表達出以荀廢莊的字眼,然而綜觀全文與他的其他著作,在荀學脈絡下廢莊仍舊是很合理的詮釋。而另一篇「廢莊」之論,林明照就曾指出,李磎的〈廣廢莊論〉對於莊學之批評主要是依據荀子之說。而本文以為,兩篇結合起來看,可以「考掘」出思想史的特殊現象 :一是莊荀之間的問題,一是儒 林明照:〈詮莊與反莊:李磎〈廣廢莊論〉中的莊學詮釋與批判〉,《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2011 年 9 月,頁 41。傅柯強調:我們不是只有「一」個歷史。傳統史學囿於思維主體、因果邏輯、完整結構等所形成的中心執念,故難以顧及主體、邏輯、結構以外的領域。但這一混沌隱藏的領域其重要性絕不下於傳統「統合歷史」。傅柯是針對史學死角所展開的努力,我們在此不妨借用他的研究視角,重新看待一些思想史上被遺漏的問題。見傅柯(Michel Foucault)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家道統論述的再商榷。
荀子寫〈非十二子〉,維護儒家之正統;然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並未評論莊子,全書只有〈解蔽〉篇中批判「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因此有學者持論,莊、荀之間,其實有相似的地方,甚至認為荀子深受莊子影響。荀子出生於趙,遊學入楚,的確深受道家思想影響, 如老莊談天道自然、虛無、無為而無不為;而荀子也講自然之天、虛壹而靜、無為而治。可以想見荀子自身即在處理儒家和道家之間的問題。然而誠如崔大華所言:「荀子當時似乎沒有察覺,在理論的獨立性與深刻性上,諸子中真正能和儒家匹敵的只有莊子,所以他把莊子思想混同一般,置於諸子之中而加以評論,未能特別地予以考察。」 也就是說,荀子沒有注意到自己與莊子之間「獨特」的問題,但莊荀之辯,卻在後代引起了不小的迴響。像本文就注意到兩篇以「廢莊」為題的著作,實際上正是「以荀廢莊」的代表。這兩篇文章明顯是站在儒家本位的立場下,思考儒家如何在時代前進的新課題。前者於魏晉時代,玄學之風的興盛下,儒家面對以道家為主流的挑戰;後者晚唐時期,佛老思潮盛行,儒者的影響焦慮更深,不得不進行一種學術統整、重建的工夫。
然而必須進一步追問,他們是如何在「尊儒抑道」的氛圍中,直向先秦荀子的?又是如何以荀學資源展開他們的新論述?誠如前文所述,荀子有取莊周之處,然後進行儒家對道家的接納與深化。其中尤以對「自然」的理解最為特殊,如天人、有無、名言等議題,無疑都是對道家思想的回應。而本文以為王坦之是以荀學的「中論」進行儒道會通;李磎則是更進一步地以荀學論證莊子之非,從虛無、天人、性情之學來證成儒家學說。於是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廢莊論〉是以荀學來儒道會通,而〈廣廢莊論〉則是以荀學來否定儒道會通。二者以正反兩面,展現了荀學的淵博,荀、莊之間的地位,以及荀子對傳承儒家譜系的「影響焦慮」 。
再者,道統說的再商榷。韓愈〈原道〉的道統說,影響後世深遠,除了奠定從道不從君的儒家理想外,還為拒斥佛老找到合法的歷史依據。對當時的儒學復興貢獻良多。蘇軾就曾讚譽:「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只是其中並非沒有可議之處。韓愈的道統以孟子為孔子之繼承者,認為:「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說:「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足見其尊孟抑荀的傾向,此後孟荀的地位消長也的確出現明顯轉折。然而熟讀漢魏、晉唐思想史者,皆知荀子思想在當時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韓愈本人也沒有自覺到其人性論、天論受荀學影響深遠,因此,韓愈道統論不能說沒有偏失。如時人李宗閔就說:「『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為不足為。若是則功業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也。可以王而王,可以霸而霸,非人之所能為也,皆此時也。人皆奉時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也,不能由功以反變者也。」(〈隨論上〉);柳宗元說:「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吏商〉)。李宗閔論述王霸功業,反駁孟子認為管仲「不足為」,甚至以時、變批評孟子有泥古之嫌;而柳宗元則認為孟子的理論「緩以疏」,不像孔子「急民」,所以不認同孟子是真正孔子的繼承者。於是從上述可知,李、柳所論皆著眼於社稷現實的需要,他們不只是不同意韓愈的尊孟之說,更多的還是尊荀之傾向。
回到「尊儒抑道」的道統上,原來我們還能看到另一個脈絡:即以荀為尊的思想傳統。不難發現這兩篇「廢莊」之論,皆以荀子為典範來批判莊子,凸顯其思想的主體性。那麼這兩篇相通的內在理路,似乎可以讓我們「察風觀勢」一番,正如劉咸炘對於史學的觀察,不須要去注意只出現過一次的事情,相反地,不只出現過一次的事情,往往能把握住當時的風向。而本文在此借用他的說法,是想提出晉、唐儒家的脈絡,從中看出學術的「風」勢變化。故本文意在指出這兩篇文章,是以儒家荀學為本位進行儒道之辨的。即在當時玄禮雙修、儒道交涉的情況下,他們面對學術範式的折衷與衝突,卻都共同選擇以荀學立場作出回應。這是學界中尚未被人留意的一環,值得多加細說討論。
二、王坦之「廢莊論」:荀學脈絡下辯難莊子,以「中論」調和儒道
王坦之(330-375)為東晉名臣,其著名的文章,莫過於〈廢莊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公謙論〉等數篇。特別是〈廢莊論〉,最為研究者所看重。從歷史可知,當時永嘉之禍,晉室南遷,劉琨、范寧、孫盛、王坦之等士人,皆開始檢討老莊思想,而王坦之處於此風氣之中,正是旗幟鮮明地反莊。他的〈廢莊論〉一開頭引述荀子之言,就透露了以荀子批判莊子的意思。全文俱引如下: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
夫自足者寡,故理懸于羲農;徇教者眾,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暗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逾于不達!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眾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
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莊子謂世間萬事、萬物皆道之所化,由道觀之,莛與楹,厲與西施,雖看似有差異,實則道通為一, 而人也是萬化之一,在道之下同層流轉,因此體道則是任自然。莊子基本認為天下事物各有其本質自然,因任物之自畸而不動,是為齊物;消解形軀的束縛,心知的限定,隨順自然是為逍遙。人不該以己意而強求改變自然,故世間萬事萬物其實並無高下、貴賤、賢愚之別,可見莊子之追求,是一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逍遙境界。於此理論之下,世間萬物之變化,皆不足以為意,人只需「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矣。問題是,王坦之所看到的現實狀況,反而是放蕩虛浮之風氣,人人競相各行其是,放達為非。因此王坦之認為莊生學說,不適用於三代以下,尤其是現下混亂的局勢。更何況多數的人,只是憑藉莊子故弄玄虛,行為不檢,越發浮濫放肆。而世人不明就裡,往往將莊學裡廢棄聖人禮法制度的部分,奉為處事圭臬,導致禮教倫常俱失,社會大亂。無怪乎王坦之認為莊子「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王坦之著眼於當時的現況,來對莊學進行非難,並且用莊子自己的言論來反駁莊子,足見,他有意要對莊學進行全面拆解,雖然在拆解的過程中,對《莊子》的理解不甚全面,有其片面性,但換個角度來看,這片面性卻有其當時現況的合理性。
由此看來,王坦之糾舉莊生之弊的原因,與當時社會背景有關;而另一面則同時顯現出他希望建立「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的社會。而此一理想世界之圖像,則與荀子所追求的禮制世界不謀而合。也因此王坦之屢屢用荀學的觀點去批判莊子。譬如荀子重視人倫教化,將人與天地並列為三才,強調人事努力與人道發揚,言「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但莊子卻講「無以人滅天」故荀子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除此之外,荀子還強調「儒效」,強調儒者「有益於人之國」,能有效回應現實上的問題,能「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故王坦之謂莊學「「利天下也少」、「不足以用天下人」。不難發現,崇儒務實的王坦之,的確肯定荀子學說,並藉此去批判莊子,認為莊子「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
王坦之的立場很清楚,即特重先王之禮教與人文化成的世界,因此在開篇引用荀子、揚雄、何晏的話,去批評莊子,但其實著重點仍是放在第一句話:「蔽於天而不知人」的荀學觀點上。因此認為:「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在他看來,孔子並非沒有能力像莊子一樣,大談天道,只是孔子明白天道遠人道邇的道理,體遠用近,所以才多談人事少談天道。而更重要的是儒家談人事,是緣人情而論,敦禮以崇化,在人倫日用之中,王坦之認為這才是真正的自然,反之莊子所謂的自然,其言詭譎,其義恢誕,背離了當世的人倫世情。因此,王坦之糾舉莊生只識其一不識其二,不懂得「體遠用近」、「德備膺教」。顯然他認為莊子是有體無用的,他繼續說:「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所謂利而不害、為而不爭,甚至「無心」卻又能「應物」,「兼忘」又不忘「動人」,諸如此類的說法,倒也非老莊道家式的柔弱、坐忘與無心,因為在荀子學說中,也有「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直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荀子? 不苟》)等守之以愚、守之以讓、守之以怯的思想。當然不伐、不爭、守之以愚、守之以讓,卻不必說成是道家的原因,其關鍵正在於:不是有沒有謙讓的問題,而是應該在什麼時候謙讓或者不謙讓。因為審時度勢、以義應變,這才是荀子所真正關心的。
正如前所述,王坦之真正在乎的是「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等成功遂事之事。所以才會批判莊子「無用」、「不利天下」。王坦之不離人文意義指涉下的「自然」,顯然是有意對當時道家玄學式的語境進行轉化。也因此,他的儒道會通的主張,則以儒家為主體。於是他提出「格諸中庸」的方式,在儒家荀學基礎上,收攝莊子,呈現體用兼之的狀態。所謂「中庸」,是表現出恰到好處、適中的平衡,因此可以兼顧到不同的,乃至於對立面的事物。「中」的概念,即是能兼容、包容,公平公正,簡言之,即中道思想。那麼「中道」其實也可作為一種「兼術」,即兼顧、相容之術:「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而荀學最核心的價值──禮論,其實也就是以「中」道的精神,「兼」而用之的:「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荀子? 君道》)
於是可知荀子的寬與不僈、辯與不爭、廉而不劌……等講法,更合於王坦之「中庸」論述。因為荀子的中論是實踐性指導,是取兩用中的思維型態,與老莊由言/意、有/無、名/無名式的超越辨證,頗不相同,特別是《莊子》一書,原書好用「至 X」或「至 X 無 X」的語言形式來指稱超越所指對象(X)更高的境界或層次,意即強調在當下的每個層次與經驗之上,有一個更高的境界向度存在。所以王坦之才會說「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那些先賢,雖然有一定的品格節操,但都難免過與不及,而他認為最能體現中庸之道的,是「體遠用近」的孔子。綜上所述,王坦之「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的講法,從方法論上是在看似儒、道觀點的矛盾對立中,採取一不偏不倚的中道路線;而在立場上,則是「在儒」與「非道」。這與何晏、王弼;嵇康、郭象等人以道家為主體,只是拉上儒家旗幟去「會通孔老」的立場大不相同。由此可見王坦之雖然主張「儒道合」,但卻有明顯的「尊儒抑道」傾向。
綜上所論,可知王坦之確實是在荀學脈絡下談廢莊的,其「以荀廢莊」的觀點讓唐代的李磎也注意到了,他說:「余既悟荀卿言,嘉王生之用心,而憐其未盡,故為廣之云。」(〈廣廢莊論〉)即是此意。
三、李磎「以荀廢莊」論:虛無、天人、性情論的建構
李磎為晚唐儒者,藏書甚豐,《舊唐書》記載:「磎自在台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僅百餘卷,經亂悉亡。」在傳世文章中,以〈廣廢莊論〉為人所熟知。而此篇文章,是對東晉王坦之〈廢莊論〉的擴充,他說: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秖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能屈其辭,折其辨,是直詬之而已。莊周複生,肯伏之乎?其終篇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魯衛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知其說詭於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周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云是,是何為不能勝非哉?余甚憎之,或有曲為之說,使兩合於六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元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既悟荀卿言,嘉王生之用心,而憐其未盡,故為廣之云。(〈廣廢莊論〉)
李磎認為儒家之說為是,道家之說為非,一是一非,天下無二道,因此認為王坦之〈廢莊論〉雖然旨意良好,但卻是以儒道會通的方式去批判,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續寫〈廣廢莊論〉。不同於王坦之,李磎所要彰顯的是莊儒之對立,以證成儒學為聖人之學。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既引荀子語,又說「余既悟荀卿言」,可見他看到了王坦之與荀學甚有淵;而李磎自己也採納「以荀廢莊」的主張。林明照就指出,李磎的〈廣廢莊論〉對於莊學之批評主要是依據荀子之說。在林明照的論文中,〈廣廢莊論〉的分析詳盡,他從針對莊子哲學思想的若干主題進行闡論與批評,呈現出李磎與荀學、玄學的關係。而本文採納林明照的意見,但是又另闢蹊徑,以荀學為脈絡考察之。也就是考察李磎的「廢莊」論,是以何種型態的儒學作為思想資源?以及如何以此資源作為一貫的中心思想?本文以為,李磎自有其思想的主體性,因此意在指出,他所涉及到的晚唐儒學議題,其實都有一貫的脈絡存在,而這個脈絡即是荀學。
首先本文以為,李磎對莊子批判性的詮釋,並未深入到莊學之中,而他真正詮釋的其實是荀學。考察〈廣廢莊論〉,他批判莊子虛無、天命、因任、性情的思想,認為莊學邏輯謬誤,不知其本。但這只是一種詮釋策略,因為李磎並不打算去考慮莊子學說中的矛盾有解決或調和的可能,而是凸顯它、強化它。目的是揭示莊學之非,彰顯儒學之正統,然後藉此針對莊子學說,提出虛無、天人、性情的新論述。而此論述,是深受荀學影響的。基於此,本文便從這三個思想主題論述之。首先是他延續魏晉時期的主題─有無之辨。他說:且觀其體虛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夫虛無用之心也,必憑於有者也。有之得行也,必存於虛也。是以有無相資,而後功立。獨貴無賤有,固已疏矣。且所謂無者,特未明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今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此言假四旁之無用也,以自喻其虛。辭則敏矣,然無用之說有三,不可混而同一。有虛無之無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用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者,則老子埏填鑿戶之說,其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於餘也。不可用之無用者,苗之莠粟之秕也。今莊之壞法亂倫,是秕莠之無用矣,而自同於有餘之無用,不亦謬乎?此所謂體虛無而未知虛無之妙也。(〈廣廢莊論〉)
李磎認為「虛無」並非什麼都沒有,而是有無相資。因此認為莊子以「知無用始可言有用」回應惠施是有所偏頗的。因為莊生「貴無賤有」,不懂「虛無」的妙用。從這點來看,李磎的確是延續了魏晉時期對有、無的辯證,只不過他更重視的是「虛無」的用效與功立。所以他接著分析莊子「無用」的意涵,指出「無用」有三層解釋:有虛無之無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用之無用者。然後認為莊子所謂「無用」是「不可用」的無用,是秕莠之無用,壞法亂倫。由此可見,李磎意在批判詮釋莊子的虛無論其實是無用論。固然李磎是從現實事務的立場去批評莊子,認為莊學偏頗並於當世無用;但問題的癥結還在於莊子錯誤理解「無」的意義了。易言之,李磎所理解的「無」,不是玄學家的虛無之意,而是儒家的靜一守本之道。靜一守本是儒道共享之資源,道家不必據為己用。所謂有無相資,也是站在儒家的立場,將「無」解釋為無限的有限之物的總和,是體常盡變無限的「有」。所以「虛無用之心也,必憑於有者也。」就應解釋為儒家荀子的虛靜心,而不是虛無義。這也就說明了,李磎站在儒家荀學的立場,將「無」的話語權挪到儒家脈絡之中。所以儘管李磎在處理的是玄學有無之辨的問題,但其實正與荀子屬於同一理路;而其對於「無」的概念,在荀子那裡也得到充分解釋。
荀子的「虛壹而靜」,有著與道家的清淨、開闊的相同旨趣, 然而荀子並非混同了儒道思想,而是將道家學說吸收調和,納入儒學系統之中,自成一體系。所以儘管「虛壹而靜」看來與道家相似,但卻並不相同。因為對荀子來說,修養工夫的最終目的是在「治」的實踐上。「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荀子? 解蔽》)荀子認為只是可道尚且不夠,還要守道與禁非道;而真正體會道的人,是對道理解得十分清楚,又能去實行的人,所以陳昭瑛認為,對荀子來說「行」才是「心」求「道」的止境。那就表示,荀子的「知道」在於實踐上的智慧,故言:「治之要在於知道」(《荀子? 解蔽》)。
準此而言,我們就能理解何以李磎要強調莊子的「無」為「無用」之論,並將「貴無賤有」,導向「壞法亂倫」了。於是植基於荀子學說上的理解,李磎所期望的「有無相資」,便成為儒術禮制的社會。所以李磎講「且觀其體虛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接著,他批判莊子「研幾於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這部分其實是繼承了荀子批評莊子「蔽於天不知人」,以及他認同荀子「天人相分」的主張。李磎說:
稱屠牛而善刀,牧羊而鞭其後,指窮於為薪,皆在生得納養之和壽矣。故譏滅裂鹵莽者,責衽席之上,設食之間,而不知滅者。然而衛靈公石槨之銘,修短必有天數矣,豈在鞭與不鞭,養與不養哉?其理自乖舛,此所謂研幾於天命乃未及天命之源也。夫因任者,因群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生欲天下而不理。曰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群矣。以為上古至德,同於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而人性得矣。自懸仁義禮樂,而人好知,爭歸於利也。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於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廣廢莊論〉)
李磎以天命論指出莊子思維的矛盾。他稱莊子一方面肯定人得以透過養生延長壽命,另一方面又認為壽命源自於天命,自有定數。而莊子學說的矛盾,來自於莊子沒有注意到天、人之間的區別。所以他批評莊子的「因任」思想。他稱莊子因任思想為人與天地、日月、星辰、樹木、禽獸一樣,都是無知、素樸的存在,而人只應順此本性生活,就可以達到像天地萬物般的和諧有序。所以莊子主張「欲天下而不理」。然而事實卻是,莊子誤解了天地自然之理,更混淆了天人之間的關係。李磎說「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者也。」天、人是有區分的,因此,天命說也應該區分何者為人事可以努力,而何者為自有定數。當然李磎在此不是要窮究天命之數,而是要「不求知天」,也就是將天命的問題,歸還於人的範圍去詮釋。如此一來,李磎完全是以荀子學說為論據,去反駁莊子了。
荀子主張天是自然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論〉)天沒有意志能降下禍端,也不會賜福於人,一切的禍福皆操之於人為。意即人世間的治亂與天無關,而與人的作為有關,故荀子明於「天人之分」。荀子認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是天職;「人有其治」是人事。顯然這是李磎立論之所在,即天地日月為「不假理者」;人則「假理者也」。那麼李磎批評莊子「天命」觀的矛盾,以及指出其「因任」思想的缺陷,皆可說是出自於荀子的「天論」。而以此延伸,在天人關係下「人性」議題,也是李磎所考慮到的,他說:「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於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
李磎認為人的天性就是有欲望,欲望導致索求與爭亂,所以聖人立「仁義」以治之。而莊子則是倒因為果地詮釋為有了仁義之後才開始出現爭亂。故言:
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之心。未為之法,則爭歸於義。先王知其然也,故高為之法訓而峻為之行,而人競學之,亦是爭勝已而爭勝之循道也。猶火之燎上也,因為之灶以煬之,水之趨下也,因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灶焉,火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矣。將壞灶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者失宜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慕矣。不尚賢,殫聖法,削曾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慕所好在於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逆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離其本,而不知好慕之心發於天機。欲絕聖賢,使天下各止其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異於毀溝壞灶,以止水火者乎?其術一何迂!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廣廢莊論〉)
李磎直言人性為性情,並定義其內容為爭上、好勝等充滿了欲望,這就好像火之燎上、水之趨下,若不加以疏導,則會導致災禍。所以人性若不以聖王之道加以疏導,就會暴亂;反之若以聖王之道教化,人之性情必合於理。可見李磎的人性論實與荀子相呼應。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荀子從人生而本有的自然慾望,言人之本性;然後從「順是」的角度,言人之性惡。意指人的自然情欲,在順性過度、無所節制的時候,便會流於惡。又,荀子主張「性」、「偽」有別、「性惡善偽」,即「性」不可學不可事,惟有待「偽」的人為努力,才能化導成善。而對於「性」的化導,則必須倚賴禮義規範,使人循規蹈矩合於善。也因此,荀子特別重視師法禮義的教化,希望人們藉此能「化性起偽」。
值得注意的是,李磎直接稱人性為「性情」,這也看出李磎的洞見。因為荀子可謂儒家中第一個正視情性欲望的人。荀子說:「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正名〉)性是自然生成的,情是性的實際內容,而欲望則是對外界事物有了反應而產生的。荀子雖然給予性情欲分別定義,但三者其實相同,而多以「情性」、「性情」並稱,所以說「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性惡〉)、「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正名〉)。荀子還說:「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正名〉)每個人的欲望多寡不一樣,但欲望確實是人的本性,這跟治或亂無關。顯然地,中晚唐儒者對於人性論的定義,契近於荀學而遠於孟。譬如柳宗元說:「孟子好道而無情」(〈吏商〉)、杜牧說:「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眾,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三子言性辯〉)二者皆肯認人的自然情性,並在人性的論述上肯定荀子。其中杜牧分析得更為細緻,有所謂的七情者,而愛、怒之情是人性之本,也是性惡之端。不過儘管人性有惡之傾向,但卻因為「世有禮法」,所以不妨礙成善的可能。這點與李磎認為人的天性欲望導致暴亂,而必須以仁義禮樂治之的主張,如出一轍。由此可見,中晚唐儒學的性情論,的確以荀學為宗。
綜上所論,李磎以荀學辯莊,「屈其辭,折其辨」,圍繞三個主題:虛無、天人、性情,證成了其尊儒抑道的思想。並由此呼應中唐以來儒學的發展,呈現出異於韓愈道統論的尊孟立場。
四、結論:「廢莊」論在思想史上的意義
從歷史上的兩篇「廢莊」論來看,可知士人在崇尚「自然」的虛無之風下,會更加強調一個規範的世界、重禮的社會,因此可以合理推論,當時需要借重荀學,以求撥亂反正,重建社會秩序。故王坦之以荀學的中道論進行儒道會通;李磎則更進一步地以荀學論證莊子之非,從虛無、天人、性情之學證成儒家道統。由此看來,同題之「廢莊」著作,不只「廢」道,還要「立」儒。在思想史上,呼應晉、唐以來儒學的發展,呈現出異於韓愈道統論的尊孟立場。
這兩篇文章若以儒道會通的思想來看,其理論的深刻度雖難以與王弼、郭象等人相符;但若放在荀學史脈絡下去考察,卻可看出二者對荀學的繼承與發展,其實頗為關鍵。也就是說藉由這兩篇文章,看王坦之、李磎是如何以荀學為資源展開他們「尊儒抑道」的新論述。像王坦之欲證明名教出於自然,但這個「自然」,卻不是當時玄風下的「自然」義,而是儒家荀學具有人文經驗的意涵。所謂利而不害、為而不爭,甚至「無心」卻又能「應物」,「兼忘」又不忘「動人」,諸如此類的說法,倒也非老莊道家式的柔弱、坐忘與無心,而是「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直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荀子? 不苟》)等審時度勢,以義應變的思想。又,他講「格諸中庸」來會通儒道,其實也正是以荀學「執兩用中」的方式調和儒道,而有別於郭象的「寄言出意」。所以其「中道」之論,不是要求抽象先驗、預設的道理,而是透過踐禮,在現實人生中取得一個合情合理的安排。也因此,王坦之說:「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
接著李磎深化王坦之〈廢莊論〉,著〈廣廢莊論〉。以荀卿「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揭開儒道之間沒有調和的可能,必須嚴別儒、道。所以他批判莊子「觀其體虛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研幾於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而他提出虛無、天人、性情的論述顯然是深受荀學影響。所謂「無」,不是玄學家的虛無之意,而是儒家荀學的「虛靜」。意即將「無」解釋為無限的有限之物的總和,是體常盡變無限的「有」。原因正在於,李磎的關懷在於「治」,所以稱莊子的「無」為「無用」之論,並將其「貴無賤有」的思想,導向「壞法亂倫」。可以想見李磎所期望的是一儒術禮制的社會。因而他繼續批評莊子「蔽於天不知人」,強調「天人相分」;又定義人性為「性情」,應以聖王之道教化,使人之性情合於理。都可說是同一理路──與荀子學說若合一契。那麼我們可以說,李磎對莊子批判性的詮釋,並未深入到莊學之中;而他真正詮釋的其實是荀學。
不難發現李磎談論到的天人關係、性情論,也是當時唐代儒者所共同關心的議題。正如馬積高所言,在唐代後期,荀學閃耀著光彩,特別是天人相分說得到了空前的闡揚。而本文以為人性論也是如此,在唐代後期,儒家性情學說得到推進與發展,皆可上溯自荀子。職是之故,荀子「蔽於天不知人」所涉及到的天、人論述,就會是儒者在「尊儒抑道」思想上的共同資源。其實,早在先秦時期,荀子就已經在處理儒道會通的問題了,諸如「自然」所涉及到的天人、虛靜、性情等主題思想,無疑都是對道家的回應。只不過在學術思想史上的流衍,莊荀之間卻越走越遠,就像〈廣廢莊論〉所拉開的差距:莊、荀之間「尖銳化」走向了對立面──從同中有異,到去同存異。這可以說是「尊儒抑道」的一個結果,也是後世儒者的選擇。
於是在「尊儒抑道」上,原來我們還能看到另一個脈絡:即以荀為尊的思想傳統。不難發現這兩篇「廢莊」之論,皆以荀子學說為典範來批判莊子,也就是說,荀學在晉、唐「尊儒抑道」的思想中,其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於此,我們應該重新省思以「孟學」為依歸的單一道統論述。如同傅柯所強調的:我們不是只有「一」個歷史。傅柯認為傳統史學囿於思維主體、因果邏輯、完整結構等所形成的中心執念,故難以顧及主體、邏輯、結構以外的領域。儘管傅柯是針對史學死角所展開的努力,而在此不妨借用他的研究視角,進入到魏晉、唐代這一段時期,考掘出荀學的影響。
荀子劝学, 荀子, 荀子简介,荀子修身,劝学荀子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以荀辯莊 ──〈廢莊論〉與〈廣廢莊論〉的「尊儒抑道」說发布于2023-03-19 21:2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