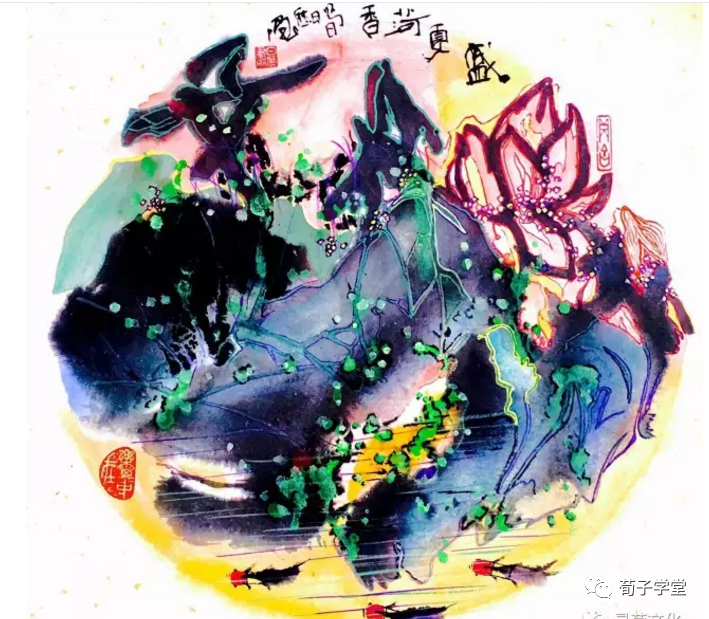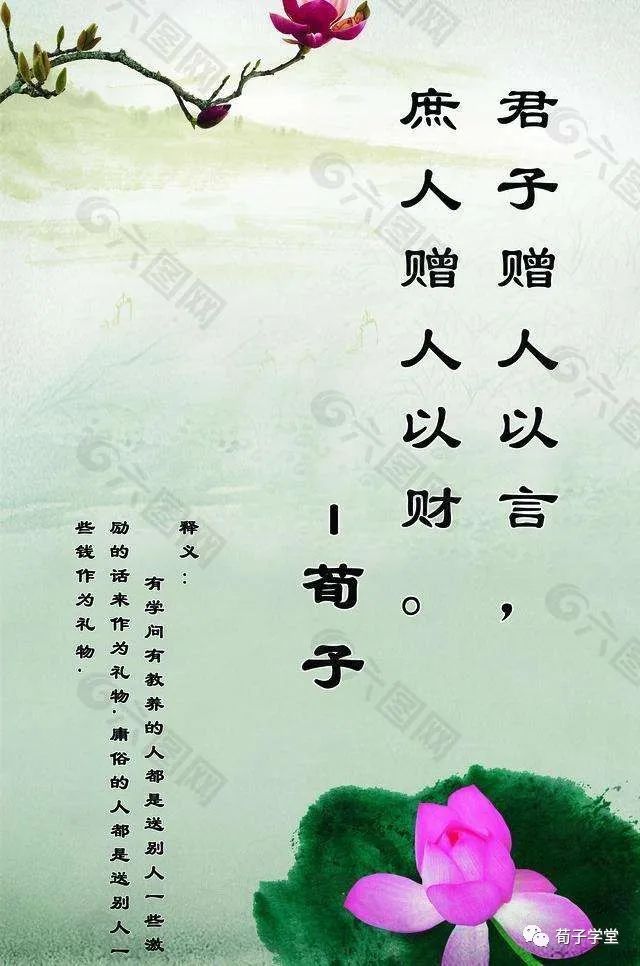摘 要:晚近以来,“性朴论”以及《性恶》晚出的观点,使得《性恶》以及荀子“性论”成为了研究热点。然而,这两种具有紧密内在关联的看法,并不能使荀子“性论”的涵义以及相应的荀子思想体系得到完整展现。因此,借用“性朴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性恶》整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从开篇到“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作为总括,文本说明了由“性伪”达成“治”的主线;其后至“岂其性异矣哉”的第二部分,文本通过两段“孟子曰”与“问者曰”的对话形式,展示了孟荀对“性”理解上的具体差异,并引出荀子思想中“性”与“礼义”的联系;而从“涂之人可以为禹”至篇末的第三部分,文本不仅展示出荀子思想中“性”的确切涵义,而且还通过阐述以人之“性”如何达成“治”的径路,明确描绘出荀子思想的整体理论框架。实际上,基于以上整体理论框架的呈现,不仅“性恶论”、“性善论”、“性朴论”三者间的纠葛得到了说明;《性恶》的作者以及与《荀子》的关系,也得到了有效地回应。
关键词:“性朴论”;荀子“性论”;“质”;“具”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 :方达(1987—),男,浙江浦江人,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先秦诸子哲学及思想史。
“性论”成为荀学研究中的重点问题,无疑源自理学家对荀子“性恶论”的认定。众所周知,理学家那里的“天理”世界所对应的全部秩序结构,都是以“性善”的内在规定作为理论基石。因此,在如此一个由先天到后天,由内而外的理论架构中,“性善论”无疑成为了唯一不可动摇的基石。相应的,以这样的立场来审视《荀子·性恶》这一“专题论述”,自然会对“性恶论”得出全盘否定的结论。然而,也正如程颐“荀子极偏颇,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所示,理学家是基于自身的立场,直接把《荀子·性恶》等同于“性恶论”。换句话说,理学家不仅把《性恶》从荀子整体思想中独立出来看待,甚至都没有对《性恶》的文本进行过精细的揣摩。也正因此,当近代传统心性之学式微后,基于对《性恶》与《荀子》整体文本的细致考察,以及对西汉“性论”相关材料的爬梳,“性朴论”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虽然“性朴论”在文献材料上有诸多证据,却也存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基于此的荀子整体思想只能呈现为一种综合性的特征,而无法呈现为严谨的体系化架构。这一缺憾既因为无法与孟子的理论系统相诘辩,而在价值判断上降低了荀子的历史地位;更因为不符合先秦儒家那种内在德行养成与外在政治治理相统一的内在脉络,而无法为荀子作为先秦时纯正“大儒”来正名。不过,如果借用“性朴论”的研究方法作更为深入的考察,《性恶》实际上以对“性善”的深入诘辩,对应为一种清晰的文本论说结构,并由此展示出荀子整体思想的理论架构。换句话说,如果不仅仅拘泥于《性恶》是否为荀子本人所作,而是把《荀子》一书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体系来看待,那么不仅《性恶》与“性朴论”的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说明,“性朴论”的上述缺憾也得到了完美的弥补。
一、“性朴论”与《性恶》文本结构的重审
“性朴说”的出现,由晚近以来通过对《性恶》的作者产生怀疑而逐渐演变而成。从辨伪的动机来看,这种作法源自于荀子思想自两宋以来遭受到的长期贬抑。从辨伪的目的来看,相关论述无疑通过证明“性恶论”并非荀子本人所持有,而为荀子作为儒家正统正名。因此,在这两种合力的影响下,“性朴说”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仍旧将“性恶论”与荀子自身思想相区隔,不认为荀子本人会得出“性恶”的单一结论;二是为了证成前者,“性朴论”的相关学者对《性恶》及相关文献作出了大量的文本考证。虽然后者所提供的文本证据具有不小的说服力,但始终无法解决荀子基于“性论”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与前述先秦儒家基本脉络如何统一的追问。因此,借用“性朴论”审查《性恶》时所取得的各种成果,在将《性恶》与《荀子》作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思想整体前提下,《性恶》的文本结构可以得到重新的划分。
关于近代以来对《性恶》以及“性恶论”进行辨伪的状况,林桂榛总结道,“系统提出《性恶》篇为后荀子者所作的……乃 1923 年刘念亲”,“蔡元培 1894 年又谓‘性恶’说非荀子所有及《性恶》为后荀子所作”,“1896 年更言高步瀛著书谓荀子以天生自然、本始材朴等言性恰证明‘性恶之诬不攻自破’及‘性恶论非荀子所作’”,“后梁启超等也认为荀子未必持性恶论,1950 年代日本学者金谷治、丰岛睦等认为《性恶》非荀子作品”。由此不难看出,对荀子“性论”的重新勘定从一开始便采用了对《性恶》进行辨伪的方式。在这一基础上,“性朴论”又根据《荀子》文本的相关内容,提出荀子本人认为“性”其实是“天生自然、本始材朴”。在证成上述两点结论的过程中,众人所采用的方法基本相同:首先从文献互见的角度入手,认为在刘向编定今本《荀子》之前,诸如韩非、李斯,以及张苍、贾谊等与荀子具有师承关系的人,从未提起过“性恶”,并由此认定《性恶》有汉成帝时期伪作或者相应讹写的可能性;其后又从《荀子》文本出发,认为荀子“性论”或是“性朴”,或是“性不善”。这种文献辨伪的方式看似稳妥,却也始终存有一个疑问:如果《性恶》伪作或者讹写的迹象如此明显,刘向在编定今本《荀子》时,为何仍将其作为重要的“专题论述”收入。事实上,“性朴论”论述的实质都是从此处入手,试图通过说明“性朴”与“性恶”的关系这一方式,来给《性恶》的作者一明确论定。
具体而言,“性朴论”所对应的伪作与讹写这两种结论,都无外乎意图从“性论”的角度给予荀子整体思想架构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从各自的论证过程中来看,二者显然都各有利弊:“伪作”无疑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文献依据,但与此同时,由于将《性恶》排除出《荀子》的整体,因此显然在研判荀子思想的整体性上有所欠缺;而“讹写”虽然给《荀子》文本提供了整体的理论性,却又无法有效地解决文本上“性朴”与“性恶”的显著差异。不过随着两种观点论述的深入,上述工作逐渐从单纯的辨伪工作转向了对《性恶》的整体考察,亦即从文本的整体性层面上对荀子的“性论”作出考察。换句话说,如果将《荀子》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进行考察,也许会对研判荀子的“性论”提供莫大的帮助。在这种考察中,周炽成先生对《性恶》文本结构的划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按其所述,《性恶》可划分为七个不同意义模块:
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安恣雎,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主题为“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
二、“涂之人可以为禹……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主题为“为何涂之人可以为禹”;
三、“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其不可以相为明矣”,主题为“可以为圣人,不等于可能为圣人”;
四、“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唯贤者为不然”,主题为“人情不美”;五、“有圣人之知者……是役夫之知也”,主题为“四种知”;
六、“有上勇者……是下勇也”,主题为“三种勇”;
七、“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靡而已矣”,主题为“性质美,需磨炼”。
不难看出,周炽成先生出于对《性恶》辨伪的目的,将与“性恶”直接相关的文字归为一类,将剩余文字归结为六大主题。
这种划分一方面将《性恶》中各个主要板块标注清楚,但另一方面由于既有的划分立场与目的,实际上遮蔽了几大板块之间应有的联系与结构。首先,第一板块虽然在内容上确实与“性恶”直接相关,但这些相对于“性善”进行诘辩的文字之间有何关联,又如何具体展开,显然通过归纳的主题并无法有效地回答。其次,剩余的六个板块虽然看似各有主题,但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如果参照着前文的“性恶论”相关文字,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单纯地对相关概念进行叙述,而是涉及了人在现实中如何进行实践活动的具体方法。换句话说,剩下的这六个板块因为具有明显的内在关联,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同一个主题。因此,如果不站在周炽成先生行文的立场上来看,反而站在“性恶论”与荀子整体思想结构的关系上看,《性恶》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三大板块。其中,从开篇到“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为第一版块,其后至“岂其性异矣哉”为第二板块,从“涂之人可以为禹”至篇末为第三板块。
第一板块主要基于荀子的整体思想架构,阐明由“性伪”达成“治”的全文主线,并由此初步呈现出这一过程中“性”、“伪”、“治”的相应内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文本首先明确说明了“性”、“善”、“伪”之间的关系:“性”与“善”之间需要通过“伪”这样的实践活动达成联结。而后文三个“顺是”所对应的“欲”,以及“从人之性,顺人之情”的“性”与“情”,显然都属于“性恶”这一应该接受“伪”的对象内容。其后,“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一方面说明“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是“伪”的内容,一方面又说明所谓的“善”就应该是“治”,并包括了“辞让”与“文理”。最后,文本用两个“用此观之”分别再次明确了“性”、“伪”、“善”的联结过程,以及“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基本观点。再进一步,文本在论述“性恶”的特征时,除了前文所呈现的“欲”、“情”两项内容外,还以“枸木”与“钝金”作为比附。如果说“欲”与“情”还因为有悖于“辞让”、“忠信”等“礼义文理”的内容,而显示出相应的实践价值判断,那“枸木”、“钝金”与所相对的“檃栝”、“砻”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实践行为中所具备的相应客观资质,亦即“性朴论”所指向的实际内容。换句话说,此处的“性”似乎除了对应为一种价值意义的根据以外,还呈现为一种客观的实践资质。而至于这两者的具体内容以及相互关联,显然正是后文论述的重点。与此同时,“伪”的内容除了前文所述,此处显然还与“古者圣王”以及“法度”有所关联。
由此不难看出,《性恶》的第一板块并不仅仅在于阐明“性恶”,而在于说明由“性”如何通过“伪”而达成“治”。事实上,后文的两个板块正是通过对“性善”的诘问,分别详细呈现出“性”的内容,以及“伪”的全部过程,并由此说明“治”的内容分别对应为“仁义”与“法正”的个人修为与政治治理的两个层面。同时,以上所涉及的所有概念以及相应的联结过程,又恰是荀子整体思想的理论体系。因此,由“性朴论”所带来的启示出发,《性恶》的文本结构得到了初步的揭示,并相应地展示出荀子思想的架构。显然,在这一架构中,“性朴论”的内容也作为一部分的构件发挥了更深层次意义的作用。
二、荀子之“性”的几种理解向度:以诘辩“性善”的方式展开
既然“性朴论”可以作为荀子之“性”的一个向度,那么对《性恶》中所谓的“人之性恶”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表述自身全部涵义的追问,便不仅衡量了“性朴论”的得当与否,更呈现出理解荀子之“性”的其他向度。
而对这一追问的解答,显然可以随着文本对孟子“性善论”的诘辩而逐渐得到展开。从整体来看,《性恶》文本的第二大板块对应为两大部分,分别都是采用“孟子曰……孟子曰……问者曰”的形式,通过对孟子之“性”的批驳,来展示荀子之“性”的涵义,并通过与“问者”的自问自答来明确“性”与“伪”联结的必要性。其中,第一部分主要说明“性”、“伪”在个人修为层面上联结的方式与必要性,而第二部分则针对的是政治治理的层面。
首先来看第一部分的文本,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今之学者,其性善”所指代的是“学”的形式与目的为何的问题。杨倞注此句“孟子言人之有学,适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矫也” ,按其所注,孟子之“学”目的在于发明“天性”中的“善”,但是形式又不是现实的外在客观行动(“非矫也”)。这也就是说,在杨倞看来,孟子之“学”只不过是“天性之善”显现于外的一种形式而已,故而“学”的目的与形式是合二为一的。再看《性恶》作者自己的反驳,“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作者认为,孟子在混淆“性”之涵义的同时,还误解了“学”的形式与目的。在其看来,“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性”是“天就”的,并不能成为“学”与“事”的目标,反而“礼义”才是“学”与“事”的目标所在。与此同时,“学”又因为在形式上与“事”相同,故而等同于一种客观的行为活动。有鉴于此,《性恶》作者认为,“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这便是说,作者在界定“性”的内涵时,还明确了“学”的形式与作用,即定位于一种现实的行为活动。
在“性”的内容层面上又进一步,后文引述“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实际上是为了继续厘清荀子与孟子在“性”概念理解上的差异。杨倞注曰:“孟子言失丧本性,故恶也。” 从对现实情境中“恶”出现的源头追问入手,孟子认为“恶”源自于对“本性”的“失丧”,“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这便是说孟子之“性”不仅仅是“人”内在的特质,而且“性善”所对应的的“朴”与“资”还可以不经过实实在在的行为,直接体现为外在社会的“美”与“利”。而这便与前一句“今之学者,其性善”意义相同,都在肯定“性”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全部意义规定的同时,否定了外在的客观显现过程与相应的实践形式。对此,《性恶》作者为了区分孟荀在“性论”上的差别,亦即丰富荀子“性论”中现实实践活动的这一部分内容,引入了由“欲”而引发的“情性”,“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并通过与“礼义”内容的相互联结,说明符合“礼义”的行为是基于“性”的内容,依靠后天“伪”的现实行为而达成。
在暂且不引入“礼义”内容的前提下,上述一部分的论述显然旨在阐明,由人之“性”如何实现现实的“辞让”这一品德。由此递进,第二部分文本中的两段“孟子曰”更是将讨论的对象,从内在的个人修为扩展到了外在的政治治理。
孟子曰:“人之性善。” 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 “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檃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从孟子“人之性善”这一综合判断入手,《性恶》文本开始对这一观点进行整体的批驳,“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作者首先对“善”进行了定义,认为“善”不仅仅是“人”内在情感的“正”与“理”,而且还体现为外在社会的“平”与“治”。与此相应,“恶”也必须区分为内在的“偏”与“险”与外在的“悖”与“乱”。因此,如果像孟子一般承认“人之性固正理平治”,即“性”本身成为了个人与社会秩序的保障,那就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从初始状态就是“善”的,后天的所有活动便失去了存有的意义。再进一步,即便真如孟子所说,“性”本身可以保障情感与社会秩序的“善”,但若当真遇到外在社会“恶”的情况,即现实情况已经跳脱出“性善”的范畴时,“性”又能作出何种有效的应对呢?而这也正是《性恶》作者的最大隐忧,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性恶》)在《性恶》的作者看来,如果漠视外在客观实践活动与政治治理的行为,“天下民人”将陷入完全的无序状态。而这显然不仅仅是理论推演会得出的必然结果,更是战国时人所面对的现实境况。
故而,从本质上看,《性恶》篇中所归结出的孟子“性善说”,不仅意味着“圣王”与“礼义”丧失了意义,而且还直接无视了“人”在秩序体系中的行动能力。由此,在结果上必将会直接导致“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的现实状态。反过来说,站在维护孟子“性善”的立场上看,即便承认了孟子“性善”中所包涵的“人”之内在的“善”与“平等”,那面对外在实存的强弱、众寡之分又该如何解决。当然,这并不是说荀学从根本上认同战国时流行的法术制度,并以此否认人内在价值根源的意义。正如《荀子》通篇所展现的,荀子的理论体系旨在现实的整体秩序层面上,给“人”提供了共同实践的空间:基于共同的实践意义源头,人可以通过后天的现实实践行为,以及相应的能力来应对不同的现实情境,并体现出相应的结果。而这一点恰是孟子本身“性论”的最大不足:基本忽视了后天实践行为的重要性,而这一缺陷直到宋明理学时才以“功夫论”形式逐渐得到充实。也正是有鉴于此,第二部分对后一个“孟子曰”的批驳最后落实在其说“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之上,亦即前文所总结的,孟子的“性论”在理论上失去了现实的“辨合符验”,在方法上漠视了“可设”与“施行”的客观行为,由此“性善”必然终将导致“去圣王,息礼义”的窘境
由以上对孟子“性善”批判的展开过程不难看出,对荀子之“性”的理解需要放在“人”、“性”、“善”、恶”之间如何达成有效的联结方式这一脉络中进行。概括而言,孟子之“性善”作为“人”的本质性规定,虽然给予“人”具有道德的意义规定,却并未提供“人”的生理资质规定,同时也未提供“社会”制度的内在意义规定,而后两者的缺失正是造成“人”在客观行为层面完全丧失实践能力可能性的直接根源。因此,荀子之“性”正是在以上诸方面中体现出了自身的涵义:首先,“性”并不是个人修为与政治治理有序性的内在保障;相反,“性”只作为上述有序性由内而外得到实现时,“人”所具备的基本实践资质。换句话说,荀子之“性”在被剥离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内在意义根据的前提下,一方面作为“人”达成上述目的的实践资质而凸显自身的内涵,更重要的在于为现实的实践活动保留了空间,并由此彰显自身的全部意义。
三、荀子“性论”自洽性的追问:以“问者曰”的方式展开
荀子之“性”虽然在与孟子“性善”的辩驳过程中得到了内涵上的理解,但仍然面临着理论自洽性的追问。
《性恶》文本当然可以攻击孟子“性善”在现实实践行为上的缺失,并由此提出荀子“性论”的丰富,但又如何来解决所有实践行为意义的根源问题呢?按照文本所述,“礼义”不仅是荀子之“性”保有理论自洽性的关键所在,更决定了荀子能否在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上超越孟子。然而,“礼义”由何而来?如果“人性恶”得到肯定,是否意谓着还有比“性”更为本质的意义规定?如果“礼义”是“圣人生之”,是否意味着出于圣人之“性”,以及由此出现的“圣人之性”与“人之性”之区分?对以上问题的解答,《性恶》文本的第二板块以“问者曰”的形式逐一展开。
如上所述,第二板块的文本在诘辩孟子“性善论”时,最致命的武器便是将“人”的内在修为与外在治理之根本意义规定,从“性”的内涵中剥离出去,使得“人”并非根据“性”而彰显自身的全部价值,并由此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实践领域。而也正是在论辩的过程中,“礼义”作为“人”的内在意义规定被相应地明确提出。然而文本一开始只说,“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明确了“礼义”才是人应该“学”和“事”的对象,并没有论证何谓“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亦即“礼义”的内容与自身根据。为了集中回应这一疑问,文本在前两个“孟子曰”的后面,以“问者曰”的自问自答形式进行了初步的阐明,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生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文本以“性善论”的口吻发起追问,“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如果“性”较之“礼义”充当着更为本质的内在规定时,“恶”的“人之性”如何能必然导向“善”的“礼义”?针对这个质问,《性恶》的作者仍然在“性”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进行回应,“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亦即“性”只是对“人”生理本质的规定,根本不可能具有意义的规定。因此,“礼义”只能来自于其他的源头,并相应的对人形成意义规定。而这正是“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表面上所要表达的内容:“礼义”的源头出于“圣人”之“伪”,而非出自“人之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生于圣人之伪”并非指的是“礼义”的真正源头,而只是表明了“礼义”与“成圣”的联结方式,亦即“伪”的重要性。对这一点的直接佐证正是后文“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很明显,《性恶》作者在此处将“礼义”对应为“器”,而“器”正是外在的现实之物。这也就是说,“礼义”于外在经验层面的呈现是以“人之伪”作为前提,而不是直接基于“人之性”。由此再进一步,“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所对应的行为次序也表明“礼义”与“法度”是“积思虑”与“习伪故”的结果,而非前提。换句话说,此处看似代表价值源头的“礼义”实际上应当作为现实秩序状态的“礼”来理解。而正是在这种“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联结的过程中,“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的观点被明确提出,即“圣”与“众”在“性”的层面上是完全相同的,二者的区隔完全由“伪”的程度作为标准得到判定。因而,后文才能从“性”的角度总结道,“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生而已,则悖乱在己”,“性”与“礼义”在原初意义上是互不干涉也毫不相同的两者,人“生而已”的只有“无礼义”、“不知礼义”的“性”,且这种“性”又必然导向“悖乱”;而至于“善”,只能通过人基于“性”的内容,对“礼义”的“强学而求”与“思虑而求”这一“伪”的行为方式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也正是上述引文段末所说“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的内在论证逻辑。
虽然上述论证再次严格区分了“礼义”与“性”在涵义上的不同,但不能否认的是,“礼义”源头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正面解答。因此,对“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的曲解与追问就会自然而然地随之产生,而这实际意味着“性善”论者对“性恶说”的反击,即通过 “圣人之性”与“众人之性”的区分来达到推翻“性恶说”的目的。正如前文所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确实会带来礼义”是由“圣人”通过“伪”而制作出来的误解,由此“性善”论者便会发问,“圣人”与“众人”的本质区分到底为何?既然只有“性”与“礼义”两种标准,你又说“礼义”后于“圣人”,那是否意味着“圣人”有“圣人之性”,“众人”有“众人之性”,如若“性”果真有两种区分方式,那是否进一步意味着,即便“性善”不能成立,“性恶”又从何而谈?对此,文本以第二个“问者曰”再次进行回应,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斫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雎,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雎,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仍旧以“器”、“性”作为比喻,“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斫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礼义”作为“器”与“人之本性”并不具有一致性,只是通过特定的实践方式而得到完成与呈现。由此,文本继续强调“性”的涵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在反驳存有“圣人之性”与“人之性”的不同区分时,再次强调对“礼义”践行的重要性。由以上种种不难看出,第二板块中的两处“问者曰”都旨在在于进一步分离“性善论”中,作为人之为人意义的本质规定的“性”,确立“性恶论”中“性”只具备“人”实践资质的规定意义。当然,与此同时也不可回避,本质意义规定的问题在此处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答,而这似乎也可以成为“性朴论”辨别《性恶》是否存有后出可能性的论据之一。虽然《性恶》本身存有上述的部分缺陷,但却从侧面反映出荀子“性论”所处的基本框架:“人”实践行为的意义规定在于“礼义”,“性”只提供“人”与“礼义”联结的实践资质条件,而“礼义”与“礼”的现实呈现则必须依赖于“人”对“性”主动行为——“伪”。由此观之,《儒效》篇所载: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正是对这一实践过程的细致描摹。用荀子自己的话来说,“闻”、“见”、“知”、“行”是“明之为圣人”的必要路径,“仁义”是“成圣”过程中需要始终秉持的价值原则,而“性”与“情”正是这一过程中需要通过“注错”来加以改造的人自身具备的资质,当完成过程中的所有环节,便可以达到“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的境界 。质言之,荀子之“性”确实是“众人”到“圣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资质规定,也是“成圣”过程展开的起始点,但其本身并不承担人之为人的意义规定这一作用。正是基于以上的观点,荀子在此处文本中初步点明了“性”与“情”的具体特质,“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而这也正为阐明荀子“性”的真实内涵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四、“质”与“具”:荀子之“性”的确切涵义及相应理论体系
如果说第二板块的内容,还是就荀子之“性”的内涵以及相应的理论自洽性进行辨明,那第三板块的内容就是对上述论证在现实中展开的过程进行的具体描述。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描述的过程中,《性恶》不仅通过与其他篇章的互见,呈现出荀子之“性”的确切内涵,以及具体的“涂人成圣”的实践路径;更通过对这一实践路径的阐明,解决了“礼义”来源的根本性问题。
从内容上看,上文所引述《儒效》的内容,以及有关“师法”的部分一直至篇末的文字,正好与《性恶》篇剩余部分内容高度吻合。大致而言,《性恶》“涂之人可以为禹”至“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一段可视为对《儒效》“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以及“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的展开论述,旨在说明由“涂人”到“圣人”的过程以及所需凭籍;《性恶》“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至“参于天地矣”一段对应《儒效》“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旨在说明实践过程的专一程度与至高“神明”境界的关联;《性恶》“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至“其不可以相为明矣”一段对应《儒效》“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至“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旨在说明“成圣”过程中所有环节的重要性,突出“涂人”主观能动的重要性;《性恶》“尧问于舜曰”至“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是对《儒效》“知”、“勇”、“能”、“察”、“辩”的展开,旨在说“成圣”过程中的几种进阶境界;《性恶》“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至篇末对应《儒效》“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旨在说明“师法”在改造“性”、“情”而“成圣”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因此,在厘清荀子“性论”所处的整体结构,以及“涂人成圣”这一过程的全貌后不难发现,《性恶》篇所论之“性”的具体内涵,正是“涂人”在“知”与“行”过程中,所必备的“知仁义法正之质”与“能仁义法正之具”两种基本资质。然而,“人”在实践行为中的“质”与“具”具体指代什么呢?在谈到“知”何以可能时,《正名》篇如是说:
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形体、色、理以目异,声 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
很明显,荀子认为“人”的认知过程是由“天官之当簿其类”开始到“心有征知”完成,即“目”、“耳”、“口”、“鼻”、“形”感知外在事物开始,“心”作出相应判断结束。而在这一过程中,“五官”无疑成为了最基本的必备条件。因此,“五官”作为认知的保障,毫无疑问成为了“知仁义法正之质”的内容。反倒是对“具”的勘查会遇到一些疑问,按照《性恶》篇所说,“质”与“具”是作为“伪”的资质而普遍存在于“涂人”身上的,而《正名》又载: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这就说明“性”、“情”、“心虑”是构成“伪”的不可更改的环节,故而“具”就有“情”与“心虑”两种可能。但也正如此段文字所示,“心虑”所施加作用的对象是“性”与“情”两个方面,其自身并不作为最基础的资质保障。此外,《解蔽》又详细阐释了“心”在认知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情”就应当是“具”的实际内容 。
相比于“五官”作为“质”的明确性,“情”所对应的“具”是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呢?“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天论》),按照荀子的说法,“情”与“五官”都是由“天”所创立并赋予给“人”的,由“五官”的具备到藏于其中的“好恶、喜怒、哀乐”本身就已经是先天完成了的生理结构 。只不过,荀子此处并没有说明“天情”为何能成为“能仁义法正之具”,而是将答案留在了《荣辱》中,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首先在“情”的性质层面上,荀子明确将“欲”与“五官”的感知能力列为“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说明“天情”的“好恶、喜怒、哀乐”实际上就是由“欲”所引发的。其后从“欲”的产生角度看,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王霸》)“欲”自身出于“感官”接受外界相应刺激材料的需求,是“必不免也”的结果。由此可知,“五官”不仅是“情”的载体,而且在基本资质这个意义上的“情”与“五官”一样,并不需要接受后天的改造,故而此时“情欲”还不能称之为严格的“能仁义法正之具”。
但进一步从“欲”自身活动的角度看,其又必然具备着“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馀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的特点(《荣辱》),而恰恰是“不知不足”这一在时间意义上具有持续性的特质对应了“人”实践行为的意义规定中,“群”所对应的内在张力这一特点 。如此,“涂人成圣”过程中的重要资质“能仁义法正之具”与“人”实践行为的意义根据之间的关联便显得十分清楚:“涂人”的实践行为的意义根据在于“群”,而实践的动力所对应的内在张力,则实际上来源于自身“欲”的“不知不足”。与此同时,由“官能之质”与“情欲之具”所组成的“性”,又是“涂人”后天自己“成圣”过程中实现实践意义的资质 。换句话说,从现实的实践过程来看,“性”中所包含的“欲”才是“涂人成圣”与“治”的重要环节,故而荀子对“欲”与“治”的关系着重强调道: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
在荀子看来,“欲”本身是先天赋予在人身之上的,“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性标准,也是“人”是否能称之为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人”的标准,而并不是直接呈现现实“治乱”的决定性因素。反而,真正导向“治乱”的是“心之所可”,“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荀子明确了“性”、“情”、“欲”之间的详细关联,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正名》)质言之,“情欲”只作为一种高于“五官”这种“知仁义法正之质”的“成圣”资质而彰显意义,但本身并不意味着能否直接导向“成圣”。相应地,“官能之质”成为了“人”可以“认知”的资质,而“情欲之具”承担了“人”可以“实践”自身意义的资质。故而,当二者统一在一起后,便着实成为了“成圣”的基石。
综上所述,荀子的“性论”本身并非直接而单纯地讨论“善”与“恶”的问题,反而只是作为“涂人成圣”的一个重要环节出现,而“成圣”的指向便是实现现实的“仁义”与“法正”这一“治”的内容。由此,在实践过程中所必备的“知”与“行”资质的意义,才是荀子“性论”的真实原义。概括来说,从“性”的构成层面看,“五官”所对应的“认知之质”与“天情”所对应的“情欲之具”是荀子之“性”的特定组成部分,二者在初生的意义上是普遍存在于“涂人”身上的,即所谓“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荣辱》)。同时,“认知之质”因为不带有任何的意义指向,符合了“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论断 ,并由此成为当下“性朴论”观点的依据。但当“性”中的“情欲之具”自身在实践序列中开始发生作用时,“涂人成圣”的过程也就相应展开。同时,也正因为“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荣辱》)的可塑造性,后天的“注错”之“伪”便开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一过程用荀子的话来概括便是“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礼论》)。质言之,“性”在荀子“性论”中作为达成最终“治”的资质固然重要,但并不以其由于“欲”的作用而所带有的“恶”为主要内容 。或者说,相较于孟子之“性”在偏重指向个人修为成圣的同时,而缺乏了在现实社会治理层面上的操作空间;荀子之“性”从一开始便兼具了上述两个层面的实践领域。也正因此,不能仅仅以个人修为层面的“善”与“恶”来评判荀子之“性”的内涵。此外,无论是从《性恶》文本在对“礼义”源头论证时的缺失,还是最后一个版块对《儒效》内容的大篇幅借用,似乎都可以说明《性恶》有后出的可能性。当然,即便果真如此,《性恶》显然还是能够深刻地把握到荀子本人思想的精髓,并由此成为荀子整体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许也正因此,刘向才会将其编入今本《荀子》之中。
荀子劝学, 荀子, 荀子简介,荀子修身,劝学荀子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性恶》的文本结构与荀子的思想体系发布于2023-03-19 21:4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