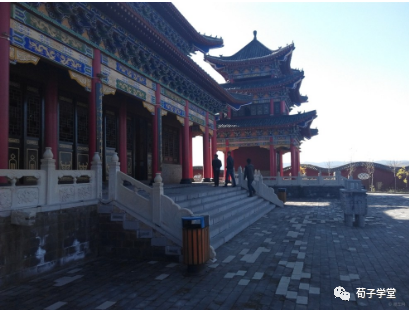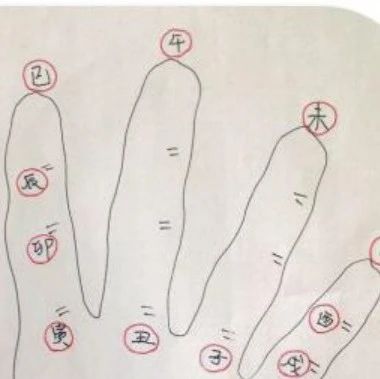摘 要:“民主”——“天惟时求民主”——是三代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包括做民之主和为民做主两个方面,二者互为联系又各有侧重,前者突出治民、教民,后者强调保民、养民,并呈现为从强调治民、教民到重视保民、养民,从提倡刑罚到主张“明德慎罚”的变化。清华简《厚父》反映的是夏人包括殷人的思想,属于“民主”说中的治民、教民说,其对典刑的推崇,对民众的不信任(“民心难测”),与周人重视保民、养民的“敬德保民”说有较大的不同。《厚父》的发现,对了解古代“民主”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民主”说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母题,春秋以后从中发展出民本说、民本君本混合说,以及君本说,以往学者仅仅从民本说对古代政治思想做出解读,是难以对其做出全面、准确把握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需要从民本范式转向“民主”范式。关键词:《厚父》;“民主” ;民本;孟子;荀子;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基金项目
收稿日期:2018-10-01
作者简介:梁涛(1965-),男,陕西西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清华简《厚父》公布后,因涉及《孟子》引《书》等内容,而备受学者关注。关于其思想主旨,更是引起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厚父》主要反映了古代的民本说,并将民本的产生推到夏商时期,认为“‘民本’问题是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元问题’,是中国早期国家机器草创时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其实,《厚父》所表达的并非民本说,而是作为三代意识形态的“民主”说,即“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只不过此“民主”说包含了做民之主和为民做主两个方面,二者互为联系又各有侧重,前者突出治民、教民,后者强调保民、养民;前者主要是君本,后者则蕴含着民本,后世的民本说实际是从“民主”说中分化出来的。虽然作为一种宗教观念或意识形态,“民主”说贯穿了三代的宗教、政治实践,但其内涵又有所变化发展,呈现为从强调治民、教民到重视保民、养民,从提倡刑罚到主张“明德慎罚”的变化。《厚父》的思想主要反映的是治民、教民说,是对夏、商政治理念的概括和总结,与周人的“敬德保民”说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拟通过对《厚父》的解读,对三代“民主”说的发展,以及春秋以后“民主”说的演变做出探讨,指出“民主”说才是中国古代思想哲学的母题,政治哲学研究需从民本范式转向“民主”范式。
一
“民主”一词在现有文献中虽出现于周初,但其反映的观念则渊源甚早,应该是随中央王权的出现而出现的。我们知道,夏代以前中国是邦国联盟时代,尧舜乃天下的盟主,其对邦国支配能力有限,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到了夏商周才出现统一的中央王权,这时中央王权之下虽然存在有大量邦国、方国,但王朝对邦国的控制力明显增强,邦国在政治上不再具有独立主权,经济上要向朝廷贡纳,军事上要随王出征或接受王的调遣。三代之王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对邦国国君具有调遣、支配甚至生杀予夺的权力,只不过后者内部尚没有建立起与王的直接隶属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已。随着中央王权的确立,“天命王权”、“王权神授”的观念随之出现,以说明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所谓“民主”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据《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曾称禹“为神主,为民父母”,《史记·夏本纪》亦称“禹为山川神主”,说明孔子的说法应是有根据的,反映的是古老的观念。禹既为“神主”,又“为民父母”,正合《左传·襄公十四年》所云:“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宋林尧叟注:“奉祭祀故为神之主,施德惠故系民之望。
“神之主”,即众神赖以得享祭祀者;“民之望”,即万民赖以足衣食者。故“神主”即“主”祭祀“神”者,代表神权或巫的力量;“为民父母”则表示教民、养民的职责和义务,代表了治权或君的统治。合而言之,大禹既具有神权,又掌握治权,是沟通天地、供养万民的统治者,也就是“民主”。不过,“民主”说虽然贯彻于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实践,是被其统治者普遍接受的,但在对于天、君、民及其相互关系上,不同时代又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据《礼记·表记》,殷人、周人在宗教信仰、政治治理上存在一系列的差异。在宗教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而“周人尊礼尚施”,在祭神的形式下突出了伦理的内涵。在政治上,殷人“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突出权威意识,强化等级观念。周人与之不同,更重视亲亲,把亲亲置于尊尊之上,“亲而不尊”,讲究人情而待人忠厚。殷、周宗教观念上的差异,前人多有讨论,而《表记》认为在政治观念上,殷人强化王权、重视刑罚,与周人有所不同,也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据《尚书·洪范》,殷臣箕子向武王进献的“洪范九筹”,其核心是“皇极”一项,而皇极就是要“惟皇作极”,一切以君王的意志为最高准则,要求“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而君王的准则,也就是上帝的准则 (“于帝其训”) ,具有绝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更有甚者,箕子还提出“休征”、“咎征”,将君王的行为分为好、坏两个方面。就“休征”而言,君王肃敬,雨水就会适时降落(“曰肃,时雨若”);君王清明,阳光就会普照大地(“曰乂,时旸若”);君王明智,天气就会温暖适宜(“曰哲,曰燠若”);君王深虑,天气就会适时转寒(“曰谋,时寒若”);君王圣明,和风就会定时而至(“曰圣,时风若”)。就“咎征”而言,君王行为狂肆,淫雨就会连续不断(“曰狂,恒雨若”);君王动静失常,天气就会经常干旱(“曰僭,恒旸若”);君王犹豫不决,炎热就会持续不断(“曰豫,恒燠若”);君王急躁不安,寒冷就会一直延续(“曰急,恒寒若”);君王昏庸无知,风尘就会不断飞扬(“曰蒙,恒风若”)。总之,君王的一举一动,无论好坏,都会影响天气的变化。这不仅是强化王权,更是神化王权,开后世天人感应的先河。
与强化“民主”的地位相应,在君民关系上,箕子则强调君王要做民之主,要绝对支配民,而不可听从于民。“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这是以星类比民,以日月类比君臣。古人认为天上的星星往往会影响到刮风、下雨等气候变化,如“箕星好风,毕星好雨”等。又认为月亮行经好风雨的星就引起风雨,如“月经于箕则多风,离(注:历)于毕则多雨”等。故庶民如同天上的星星,他们好恶无常,不可取法。日月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决定四季的变化,此象征“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如果月亮失常,跟随了星星,就会从其星而引起风或雨。故此章是说:“政教失常,以从民欲,亦所以乱。”(伪孔注)“喻人君政教失常,从民所欲,则致国乱。”(《正义》)如果将殷人“从民所欲,则致国乱”的观念,与周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国语》引《尚书·泰誓》)的信念做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甚至是对立。晁福林先生说,“箕子献‘洪范’九畴,着力提倡王权,事实上并未脱开商人观念的影响,是商人整体意识形态的反映。”“箕子所献九畴大法的核心是要武王成为作威、作福、玉食之君王,这一主张是为专制王权张目”,“与此后周人‘敬天保民’之民本观念相迥异是符合事实的。
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殷人没有保民、养民的观念,任何国家都是君与民共同组成的,所谓“民主”首先是民之主,没有民也就无所谓主。虽然古代的“民主”说一开始主要关注的是做民之主,是君对民的统治、管理,和民对君的依附、服从,但随着对民之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就不能不涉及为民做主以及保民、养民的内容。清华简《尹诰》中商汤称:“非民无与守邑”,“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商书》中也有“施实德于民”(《盘庚上》),“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盘庚中》)。前后,先王也。承,读为“拯”。我们的先王,无不是想着拯救和保护民众的。但如学者所言,这只是统治者重民、爱民的一些说法,并没有达到“以民为本”的地步,其在殷人的思想中只具于从属的地位。
与殷人不同,周人的“民主”说一是突出德,二是重视民,而不论是德,还是民,都为天所喜好和关注,故敬德保民方可得天命,为“民主”。《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注:改变祭品),惟德繄(注:是)物。’”上天公正、无私,对所有族群一视同仁,并根据他们的德来选择“民主”。上天喜欢的不是黍稷的芳香,而是美德的芳香。民众奉献的祭品没有差别,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祭品,才能获得上天的青睐和欣赏。“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故王要赶紧恭敬行德,只有恭敬行德才能获得长久的天命。在统治方式上,周人主张“明德慎罚”,慎罚并不是不要刑罚,相反如学者所指出的,西周政治理念之主流就是“软硬兼施”、“宽猛并济”,“德”、“刑”是维系政治秩序两种不同的方式,形成所谓“德、刑二元主义”。所以周人的“民主”说同样包括了保民、养民与治民、教民两个方面,既强调要为民做主,也重视为民之主,只不过由于周人突出了民与德,主张明德慎罚,其“民主”说较之殷人,更强调保民、养民和为民做主一面而已。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厚父》的思想,就容易把握和理解了。
二
《厚父》记载某王与夏人后裔厚父的对话,这位王,笔者同意李学勤等学者的看法,认为即周武王。而厚父,有学者推测可能是杞国国君。盖周人得天命、成“民主”后,封夏人后裔于杞,封殷人后裔于宋,同时在政治上采取兼容、开放的态度,积极总结、借鉴夏人、殷人的治国方略和政治经验。《尚书·召公》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监于有殷”,武王访箕子,《洪范》是也;“监于有夏”,武王问厚父,本篇是也。故《厚父》与《洪范》一样,应属于《周书》,而非学者所认为的《商书》或《夏书》,是周人对夏朝政治理念的记录和总结。不过由于殷革夏命后,夏人长期生活在商人的统治之下,故厚父的观念中也包含了商人的思想,受到后者的影响,实际融合了夏人、殷人的思想。《厚父》云:
惟祀,王监嘉绩,问前文人之恭明德。王若曰:“厚父!朕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惟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繇下为之卿事,兹咸有神,能格于上,知天之威哉,问民之若否(注:犹善恶),惟天乃永保夏邑。在夏之哲王,乃严寅(注:恭敬)畏皇天上帝之命,朝夕肆祀,不盘于康,以(注:治理)庶民惟政之恭。天则弗斁(注:厌弃),永保夏邦。其在时,后王之享国,肆祀三后,永叙在服(注:职位),惟如台?”
《厚父》第一简有残缺,简首缺四字,学者一般补为“惟王某祀”,因下句提到王,补为“惟某某祀”似更合理。这位“王”如前所说,应是武王。“嘉绩”,美好业绩。“前文人”,也见于《尚书·文侯之命》,伪孔注:“前文德之人。”这里指夏人的先祖禹、启、孔甲等。武王想借鉴夏人建立的功绩,了解其先王的恭敬显明之德,于是询问厚父。由于夏朝的第一位先王禹是通过治水获得天命,成为“民主”,故武王首先问禹治水事,但这段文字有残缺,约缺十一字。“乃降之民”的主语是天,降,赐也。由于禹治水有功,上天便赐给他民众,建立了夏邦。不过禹虽是夏朝的建立者,但按照当时的禅让传统,并不能传子,而是将王位传授给益。《孟子》记载此事:“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万章上》)这是从民本解释启之得位,认为启得民心因而得天下。不过《竹书纪年》则说:“益干启位,启杀之。” 《史记·夏本纪》也记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淮南子·齐俗训》称:“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可见启之得位并非只是民众的拥护,而是伴随着激烈的武力斗争,只不过由于启是最后的胜利者,成王败寇,故“启惟后”,启成为天子、“民主”。
在孟子眼里,启是以德而得天下,而《厚父》则说:“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关于启之失德,史籍有载。《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注:大)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注:启第五子武观)用(注:因而)失(注:读为‘抶’,击,指叛乱)乎家巷。”夏启纵情声色,寻欢作乐,不顾及后果,致使儿子武观酿成内乱。《墨子·非乐上》引《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注:锵锵)铭(注:读为‘鸣’,奏)苋(注:当为‘筦’)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注:当为‘天’),天用弗式。”(《墨子·非乐上》)“弗式”,不用。启淫逸纵乐,声闻于天,上帝不能接受。不过上帝虽然不满启的德行,但并不否认其天子地位,而是派皋陶为启的卿士,负责司法,协助其治理天下。而不论是启还是皋陶,都有神力(“兹咸有神”),能达于上天(“能格于上”),能知天之威严(“知天之威哉”),能察民之善恶(“问民之若否”),因而上天长久保佑夏邦。后来夏代贤明的君主,也能够恭敬畏惧皇天上帝的命令,终日祭祀(“朝夕肆祀”),不敢享乐(“不盘于康”),治理民众,勤于政事(“以庶民惟政之恭”)。故天不厌之,永保夏邦。在那时,要是后来在位的夏王,如夏桀之流,不忘祭祀禹、启、孔甲“三后”,遵从他们制定的法度,就会“永叙在服”。“叙”,通“绪”,继也。“在”,介词,犹“于”。“服”,职事、职位。故“永叙在服”是说,永继于位,引申之,指永保其国,永享天命。武王问,我的看法如何呢?
厚父拜稽首,曰:“都鲁(注:叹词),天子!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之(注:至)慝王乃遏佚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天乃弗若(注:赦),乃墜厥命,亡厥邦。惟是下民,庸(注:均)帝之子,咸天之臣民,乃弗慎厥德、用(注:以)叙在服。”
对于武王的疑问,厚父以天设立君、师的职责和目的作答。由于这段文字与《孟子》引《书》内容相近,颇受学者的关注。然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厚父》与《孟子》引《书》文字虽然近似,但内容并不相同。《孟子》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梁惠王下》)认为天设立君、师的职责是“助上帝宠之”。“宠”是宠爱之意。故四方民众有罪无罪,都由我来负责。这是典型的保民、养民说,属于周人的思想。而厚父则强调“其助上帝乱下民”,“乱”,治也。天设立君、师是帮助其治理下民的,从下文的论述看,治理的手段首先是刑罚。天亡夏邦,也是由于夏桀之流的“慝王”,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放弃了先哲王孔甲的典刑,沉湎于“非彝”也就是不合礼法之事,结果天不予宽赦,遂中绝其命,毁灭其邦。故夏之失国,不在于失德,而在于失刑。这是典型的治民、教民说,反映的是夏人、殷人的思想。虽然《厚父》与《孟子》所引《书》都主张君权神授,认为“天降下民,作之君”,属于古代的“民主”说,但在思想倾向上又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突出治民、教民,后者强调保民、养民。从《厚父》到《孟子》引《书》,正反映了“民主”说内部的发展和变化。
有学者注意到,在后人的记述中孔甲乃是一“淫乱德衰者”,如《国语·周语下》:“孔甲乱夏,四世而殒。”《史记·夏本纪》也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但在《厚父》中,孔甲被称作“先哲王”,他的故法、常规被视为后王应该效法的准则,显然又是一个“有德者”。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民主”观念的变化有关。虽然都是谈“民主”,但夏人、殷人强调做民之主,重在树立权威,加强对民众的统治,所以突出刑罚的作用。而周人则主张为民做主,提倡“敬德保民”、“明德慎罚”,试图以德来协调部族间的关系,增加其归附和向心力。“民主”观念既已变化,对“民之主”的评价自然也不同。由于周人观念的影响,孔甲逐渐被视为暴虐的昏君和“乱夏者”,而在夏人眼里,孔甲则是以刑治国的“哲王”。正如学者所说,“禹乃言其功德与立国,至于治国的祖宗之法,则在启与皋陶,无疑主于刑。因此,孔甲之典刑,正是上承夏启皋陶,重申以刑治国,维护祖宗之法。厚父之言,显然对以刑治国持赞赏态度,并进而将夏朝灭亡归因于‘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
夏虽已亡国,但其“下民”,也就是下文的“臣民”,包括臣下和民众,仍是上天之子,上天亦将其当臣民看待,只是没有谨慎其德,这里的德主要针对“非彝”的“彝”,也就是礼法而言,“弗”“用叙在位”,前一句的“弗”延续到这一句,不继于位,也就是不再享国、被授予天命。故对于武王的疑问,厚父明确肯定夏之亡国,是违背了以刑罚治国的传统,放弃了孔甲之典刑,这与周人对于夏、殷之鉴的认识,显然有所不同。于是武王转而问及“小民之德”。
王曰:“钦之哉,厚父!惟是余经念乃高祖克宪(注:效法)皇天之政功(注:政事),乃虔秉厥德,作(注:起)辟事(注:侍奉)三后。肆(注:今)女(注:汝)其若龟筮之言,亦勿可专改(注:擅改)。兹小人之德,惟如台?”
“钦之哉”,勉励之辞。“皇天之政功”,也就是上天之政事,因上天“命皋陶下为之卿士”,确立了夏的治国之法,故夏之祖宗之法亦可视为“皇天之政功”。下一句“乃虔秉厥德”的“德”也主要针对此而言。厚父既言孔甲之典刑,武王遂称赞其高祖能够效法“皇天之政功”,虔诚地秉持德,起而侍奉三王。下面两句较费解,学者的理解也存在分歧,从文字看,是说今天你当听从龟筮之言,不可轻易改变。似是武王建议厚父多听从龟筮之言,而不必拘泥其高祖的做法。以上是武王对厚父的客套之言,其真正想问的则是,“小人之德”如何?“小人”指下层民众,被统治者,“德”指其行为、表现。因夏之先王以典刑治国,与其对民众的认识有关,故武王由先王之法问及“小人之德”。
厚父曰:“呜呼,天子!天命不可忱斯,民心难测。民式克恭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注:效法)明德,慎肆祀,惟所役之司民启之。民其亡谅(注:诚),乃弗畏不祥。亡显于民,亦惟祸之攸及,惟司民之所取。今民莫不曰余保教明德,亦鲜克以谋。
曰民心惟本,厥作惟叶。矧(注:亦)其能贞良于友人,乃宣(注:恒)淑厥心,若山厥高,若水厥渊(深),如玉之在石,如丹之在朱,乃是惟人。曰天监司民,厥徵如佐之服于人。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民曰惟酒用肆祀,亦惟酒用康乐。曰酒非食,惟神之饗。民亦惟酒用(注:以)败威仪,亦惟酒用恒狂。”
厚父提出“天命不可忱斯,民心难测”,将天命与民并举,形式上似与周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的主张相近,但表达的思想则正相反。周人主张“天畏棐忱”、“天不可信”,但又认为民情、民意是容易发现、了解的,了解了民情、民意,“敬德保民”,也就可以得天命。这是以天命的形式肯定民情、民意,反映的是保民、重民的思想。厚父则不仅认为天命不可信,民心也难以了解、观测。民众既可以做到恭敬敬畏,畏忌不祥,保守、效法明德,谨慎祭祀,也可能不讲诚信,无所畏忌。而民不懂得诚信、畏忌,就会遭罹祸患。“亡显于民”一句,承前省略了主语“谅”、“畏不详”。所以民心既可向善也可向恶,向善向恶都是“司民”教化的结果。虽然民众口头上都会说自己保守、效法明德(“今民莫不曰余保教明德”),但很少有人真正如此谋划(“亦鲜克以谋”)。可见,民众的言论不可相信,其心也难以观测,真正有效的还是教化、刑罚,这是一种教民、治民说,与周人的思想明显有所不同。
武王问“小民之德”,此“德”主要指行为、作为而言,厚父答以“民心难测”,以内在的心去说明外在的德,认为行为的发动乃由心所决定,在思想认识上无疑是一种深化。但其心仍主要是经验心,心可善可恶,受环境和教化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厚父提出“民心惟本,厥作惟叶”。民心是根本,行为是枝叶,有什么的内心就有什么样的表现,心向善行为亦善,心向恶则行为亦恶,这当然不是什么民本说,而是对民众的一种怀疑和不信任,与“民心难测”的判断是一致的。不过《厚父》虽然认为“民心难测”,但也不否认民众可以通过努力成就善。如果能对友人忠贞诚信,使心长久地保持善,如同山终成其高,如同水终成其深。如同从石头中雕琢出玉,如同从朱色中提炼出丹,如此才成其为人。可见,只要“宣淑厥心”,就可以成善;若不敬德,自我放纵,也可以为恶,其中最严重的行为就是饮酒了。民若是放纵饮酒,不仅会败坏威仪,也会长久发狂。所以酒只可用来祭祀、享神,而不可用酒来享乐。民应恭敬其德,而不可沉湎于酒。《厚父》虽然没有说明,但显然认为,对于放纵饮酒者当由“司民”刑罚处置。不过“司民”虽然负责民众的教化、治理,但也要受到上天的监督,故上文专门强调,“天监司民,厥徵如佐之服于人”。“佐”,四肢。《逸周书·成开》:“人有四佐,佐官维明。”陈逢衡云:“人有四佐,谓四枝。”“人”,此指身体。上天监督官吏,就征状就好比四肢要服从身体。故“司民”也不可为所欲为,而应恭敬天命,服从其监督。
综上所论,《厚父》是武王访于夏人后裔厚父的记载,性质类似于《洪范》,
只不过前者是“监于有夏”,后者是“监于有殷”。由于厚父长期生活在殷人的统治之下,其思想也可能包含了殷人的观念。武王访厚父,目的是了解其“前文人之恭明德”,以夏为鉴,敬德保民,治国安邦。但厚父对孔甲之典刑的推崇,对夏桀亡国的总结,与周人观念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厚父所言,对于武王可能只具有反面的借鉴意义,而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晁福林先生曾分析指出,箕子所陈《洪范》九筹并没有为周人所接受。“箕子着意于为王权张目,实是殷人观念的体现,并不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周代的政治家们并未因循箕子的思想,并未一味彰显、加强王权,而是总结出‘敬天保民’的理念,并由此出发来制定治国方略。”类似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厚父》这里。《厚父》虽然在政治实践中没有发挥作用、产生影响,但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了解古代“民主”思想的珍贵文献。
三
作为夏、商、周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民主”说实际是一种君权神授的思想,是服务于王权统治,是为其合法性提供理论根据的。但三代的“民主”说,从一开始就包含有重民、保民的因素,并呈现出从强调做民之主到重视为民做主的变化。《厚父》的发现,以及其与《孟子》所引《书》的关联,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变化的具体过程和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周人虽然在对民的态度和认识上,较之以往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政治主张,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熠熠生辉的思想命题,但这些具有鲜明民本色彩的主张和命题仍主要是从属于“民主”说的,是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周人的天命信仰,所关注的仍主要是政权的授予与得失,是一种政治神学,“敬德保民”是为了配享天命,是为了“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召公》),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用康保民”(《康诰》)、为民做主是手段,“宅天命”、做民之主才是目的。因此准确的表达或许应该是,周人具有了民本的萌芽和观念,但还不具有完整、独立的民本学说。周人的政治理念依然是“民主”说,而“民主”从根本上讲是君本,周人的民本的价值理念与君本的实际追求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民主”说的基本内容。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国人地位的提高,并在政治领域开始发挥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左传·桓公六年》记随大夫季梁曰: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夫民,神之主也”是“夫君,神之主”的反命题。由于古代政治的合法性来自天命、神意,掌握了祭祀权,垄断了与神圣天意的沟通,也就掌握了现实的统治权,故“夫君,神之主”是以天命、神意的形式肯定了君本。而季梁“夫民,神之主”的命题则扭转了传统的认识,认为民才是真正的主祭祀者,故是以天命、神意的形式肯定了民本。又《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就迁都于绎一事进行占卜,结果出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情况,邾子曰:
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
当时邾文公已在位五十一年,年事已高,经不起迁都之劳。故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如不迁都寿命还可延长,为何不这样做呢?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命在养民”指国君的使命在于养民,命是使命之命,指天之所命。至于寿命的短长,只可说是时运了。“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同上)当国君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邾文公依然选择了后者,认为国君的利益是从属于民众利益的,民众既然得利,君主自然也有利,这当然是一种民本思想。邾文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思想,显然与“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的信念有关,这一信念来自于《孟子》所引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是对周人保民、养民说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不过春秋时期,虽然民本思想得到一定发展,但在现实中依然是以君为本,故当时更多的思想家是试图将民本与君本协调、统一。《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对晋悼公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师旷认为“天生民而立之君”,职责是“司牧之”,不同于邾文公的“以利之”,所强调的是教民、治民,而不是保民、养民,主要继承的是《厚父》的思想,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邾文公从《孟子》所引的“助上帝宠之”发展出民本思想的话,那么师旷则从《厚父》的“助上帝乱下民”完善了君本说,提出“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同上)的主张和命题。不过师旷生活于民本思想得到发展的春秋时代,不能不受其影响,不能不考虑约束君权的问题,这样他又试图立足于民本来限制君本。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天之爱民甚矣”,近于孟子所引的“助上帝宠之”,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天宠爱民众,所以就不会允许国君一人肆虐于民众之上,放纵其淫欲。这不同于师旷前文的君本思想,而具有鲜明的民本色彩,所突出的是保民、养民,而不是教民、治民。在同一段话中,师旷将“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和“天之爱民甚矣”两个分别具有君本、民本倾向的命题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其思想调和、折中的特点。所以他一方面主张,“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认为民众应该热爱、敬畏君;另一方面又提出,“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同上),甚至认为对于无道的国君可以流放。这说明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虽然有所发展,并与君本思想产生紧张、对立,但思想界的情况是复杂的,有人试图从民本突破君本,也有人试图调和民本与君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民本是孕育于“民主”说之中,是从后者发展出来的,故往往与君本纠缠在一起。很多人是在治道而不是政道上谈论民本,是在君本的前提下倡导民本,民本无法上升为国家最高的价值、政治原则,即使有一些闪光的民本思想和举措,也无法突破现实中的以君为本。这样实际上是二本,政道上是君本,治道上是民本,而无法真正做到一本——以民为本。要想突破“民主”的束缚,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就需要从权力私有走向权力公有,从“君权神授”走向“君权民授”。战国时的儒者某种程度上已认识到这一点,《礼记·礼运》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慎子·威德》)指权力公有。而要实现权力公有,就需要“选贤与能”,把最有才能的人选拔出来,替民众管理天下,此乃理想之大同之世。大同社会虽有君、有民,但其关系不同于权力私有的小康之世。《礼运》云:
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
明,动词,教导、明白之意。国君是需要被教导、明白的,而不是去教导,使别人明白的。不是国君教导民众,而是国君需要听取民众的意见和臣下的教导,这与“民主”说强调国君对民众的教化显然有所不同。同样,国君是被民众养活的,而不是国君养活了民众,这与师旷所言国君“养民如子”,“民奉其君”,“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也有根本的不同。凡主张君本者,无不以为是国君养活了民众;而主张民本者,则认为是民众养活了国君。君养活民,还是民养活君,是区分君本与民本的一个重要标准。国君的身份不同于民众,是专门的管理者,是政治领袖,因此民众应该服从、侍奉君,而不应让君服从、侍奉民,这是从治道上讲,指管理上的统属关系,而不是政道上的国之根本。笔者曾经考证,战国时期曾出现一个宣扬禅让的社会思潮,并发生燕王哙让国的政治事件,《礼运》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完成的,其对君、民关系的独特理解,显然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礼运》之后,孟子、荀子两位大儒均接受“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但在对民本与君本关系的理解上又有所偏重。孟子曾以尧舜禅让为例,说明天下非天子的私有物,而是属于天下民众的。其理由是“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最高权力是在天手里,给谁不给谁应由天说了算,而不能由天子私自决定。但“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天是根据人们的行为和事件表示天命授予的。当初尧让舜“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所以舜之得天下可以说是:
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
舜的天子之位既来自天,也是民众的授予。而在孟子这里,天是形式,民众的意志、意愿才是最高目的。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应经过天与民众的认可,“这种区分的内在含义,在于肯定天下非天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之人或天下之民的天下。”故在孟子看来,天子不过是受“天”与“民”委托的管理者,只具有管理、行政权,而不具有对天下的所有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民为贵”不仅是价值原则,也是政治原则,不仅认为民众的生命、财产与君主、社稷相比,更为贵重、重要,同时也强调,国君的职责、义务在于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否则便不具有合法性,可以“革命”、“易位”。
不过在经历了燕王哙让国失败之后,孟子对“选贤与能”、实行禅让持保留态度,认为“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万章上》),表明他不再看重禅让与世袭的差别,不再强调对于天子、国君选贤与能的必要。在《礼运》那里,被认为存在根本差别且分别属于“大同”、“小康”的政治原则,却被孟子说成是“其义一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本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民为本”是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天下为公”是政治原则,“选贤与能”是制度设计,“以民为本”是价值目的。只有选贤与能、实行禅让,才能保证天下为公、权力公有,只有天下为公、权力公有,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才能得到落实和实现。由于孟子不再坚持选贤与能、实行禅让,天子即位之后,除非残暴“若桀、纣者”,否则也不会被轻易废弃。而一般的人想要成为天子,“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 (同上),才可以实现。这样权力公有就成为空洞的口号而无法落实,民贵君轻也成为道德说辞而失去现实的意义。孟子放弃禅让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抉择,具有某种无奈甚至必然,但对其民本思想则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其无法突破君本的束缚和限制。孟子的思想或许可以概括为政道上的民本,治道上的君本,至于政道与治道如何统一,则是其没有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孟子主要继承了周人“民主”说中的保民、养民说,以及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而向前做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荀子则更多地吸收了古代“民主”说中的治民、教民说,同时与保民、养民说相调和,因而其与《厚父》的内容多有相近之处。以往学者认为,荀子也有民本思想,主要根据是《荀子·大略》: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这是以天命的形式肯定生民不是为君,而立君则是为了民,确有民本的性质。但仔细分析又不难发现,荀子对“以为民也”并没有做具体规定,上天设立国君,究竟如何为民?是教之、治之,还是保之、养之?并没有详细说明。如果与《厚父》的“乱下民”,或周人的“宠之”、“以利之也”做一个比较,不难发现后者对国君的职责做了明确规定,而荀子却没有,只是笼统提出要为了民。如果上天设立国君,其目的是宠爱或者有利于民,那么国君的职责就在于关注和保护民众的利益,这往往具有民本的性质。相反,如果上天设立国君,其目的是治理民,甚至是民众的过错,那么国君的职责就在于建构与维护政治秩序,这又具有君本的倾向。从荀子的一些论述来看,其所谓的“以为民也”,实际包括了治民与养民两个方面,是对《厚父》以及周人思想的折中与调和。在荀子看来,君之为民,首先是制定礼义,确立法度,使民众摆脱“偏险悖乱”的困境,以达到“正理平治”的结局。所以治民与养民是统一的,只有治民,才能养民;只有建立起礼义秩序,才能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和物质利益。礼义、名分才是天下最大的利益,国君则是制定和管理名分的关键所在。一旦没有了国君、礼义,社会就会陷入“强者害弱”、“众者暴寡”的混乱局面。故荀子的“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实际是指治民以养民,它虽然具有民本的性质,但也强化了君主的地位和权力。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并不强调君主的权力需要经过民众的授予,这就使其权力公有的观念大打折扣。与孟子相同的是,在经历了燕王哙让国失败后,荀子对禅让同样持否定态度,“‘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擅让恶用矣哉?”(《正论》)这样就使权力公有的观念失去了制度保障。所谓“以为民也”,主要是一种道德的职责和说教,至于如何为民,则取决于君主的抉择和判断。这样荀子思想中又存在明显属于君本的内容,“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君道》)君不仅能治理人,还能抚养人,更能重用人、文饰以区别人,“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富国》)这是明确肯定君乃天下之本,属于典型的君本说。前文说过,“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民为本”三者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荀子既然对于前两项或有所保留,或根本放弃,作为第三项的“以民为本”自然也大打折扣,笼统将荀子思想概括为民本,是不恰当也不准确的。最能反映荀子君民思想的,应是下面的文字: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同上)
君是源,民是流,君的治理、教化决定了民的表现。君若能爱民、利民,民则能为君所用;相反,若对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所用,则完全不可能。荀子的君民思想,似可概括为政道上的君本、民本混合,治道上地地道道的君本,实际是对古代“民主”说中教民、治民说与保民、养民说的折中与调和,但同时又做了进一步发展。从这一点看,真正与《厚父》思想相近甚至可能受其影响的应该是荀子,而不是之前学者所关注的孟子。
综上所论,三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乃“民主”说,包含了做民之主和为民做主两个方面,并呈现出从强调教民、治民到重视保民、养民的变化。春秋以降,“民主”的发展演变实际存在三条思想线索:一是突出古代“民主”说中蕴含的民本思想,由“民主”而民本,以春秋时期的邾文公、战国时期的《礼运》、孟子为代表,并经明末清初黄宗羲,下接近代的民主(Democracy),构成了“民主”——民本——民主的思想线索。第二条线索是将“民主”说中的君本、民本相融合,既强调做民之主,又要求为民做主;既肯定君主治民、教民的合理性,又要求其保民、养民,照顾到民众的利益。这条路线以春秋的师旷、战国的荀子为代表,秦汉以后更是大行天下,成为两千年帝制的主导思想。秦汉以后的帝制社会中,实际产生影响的便是源自荀子的调和君本与民本的思想。谭嗣同称:“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未必准确,但若是指君民关系的话,仍是可以成立的。第三条线索则是继承“民主”说中的君本说,发展为尊君卑臣、崇君弱民的思想,所谓“天主圣明,臣罪当诛”,其在法家思想以及后世的政治实践中不绝如缕,发挥着作用。以上三条线索中,第一种思想最有价值,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并对理解、吸收近代的民主观念起到积极作用;第二种思想在传统社会中影响最大,是帝制时代的统治思想,虽然也打着民本的外衣,实际却是民本与君本的混合,是君本前提下的民本。第三种思想是赤裸裸的君本,虽然是一个暗流,但被历史上的独夫民贼所信奉,成为其压迫、摧残民众的理论依据。以上三种思想都源自古代“民主”说,是从后者发展分化出来的,“民主”说才是古代政治思想的母题,搞清“民主”说的具体内涵和发展演变,才能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做出全面、准确的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需要从民本范式转向“民主”范式。
荀子劝学, 荀子, 荀子简介,荀子修身,劝学荀子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清华简《厚父》与中国古代“民主”说 ——兼论与荀子思想的关系发布于2023-03-19 21:5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