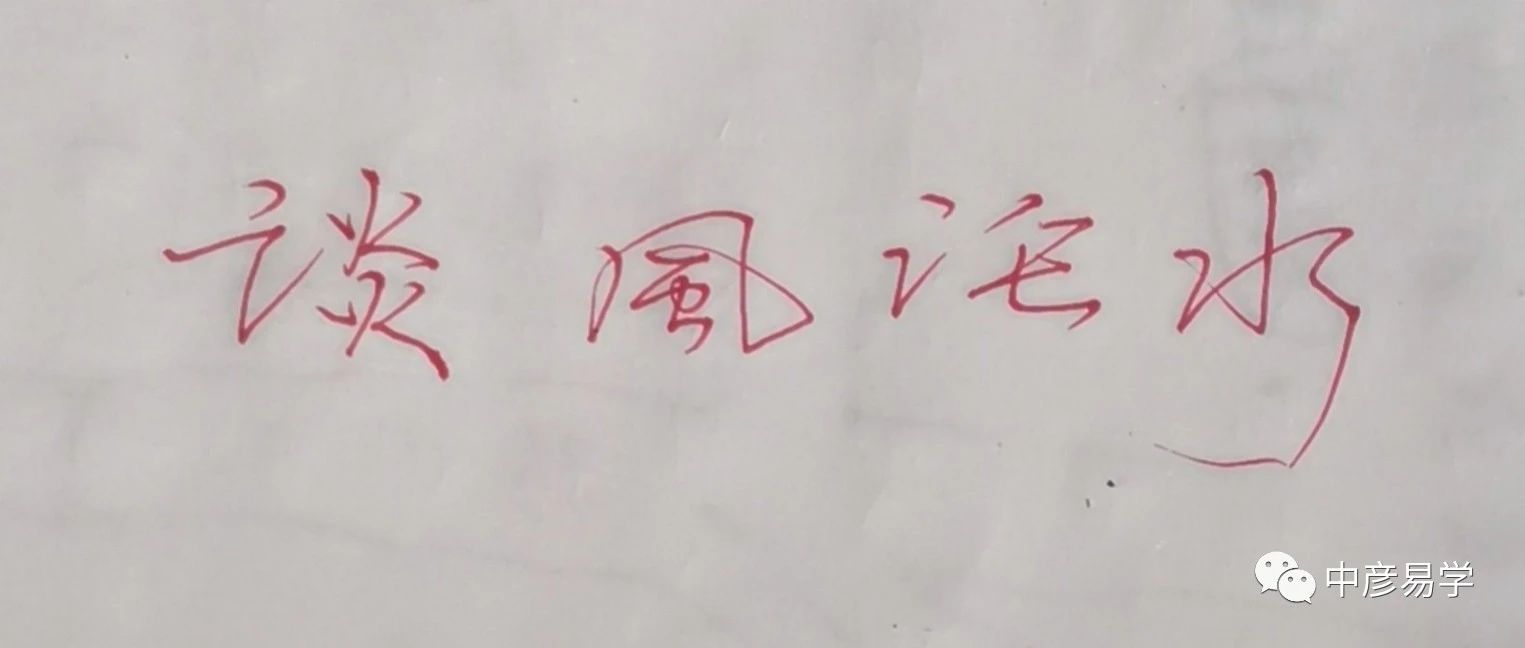字数: 约2913字
阅读时长:约10分钟
寻找佛教的故乡
中 国
佛教进入中国后,没有立即引起热烈的反响。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率先在政坛掀起狂风骤雨的是诞生于本土的道教而不是佛教,道教甚至还一度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所幸后来被和平收编。西晋统一天下后,北方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因为对汉地文化缺少归属感,北方民族皈依佛教的意愿更为强烈,这使佛教慢慢的取得了跟儒家分庭抗礼的地位。纵览整个南北朝,无论北方还是南方,佛教的政治影响力都极其巨大,看似佛教在中国找到了圆满的归宿。
然而在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改变了王朝的运行结构。深受儒家经典浸染的文人官僚,逐渐取代世袭贵族,接掌了行政权力,佛教的存在感也随之一落千丈,不复当年。欧阳修曾经记载一事:宋太宗一日来到佛寺,在佛像前烧香,询问当时的高僧赞宁是否应该拜佛,赞宁说:“不拜。”问其缘故,回答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从此皇帝烧香不拜就成了定制。皇权不再接受宗教的制约,甚至可以与佛陀平起平坐。
佛教在中国和在印度一样,都需要面对跟本土传统之间的巨大分歧。与印度人相反,中国人不关心神性,敬鬼神而远之,对于远离现实的形而上学概念,更情愿作模棱两可的处理。在印度造成轩然大波的无常、无我、涅槃,被眼力刁钻的儒家学者轻轻放过,印度人看来稀疏平常的轮回、业果反而遭到了穷追猛打。双方乐此不疲的进行论战,梁武帝号召信仰佛法的大臣写了一堆批判论文。说来说去,这些不是讲讲道理就能轻易解开的问题,倒不如把人放在印度生活几年或许更为直接。
在中国人的宇宙观里,世界是一旦启动就无限旋转下去的陀螺,具有起点但没有尽头。每年都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界毁灭”这类妄想从来不会产生。曾经有人为此担心,却留下了“杞人忧天”的笑柄。天地犹如父母,人类就是他们的孩子,哪里有父母抛弃孩子的道理孩子对于父母也是同理,就算人类不得不去流浪,也要把地球带上。然而,其他文化却不这么想:既然世界由神创造,那么也将由神来毁灭。地球充满邪恶,毫不值得留恋,要么毁于战争,要么迎来审判,历史必有终结,罪孽终将荡尽。佛教另有看法:世界的生生灭灭,本由因缘和合所致,经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便是一大劫,无穷无尽的循环下去直至永远。这与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共生循环宇宙”理论倒有些许相似。
中国的家庭观也是佛教面对的棘手问题。儒家将“齐家”与“治国”等量齐观,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人的眼中,家庭就是人生的全部,自打生下来,就签订了终身契约,不允许辞职,也不能退休,除非恩断义绝、一刀两断。儿女的未来由父母掌管,守孝三年也是理所应当。相比之下,印度人不把出家视为稀罕,本来就是应尽的义务。原来按照婆罗门的传统,孩子到了一定年纪,就应送到导师那里学习吠陀,持守梵行,乞食托钵。成年之后再还俗回家,娶妻生子,继承家业。等到儿子长大成人,所欠祖先的债务便可偿清,自己从此离开家庭,专心解决来生大事。所以出家本身并不要紧,选择出哪个家才是关键所在——出佛教的“家”,还是别的宗教的“家”。
文化的落差遮盖了很多本质问题,让人纠缠于细枝末节而无法自拔,如同管中窥豹,好似盲人摸象。摸到了象腿就以为大象是根柱子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反过来也说明,真正的佛法不可用有形有相的事物限定,而是超越了任何一种民族、任何一种文化。
通常把佛教与儒家、道家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合称为“儒释道”。“释”是“释迦牟尼”的简称,用来指代佛教。佛教虽然是一种外来文化,然而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液,为父权至上的古代社会平添了一些母性的光辉。如果用家庭来作比喻,儒家好似一位严厉的父亲,教你尽忠行孝、光宗耀祖;佛教犹如温柔的母亲,教你存心仁厚、积德行善;道教像是叛逆的大哥,教你抛下功名,清虚无为。离开佛教的中国,令人不堪设想,那将彻底沦为权谋者的战场,亦或是穷途者的围城。
中 国
下 篇
一般来说,佛教是弱势群体的避风港湾。胜利者虽然只占社会中的少数,却垄断了规则的制定,使得规则总是偏向于胜利者,难以顾及大多数人。这就是为什么士大夫总要找佛教的麻烦,也是为什么佛教历经磨难而总是屡禁不绝。佛教的宗旨就是给予众生平等的保护,何必要有亲疏远近的分别并不反对那些天纵英才去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潜质。很多人只想过平静生活,却被逼着去跟天才看齐。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彼此间的攀比,以家族的旗号把人变成了牟利的工具。
儒家对于佛教的压制,本质上是为了消除其政治影响,未必要把它从民间也斩草除根。尽管士大夫的奏折把佛教描绘得不堪于目,但是皇帝的圣旨喜欢把灭佛说成是保持佛教的健康发展,滥竽充数之辈需要清理,鱼龙混杂不是长久之计。此时的帝国已经在儒家那里找到了坚实的精神支柱,佛教大可以离开庙堂,恕不远送。
政治命运的交替,也反映在各个宗派的兴衰。当初那些颇受帝王眷顾的宗派,正应了那句老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唯识宗的崛起得益于玄奘大师与唐太宗的特殊关系,华严宗的兴盛跟武则天的大力支持直接有关,唐玄宗对于密宗青睐有加,而这些宗派皆如昙花一现,后世难觅踪迹。
与之相反,当初婉拒武则天的六祖惠能,他的禅宗南派延续至今,子孙兴旺;深受武则天优待的禅宗北派则遁影无踪。律宗分支中的相部宗和东塔宗,他们在戒律上的论争,甚至让唐代宗都不得不出面调解,再后来便销声匿迹;反倒是在终南山深居简出的道宣律师,他的南山宗却绵延不绝,传为正宗。备受隋炀帝喜爱的天台宗,进入唐朝后偏安江浙一隅,远离政治中心,在宋代迎来中兴。坚持民间路线的净土宗连续穿越了历史周期,保持着稳健增长。
这些例子无一不说明:一时得势与否,取决于当时的需要;生命能否长久,内在价值才是根本。
以唐武宗灭佛为分水岭,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在此之前,佛教的寺院往往坐落在繁华的都市,接近政治中心。皇亲国戚们喜欢把自己的旧宅改建为寺院,交给僧团使用。高僧们除了指导修行、管理寺院,还要小心斡旋于皇权四周,把握政治的微妙平衡。当皇帝御驾亲征,要陪侍身边;当全国遇到大旱,要施法降雨;当皇帝喜得贵子,要上表祝贺,顺便趁着龙颜大悦,请皇帝为新译经文赐写序文。
寺院的管理一般延用印度寺院的传统,采用以上座、寺主、维那——三纲为主的分权体制。用一个国家来比喻的话,上座类似于总统,在佛法修行上具有最大的影响,是全寺僧人的表率;寺主类似于总理,在日常事务上具有最大的权力;维那类似于检察官,在督导纪律上最有分量。三者各司其职,相互合作而非隶属。凡是重大事务,都要经过僧团的集体决议,羯磨类似于表决,授筹类似于投票。以佛陀制定的戒律为准绳,戒条为纲,犍度为目,交织成疏而不漏的法网。
在唐武宗之后,佛教逐步退出了城市,走进了山林。僧团不再仅仅依靠大施主的供养,而是自力更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寺院的管理体制从三纲分立演变为一元领导,这便是禅宗开创的清规。禅宗寺院将方丈视作佛陀的代表,方丈率领的执事分为东西两序,犹如朝廷的文官武将。
通常把唐朝视作中国佛教的顶峰,之后盛极而衰,走向漫长的下坡路。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唐朝又是一个新的开端:一种新的佛教形态从一个新的方向进入到了中国。佛教的二次传入,意义深远而又容易被忽略。帝国的戏份只会越来越重要,没有丝毫削减。
延伸资源下载(千G中华传统经典古籍|儒释道古本及民间术数大全超强版持续更新中......)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 贤超法师:寻找佛教的故乡【二】发布于2022-01-21 15: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