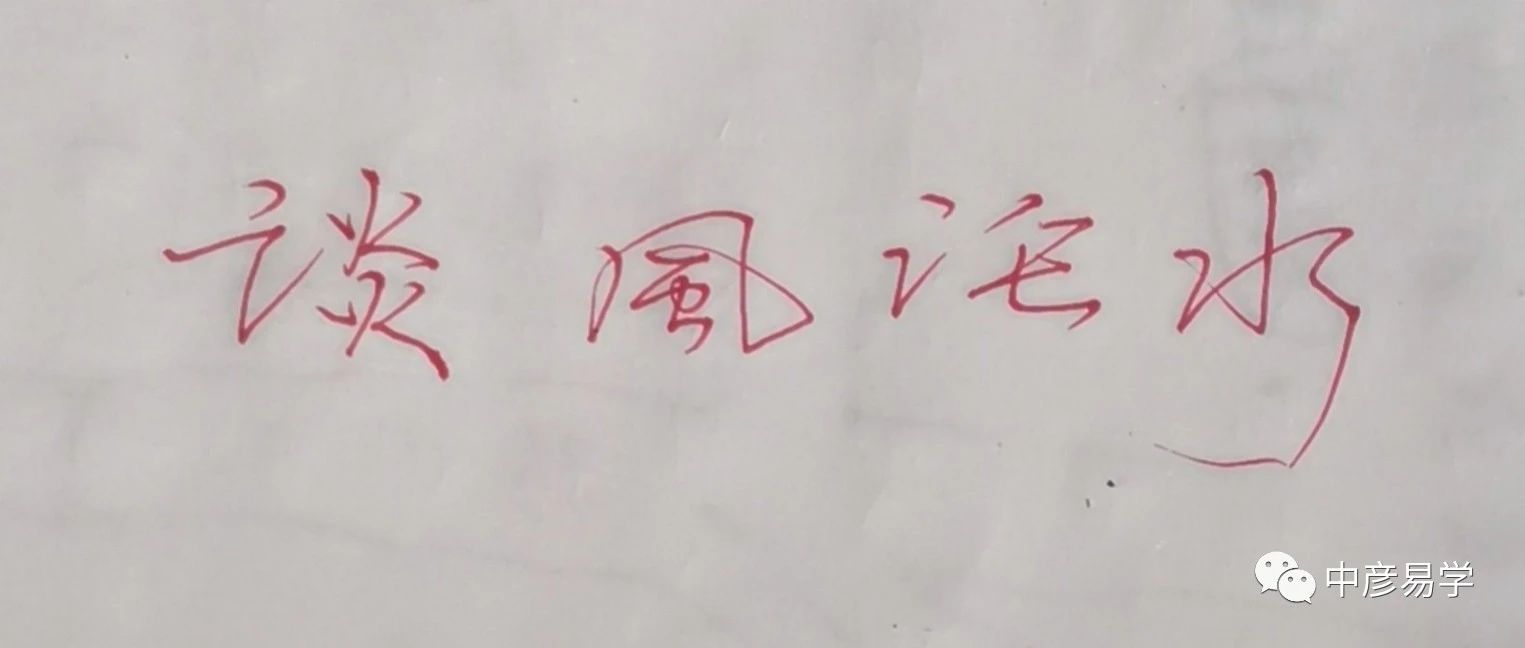(作者:纪赟,现任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兼教务主任、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博士论文《梁慧皎<高僧传>研究》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现主要从事佛教文献学、佛教制度史、敦煌学、佛教艺术诸学科之教学研究。纪赟老师提供图文并惠允首发大作,在此特表感谢!)
内容摘要:这批犍陀罗语写经创造了至少两个记录,第一是其中有一部《譬喻经》残片,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是在公元前184-46年之间,也就是说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佛经!以后再要打破这一纪录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第二个记录也是佛教文献界更为关注的,就是其中的大乘佛经!也即福尔克自己与日本著名佛教文献学家辛嶋静志所研究校勘的《般若八千颂》的第一与第五品残片。这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大乘”佛经!它对于佛教史研究的意义极其重大。因为首先就年代而言,其断代为公元后47-147年,而且据研究抄自一个更早的版本,所以我们还可以将大乘佛经的(书面)物质形式再往前推进一步。同样重要的还有,通过语言学比较,可以大体推断出这部大乘经就是来源于犍陀罗地区,其原始撰成语就是犍陀罗语。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大乘佛教起源阶段的研究多了一个无比珍贵的确凿证据。其次,有意思的是经过多语种《般若八千颂》的对校,学界发现这个犍陀罗语本比十多年前发现的巴米扬贵霜时期(公元后三世纪的下半叶)梵语本《八千颂》残卷,更为接近中国早期支娄迦谶的译本。换而言之,就是这个早期中国汉译本比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梵语本还要更为接近此经的原始本!
此外,纪赟老师介绍说,这次发现的断代为公元1世纪的实物大乘佛经,是一个更早的经典版本的抄写本,因此实物大乘经典的更早存在还可以合理地往前推。根据日本著名文献学家辛嶋静志和其老师K.R.Norman的文献学和语言学考证推断,书面大乘经典肯定是公元前就有的了。此外,美国著名文献学家那体慧JAN NATTIER有一本重要的研究大乘佛教的書,叫A few good men,是研究《法鏡經》(即《郁伽長者會》)的,此書第45-46頁中提到此经的時間斷代為“公元前一世紀”,而其他大乘佛經如《八千頌》、《般舟三昧經》等還要早一個世紀,就是出现于於公元前二世紀,只是當時還處於口傳階段,沒有書面存世。這點與小乘佛經一樣,小乘經也是在公元前一世紀才開始寫下來的。
本号将继续跟踪关注有关佛经形成的文献研究进展情况。
犍陀罗语是什么
一般人印象中,印度的佛经都是用梵语(Sanskrit)书写的,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在早期佛教文献之中。其原因是因为佛陀特殊的语言政策,在此方面北大季羡林先生已经有过很好的研究,学界也早就得出结论。即佛教最初所传播的数百年中是以俗语(Prakrit),而非梵语为载体的。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佛教从一诞生起就致力于向普通民众传教,而与以上层贵族语言梵语为基础的具垄断性的婆罗门教不同。
但是后来佛教文献经历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典改译过程,这就是佛经梵语化运动。顺便说一句,这个翻译过程中还产生了不少误解与错误,比如大乘佛教这个术语中的“大乘”(mahāyāna,伟大的车乘),据日本文献学家辛嶋静志的研究,其实本来是犍陀罗语mahājāna“大智慧”,后来在梵语化时被错译为了mahāyāna(梵语“大智慧”的正确翻译应该是mahāj?āna),以后也就逐渐以讹传讹了。梵语化运动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与印度社会后来婆罗门教回潮以及梵语地位的回归有关,这也影响到了佛教内部。因此在数百年间这些俗语佛经就逐渐被改写为佛教混合梵语和最后纯正的梵语佛经了。
就存世的梵语佛经情况来看也是如此,目前梵语佛经中规模比较大的搜集品之中,其年代先后排序大体为:中亚新疆地区搜集品、西藏地区收藏与尼泊尔搜集品等,而其中最古老的中亚新疆地区发现的梵语经典也基本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后。另外说一句闲话,中国内陆地区一则因为气候不够干燥(保留佛教古写本较多的西藏、中亚与尼泊尔大多气候干燥,又与外世较为隔绝),二则因战乱频仍,基本很难保存非常古老的贝叶经。所以虽然据古文献记载像法显、玄奘、义净等印度求法僧都曾带回了大量印度语佛经,但在内陆却基本很难保存下来。数月前去大陆某著名寺院参观,有负责人指其珍藏的贝叶经说是玄奘时代的,但一望而知非为那个时代的文字,时代应不会太过久远。
那么什么是犍陀罗语(Gāndhārī)呢,如果用学术的定义,那它首先是一种俗语,或者叫中期印度-雅利安语(MIA),更准确的说是一种从古代印度-雅利安语(OIA)派生出来的方言。顾名思义,其得名是来自产生与原始通用地点,即以白沙瓦河谷地带为核心的犍陀罗地区。此种语言的字体也较为独特,就是从右向左反向书写的驴唇文(Kharo??hī,或称佉卢文),(见图1,驴唇文残片)此文字据传是由一位驴唇大仙所创,因此得名。而犍陀罗地区又因其地扼北印度通往希腊化地区、中亚与中国的要冲而成为了文化的交汇点。
那么这种语言对佛教的重要性何在呢简而言之,目前存世最为古老的佛经全部为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区出土的,并且全部都是用犍陀罗语书写!而梵语佛经一般而言,要比犍陀罗语佛经晚至少好几百年。原因除了佛教的原始语言政策之外,另外,犍陀罗语还曾经是在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传播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贵霜王朝的官方语,它还曾是中亚很多地区佛教徒的共同语与经堂语。这种宗教功能类似于基督教世界中世纪的拉丁语、后来北传佛教世界的梵语与南传佛教世界的巴利语。只不过由于中亚政治的变迁,在公元三世纪后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却在佛教从印度向中国传播,以及大乘佛教逐渐发展兴盛的这一关键时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并成为了这一伟大的佛教枢纽时期的实物见证。
就形式而言,犍陀罗语写卷也非常有特点。在此要简单说一个被人误解的重要事实。即人们一提到印度佛经,就想到贝叶经。但其实整个印度次大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载体,即南部的贝叶经与北部的桦树皮写经。由于印度次大陆北部与中亚地区不产棕榈树叶,因此就使用桦树皮来书写。而目前中亚地区发现的早期佛教文献,尤其是犍陀罗语佛教文献主要是书写在这种载体之上。(见图2明显带有桦树皮疤痕的写经)
犍陀罗语的发现:百年前的发现
犍陀罗语的发现并非始于当代,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犍陀罗语本佛经就是和田本《法句经》。这个写卷其实被人为地分为了两部分(可能是商人牟利所为),分别为法国与俄国探险家所得。其中法国部分可能是由1892年由法国探险家吕推(D.deRhins)与李默德(J.F.Grenard)在新疆发现。此后他们继续前往西藏考察,结果吕推在途中被杀,为此还酿成了外交事件。这个写本到了1897年,才由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S.Lévi)与塞纳(E.Senart)加以研究,并旋即由后者作了刊布,并在第一届东方学家大会上做了报告。巧的是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俄国部分也浮出了水面。(见图3犍陀罗语《法句经》的照片)
俄国部分的发现者是俄驻新疆喀什的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N.F. Petrovsky),并被带回了圣彼德堡,由著名东方学家奧登堡(S.F.Oldenburg)研究,但没有刊布照片或录文,因此在学界影响也不大。此后就有了不少伟大的文献学家都加入了对犍陀罗语的研究之中,如伟大的巴利圣典学会的创始人戴维斯(T.W.Rhys Davids)、德国印度学家吕德斯(H.Lüders,陈寅恪的老师,也是季羡林的师公)、比利时佛教大师普散(dela Vallée Poussin)等。普散在汉语世界中人们对其所知甚少,但他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普散19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后来学习梵语、巴利语、阿维斯塔语、汉语与藏语,他的一些重大佛学研究成就皆是以这些经典语言为基础。令人惊奇的是直到退休为止,他在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的科目却主要是希腊语与拉丁语的比较语言学。
而对犍陀罗语研究史特别重要的则是英国语言学家贝雷爵士(Sir H.W.Bailey),这也是一位佛教文献学界的奇才,他在很年轻之时除了欧洲的古典与现代语言之外,还涉猎了阿拉伯、泰米尔、波斯、日语等,据说他能够阅读的语言超过五十种,后主要在英国剑桥从事教研,至1960年更因研究杰出而受勋。贝雷在1946年发表了一篇里程碑似的文章,即《犍陀罗语》(Gāndhārī),这是后来学界将此种语言定名的依据之一。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原苏联将其所藏的写本交给了剑桥的另一位印度学家布腊夫(J.Brough)加以研究。这样他利用俄藏部分,再加上法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的一些以前未发表的残片,就第一次将这部犍陀罗语本《法句经》作了整体性研究。其成果就是犍陀语研究史上的经典——出版于1962年的《犍陀语法句经》一书。(见图4书影)因此我们也得以知道了此部犍陀罗语佛经的原貌,写本原件约20厘米宽,5米长。原件可能是卷在一起的,但发现者为了牟利却将之切割开来分别售给了法国与俄国人。这部佛经的断代,据北大林梅村老师考证,是公元175-230年之间,其部派归属可能是法藏部。
以后佛教学界能够获得的犍陀罗语材料甚少。真正的转机是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段时间内中亚尤其是阿富汗地区的动荡局势。众所周知,这种混乱的局势一方面造成了文物的大破坏,比如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就被永久性地毁坏了。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走私集团的猖獗,也使大量佛教文物被盗卖到了欧美日,其中就包括珍贵的犍陀罗语写卷。值得一提的就是不少这些犍陀罗语与其他语种的佛教经典,是由伦敦一家名叫福格(Sam Fogg)的中世纪古文物店转手。此店还出版有自己的售卖品目录,其中佛教写本可参《丝路上的写本》一书。(见图5书影)
百年后的发现:不幸中的万幸
相对于梵语与巴利语文献,现存犍陀罗语文献数量较少,从事研究的学者也屈指可数,大体是以下这几个团队。第一批重要发现的研究者是美国美国华盛顿大学邵瑞祺(Richard Salomon)为核心的团队。前文已及,继百年前犍陀罗语《法句经》之后,新发现的犍陀罗语文献中主要是些世俗文书等,并且也非常零星破碎。而到了上世纪末,由于阿富汗地区的战乱与文物走私猖獗,大英图书馆得以募集了大量犍陀罗语文献,并委托华盛顿大学的团队加以研究。这一批共有29捆桦树皮写卷,此后这一团队后来又获得了斯尼尔搜集品的部分与华盛顿大学自己所购得的一种阿毗达磨文献,利用这些材料他们从1999-2010年共出版了七本专著,其成员后来还在继续编写犍陀罗语辞典。(见其中两本书的书影,图6、7)
学者刚拿到这些写卷之时,其形态非常糟糕。(见图8,犍陀罗语写经初始状态,图9整理后的情况)因为这些写卷时代久远,已经离现在有两千年之久。说两千年这个概念太抽象,但在十四世纪的明代,据载宋刻本(十至十三世纪)就价值不菲,甚至要论页论银的地步,而此写卷甚至比宋刻本还要早上千年!所以虽然中亚地区保存条件好,但每包写卷还是像糖果一样融在了一起。所以要靠文物专家来处理,先加湿以增加写本的韧性,再慢慢展开,并夹在两片玻璃片中真空保存,这样才送到写本专家手中转写、翻译。这些写卷最早是被发现于一些陶罐之中,其原始埋藏地点可能是在覆钵形的佛塔内。比如其中斯尼尔搜集品的犍陀罗语佛经就是放在高35厘米,瓶口直径30厘米的陶罐中,这些陶罐上不少还有铭文(见图10,写经罐,图11内装佛经的陶罐)。
至于这些佛经的性质,据邵瑞祺估计,由于基本都是残卷,并且破损严重,所以应该是被抛弃或者用坏了的卷子,不能随便乱弃,就遵循佛教的典仪被置于罐中埋藏了起来。这种收藏方式,当然也让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著名的死海古卷。所以它不是佛教文献学家科林斯所提出的“仪式性藏经”,而是寺院中大量使用后废弃经卷的埋藏,这一点与敦煌藏经洞中的情况颇为类似。后者,按照著名敦煌学家方广錩先生的理论,也属于废弃的经卷。
这些文献既给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因为它们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佛教经典,基本都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左右,也就是说这些经典抄写之时,学界承认的最早译经师安世高正在中国忙碌地译经呢!而且大英图书馆搜集品中还提到了公元后一世纪早期的印度—斯基泰皇室对小乘法藏部的供养,而这要比稍晚大乘佛教处于鼎盛时期的贵霜王朝更早,也就是说为我们对此一过渡时期的佛教面貌提供了侧写。
但这些经典所带来的遗憾也很明显,就是到此时所发现的经典主要只是小乘经,比如《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法句经》、《无热恼池偈》等,而没有大乘佛经!因为佛教文献界一直有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就是大乘佛经在早期印度佛教界的地位与实际情态。有些学者,比如在欧美影响很大,同时争议也很大的著名佛教文献学家绍本(Gregory Schopen)就通过大量考古资料的研究,认为大乘佛教在印度的石刻史料中出现极晚,因此大乘佛教可能并没有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兴盛。由于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找到大乘佛经的影子,所以学界对于他的这个大胆假设就无法证实或证伪。
到了2006年,由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的两位学者纳西姆?汗(Nasim Khan)与索黑尔?汗(Sohail Khan)介绍了一批新发现的写本,这就是令人震撼的巴扎尔(Bajaur)搜集品,这个写本最让佛教文献学界激动不已的就是终于找到了犍陀罗语“大乘”佛经!这批写本发现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福尔克(H.Falk)教授就与慕尼黑大学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教授共同组织了“犍陀罗出土早期佛教写本项目”团队对之加以研究。这个搜集品共有18个桦树皮写卷,其中最长的一个写卷长度超过了220厘米。
这批犍陀罗语写经创造了至少两个记录,第一是其中有一部《譬喻经》残片,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是在公元前184-46年之间,也就是说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佛经!以后再要打破这一纪录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第二个纪录也是佛教文献界更为关注的,就是其中的大乘佛经!也即福尔克自己与日本著名佛教文献学家辛嶋静志所研究校勘的《般若八千颂》的第一与第五品残片。(见图12犍陀罗语本《八千颂》)这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大乘”佛经!它对于佛教史研究的意义极其重大。因为首先就年代而言,其断代为公元后47-147年,而且据研究抄自一个更早的版本,所以我们还可以将大乘佛经的(书面)物质形式再往前推进一步。同样重要的还有,通过语言学比较,可以大体推断出这部大乘经就是来源于犍陀罗地区,其原始撰成语就是犍陀罗语。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大乘佛教起源阶段的研究多了一个无比珍贵的确凿证据。其次,有意思的是经过多语种《般若八千颂》的对校,学界发现这个犍陀罗语本比十多年前发现的巴米扬贵霜时期(公元后三世纪的下半叶)梵语本《八千颂》残卷,更为接近中国早期支娄迦谶的译本。换而言之,就是这个早期中国汉译本比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梵语本还要更为接近此经的原始本!我想这对于很多致力于研究与推广汉语佛经的学者与教界,都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巴扎尔写本之中,还包括一部《阿閦佛国经》残片,(见图13)此经的出现对于净土宗佛教研究也极具意义。在此我略提一下美国著名佛教文献学家那体慧(Jan Nattier)。她曾任职印第安纳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国际高等佛教研究所。她在早期汉语佛教文献研究领域中成果丰硕,但华语佛教研究界除了知道他是威名赫赫的禅宗史学家马克瑞(John R. McRae)的夫人,或者她的“《心经》伪经考”外,对其研究成果所知甚少。此人早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接受佛教文献学训练,早年跟随来自中国察哈尔的蒙古学家约翰?贡布扎布?杭锦(John GombojabHangin),以及克鲁杰(John Krueger)学习蒙古语,跟随霍夫曼(Helmut Hoffmann)学习古藏语与敦煌文献,跟随克拉克(Larry Clark)学习古回鹘语。此校在汉语佛教研究界名气不大,但在当时、现在都是中亚研究的重镇。这一学术经历对那体慧学风的形成与学术视野的开拓具有较大影响。1974年她校勘并翻译了回鹘语的《慈悲道场忏法》(K?anti q?lmaq nom bitig,即《梁皇宝忏》)。此后那体慧到哈佛大学先后获得硕士(1980)、博士(1988)学位。其硕士导师为永富正俊,那体慧跟随永富学习《八千颂般若经》的汉文文献。其博士导师为著名蒙古学家柯立夫(F.W.Cleaves,1911-1995)。博士论文就是其成名作《未来某时:佛教法灭预言研究》,和她几年后对《心经》的研究一样让人震撼,此书也具颠覆性的成果,我们习以为常的正法、像法、末法三分其实在文献学考校下根本经不起推敲!
而她在2000年发表了《阿閦佛国土:净土佛教史中失掉的一环》,此文从最古老的汉译本《大阿弥陀经》来检视净土佛教的印度本源,并认为阿閦佛国土是其中的过渡阶段。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认为阿弥陀佛凈土思想与此前的佛教思想关系甚少,因而需要从印度域外,比如波斯、希腊来寻找凈土思想的渊源。那氏则直接从印度文化本身寻找相关证据,从而跳出旧有模式,为净土思想的产生找到了新的合理解释。而犍陀罗语《阿閦佛国经》的发现,也完全证明了那氏研究的前瞻性。如果学界对此发现更加重试,或许可以让我们重新来书写早期净土宗的发展史!
除此之外,挪威著名大亨兼收藏家斯柯延搜集品之中也同样存有犍陀语本写经。它们目前正在被慕尼黑大学哈特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加以研究,包括《贤劫经》、《菩萨藏经》、《集一切福德三昧经》。而另一位匿名收藏家还藏有一部《大乘顶王经》残片。最后两部大乘佛经特别值得一提,众所周知,1999年7月30日(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日本大正大学高桥尚夫教授在布达拉宫发现了学界教界认为久已失传的梵本《维摩诘经》,此后文献学界对此经就更加兴趣浓厚。(见图14书影)而在犍陀罗语《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之中出现了khu kulputra so vimalak(*rti tathagata)的文字。最初学者发现vimalak(*rti),也即“维摩诘”或“净名”时都十分振奋,以为可能会是《维摩诘经》。但在释读后面的部分后才知道此句就是罗什所翻译《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中的“(男子)净名(王如來说是法已)”这一句。而公元1-2世纪的犍陀罗语《大乘顶王经》中的主人公又是维摩诘居士之子,因此学界正在对未来出现大乘《维摩诘经》的可能翘首以待。
拜全球化的影响,人类间的文化交流日益便捷,一些偶然的因素就会使那些沉埋在历史深处的碎片浮出海面。在佛教领域之中,上世纪末开始对日本古写经的系列整理与研究,犍陀罗语佛经的发现,再加上西藏地区梵语佛经的整理,都极大地改变了不少过去我们对于佛教的印象,也将改变将来佛教研究的面貌。然而,这些无比重要的发现与研究,却往往还是藏在深闺人不识,所以究竟这些伟大的学术发现能与我们的日常宗教与世俗生活有什么影响,则恐怕还只能拭目以待。
延伸资源下载(千G中华传统经典古籍|儒释道古本及民间术数大全超强版持续更新中......)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 第二辑经解篇纪赟:佛教经典大发现时代:佛教的死海古卷犍陀语佛经篇发布于2022-01-21 17:53:11